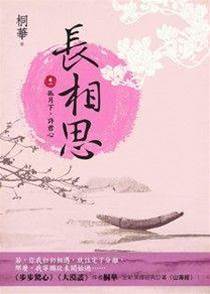《重生之蒲葦如絲》 第40章 四十
吉祥布莊離百福巷不過一里有餘,店面不大,除了十幾種不同材質和花樣的布匹之外也兼售,主要的客人應當就是在百福巷那一片的尋常百姓。
如姒隨手翻了翻,店裡最好的大約便是上所穿綠的松江細布,餘下的便是青灰褐之類更適合男子的布細布,不一而足。
采菀跟在如姒後,也附和著翻了翻,自然是完全心不在焉的。然而眼睛朝櫃檯掃了又掃,卻並沒有看見有學徒的樣子。
這家布莊實在不大,如姒幾乎將所有料子都看了一回,仍沒有見到陳潤的影子,索便去問掌柜:「老闆,你們店裡可以定做裳麼?若是買的多些,有沒有學徒能將料子送到我家裡?」
那掌柜是個四十來歲的婦人,容貌倒是平常,行言語之間十分剪斷利落,明外的很。聞言立刻滿臉都是笑容:「當然是能送的,姑娘要多料子?也是能做的,姑娘要做什麼裳?」
「裳,是給家人穿的。尺寸容我再問問,」如姒信口回應,「料子,還有這種淺綠的嗎?另外——」新手又指了幾個其他的深細布,「每樣兩匹吧。如果總共是十匹布,今天能送過去嗎?」
「十匹啊,」那婦人笑容越發燦爛,卻也有兩分著急,「這個,我那個外甥今天病了,明日便給姑娘送去行不行?」
「病了?」如姒隨口應付道:「哦,那也可以罷。這料子多錢一匹?」
那婦人不聲地再打量如姒兩眼:「這料子可輕的很,只要一兩銀子一匹,姑娘要十匹,便是十兩整。我再送姑娘兩軸綉線可好?」
「這樣的料子哪裡要一兩銀子,你當我們是冤大頭嗎!」采菀忽然反駁道,語氣里竟是很帶了些怒氣。
Advertisement
如姒不由詫異地看了看采菀,便是這價格有水分,卻也不值得這樣生氣,采菀並不是這樣暴躁的脾氣啊?
那婦人眼珠一轉:「哎呦這位姑娘脾氣還真是急啊,這料子是上好的松江細布啊,不信打聽打聽,這條街上誰不知道我胡二娘是最公道的了。姑娘若是嫌貴,既然要這樣多,那再減五百錢也使得。」
采菀拉了拉如姒的袖子:「姑娘,咱們走罷。」
如姒心知有異,便向那胡二娘敷衍了一句:「那我們再看看,若要便明日再來。」
胡二娘冷了臉:「嘁,買不起還大開口。不買拉倒!」
采菀瞪了那胡二娘一眼:「我們姑娘有錢的很,誰要買你家的破布!哼!」拉著如姒就走。
出了店門又走了半晌,如姒見采菀氣平了些,才低聲問道:「這是怎麼了?不是陳潤的姨母麼?」
采菀垂了眼皮:「好像只是同鄉同族罷了。他以前說過,在到辜掌柜的綢緞莊子之前,曾經幫襯過一個遠親。只是那親戚待他很不好,又累又苦,還又打又罵。他……他手上有塊疤,便是那親戚用簪子扎的。這些事太久了,我起初並沒想起來。剛才聽說了一句外甥,才……」
如姒這才明白,心裡算一算時間,第一世的如姒是十六歲出閣,大概十七歲的那年采菀與陳潤初相識。那麼現在就是倒回來三年的時,所以陳潤還在跟著親戚而非老實厚道的辜掌柜。
但這也不難解決,學徒又不是賣,大不了直接將陳潤雇傭過來。反正如今燕微嫁妝歸還回來之後,如姒的下一步打算也是開鋪子做生意,陳潤正是個得用的人才。而今日出來除了買布,還有一件事就是去拜訪上次沒能見到的素三娘子。
Advertisement
按著第一世的記憶,並沒有近親在京的陳潤在斷重傷之後是由鄰舍們照顧的,當中也有素三娘子。那麼如今素三娘子或許也已經認識陳潤了呢?
如姒又寬了采菀兩句,便帶著往百福巷的方向直接走過去。
剛走了沒幾步,便聽街上一陣突如其來的腳步以及驚呼之聲。
如姒和采菀自然也駐足過去,便見自大街的西端,有人狂奔而來,兩旁的攤販趕忙儘力收拾東西向路邊後退,而行人也紛紛閃避。
在其後不遠還有數人追趕:「站住!」
如姒和采菀雖然退到了路邊,心裡卻也好奇的很,不由探頭張過去,心想難道這又是一個燕榮式私奔麼?
眼看奔逃之人漸漸靠近,便能看清他材很是高大魁梧,手上還持著染著跡的單刀,一臉兇神惡煞。
而後頭追趕的大約有五六人,大都是衙門公差,在狂奔之中速度有快有慢,而最接近的一人,赫然便是陳濯!
如姒看清了陳濯的臉不由一驚——自己這到底是什麼人品啊!
不過就是上街買個布,居然就能現場圍觀警草抓賊!
然而這個興和刺激的覺下一秒就變質了,因為那在前奔逃的大個子見陳濯愈發近,竟向如姒這個方向沖了過來!
這——這是要抓人質嗎?
這時候該怎麼辦!
轉逃跑?
立刻爬樹?
還是大一聲你看不見我!?
如姒呆了一瞬之後,竟然在對方要到面前時順從了自己膝蓋與地球引力的本能——抱頭猛地一蹲!
那人已經手要去抓如姒了,這一蹲剛好他撲空!
只是那人反應也快的很,轉了個便要去拉采菀。
這時便聽「嗖啪!——嘩啦啦」,勁風呼嘯,一條銀閃耀的九節鞭竟從另一個方向攻向那大個子!
Advertisement
如姒和采菀愕然過去,銀閃耀,英姿颯颯,然而並不是燕萱,而是一個從沒見過的英氣。
這一緩之間,陳濯已經趕到,見那與那人纏鬥,竟怔了一瞬:「音兒?」
?
認識的?
如姒不由皺起眉頭,陳大警草,你每次都是跟一起聯手抓人哦!
「濯哥哥!」那顯然對武功很有自信,形翻飛便如花蝴蝶一般,纏鬥之中還帶著笑音了一聲。
陳濯那發怔也不過一瞬之間,幾乎是話音出口的同時便加戰團。
於是三生有幸的如姒帶著非常不同的心再次圍觀了一場大盛警匪現場格鬥戲。
只不過這次,一點也沒覺得這場打戲彩。目幾乎一直跟著那,看年紀大概十五六?白裡紅,段健修長,一看便是常年運好的妹子。柳葉眉,圓圓臉,雖然算不得什麼絕麗人,卻也是青春風華一枚。
為什麼會武功的妹子看起來這麼酷炫!
為什麼似乎跟陳濯很又很配的樣子!
又看了兩眼陳濯,幾日不見,難道這傢伙又變帥了麼?
不是之前見過幾次的海青公差服,而是一襲蟹青細布長衫。也沒戴帽,而是簡單的男子發冠,卻顯得愈髮鬢若刀裁,劍眉星目。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白襯衫理論,淺服檢驗男神麼?
如姒正在這邊胡思想,適才那些落後幾步的公差捕快們終於趕到了。而那人已經被陳濯和那一同制服,餘下的公差便上前給那人帶鐐銬枷鎖,又向陳濯道謝:「陳捕頭,今日不當班也勞你抓人,多謝了!」
陳濯微微頷首,帶了些笑容便更顯得俊無儔,向自己旁那指了指:「多謝柳小姐才是。」
Advertisement
有捕快聞言便認出來:「哦,這位是刑部柳大人的千金?失敬失敬,多謝柳小姐。柳小姐果然好手!」
那姓柳的抿笑道:「我的手哪裡比得上濯師兄。你們太客氣了。」
居然還是師兄師妹?
眼看著這個警匪作片有轉向港式警匪言橋段的意思,早已經扶著采菀站起來的如姒只覺得心頭無名火起,撇了撇,轉便走。
走出去十幾步,一陣清風拂過,如姒因著剛才被嚇出了不冷汗,額上和背上就都有些涼津津的。想拿帕子,一卻發現找不到。估著是剛才掉了,用手背蹭了蹭額角便想轉去找。
「是在找這個?」
一個頎長拔的影竟然就在三步開外,修長掌中赫然便托著那一方綉了葦紋樣的帕。
如姒一抬頭,對上陳濯那張有點帥出新高度的英俊臉孔,心裡先是一跳,隨即餘便掃見陳濯後不遠的柳氏英氣,眸子里又黯淡下來。
如姒垂了眼皮,手將自己的帕子拿回來:「多謝陳捕頭。」
陳濯見臉一時一變,此刻顯然又不高興了,心裡便微微一,和聲探詢:「可是又出了什麼事?家裡的事還是不順利麼?」
如姒一怔,復又抬眼去看他,瞬間就有點發獃。
砰砰,砰砰,砰砰,如姒覺得好像能聽見自己心跳了。
該死的,這傢伙為說話和眼神都這麼溫啊!
「咳咳,師兄,這位是?」
如姒也不知道柳氏這個時候的話是不是好時機,趕低了頭,讓自己好像有點發燙的臉龐緩一緩。
不知道為什麼,剛才心裡那點莫名的複雜緒好像融掉了。
「這位,」陳濯頓了頓,「是家母的朋友,濮姑娘。濮姑娘,這是刑部副捕頭柳大人的千金,柳小姐。」
「我柳澄音,」大大方方地自我介紹了一下,「濮小姐好。這是來買東西的?」
如姒緩了緩緒,重新抬頭過去,出一個同樣燦爛的笑容:「柳小姐好。我是要去探陳夫人的。」
刺啦啦,刺啦啦。
如姒覺跟柳澄音的這一個微笑照面之中,好像都能聽見電流聲了。
「這麼巧?」柳澄音揚眉一笑,「我也是呢,那濮小姐剛好跟『我們』一路。」
我們?
如姒笑容不變,看了一眼陳濯。
陳濯角浮起一極為淺淡的笑意,目溫厚依舊:「可坐了馬車?走過去會不會太累?」
如姒搖搖頭:「不妨事。」這次的笑容里,卻又不同了。
一路走過去的氣氛很奇異,柳澄音有一搭沒一搭地對如姒問東問西,在采菀聽起來實在是厲害的很,刑部副總捕頭的兒果然是承廷教,很會旁敲側擊地探問祖宗十八代。
然而看了無數古今中外罪案劇的如姒哪裡會怕這個小丫頭!
十五六的啊,那就是高一啊,還能聰明過工藤新一?
每一個問題在如姒看來都是清澈見底,說來說去都可以翻譯總結一句話:你這個不知道從哪裡來的狐貍跟我親的師兄濯哥哥到底是什麼關係?
對此如姒只有一個萬能回答:呵呵。
猜你喜歡
-
完結97 章

廢後謀
那年,看見他,仿佛就已經中了她的毒,日日思念不得見,最後她嫁給了他的兄弟,他只望她能幸福,哪成想,她的夫君一登基,就將她打入皇陵守孝,既然如此,他不會在放過與她相守的每一個機會了,就算全天下人反對,又如何,他只要她。
17.4萬字8 9475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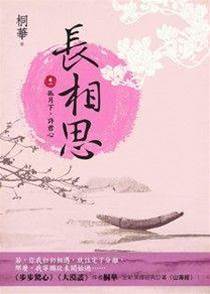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09 -
完結353 章

嫁給白月光的宿敵之后
蘇明嫵本該嫁進東宮,和青梅竹馬的太子舉案齊眉,然而花轎交錯,她被擡進了同日成婚的雍涼王府中。 恨了符欒半輩子,住在王府偏院瓦房,死前才知策劃錯嫁的人是她的心頭硃砂白月光。 一朝重生,蘇明嫵重生在了洞房翌日。好巧不巧,她正以死相逼,要喝避子湯藥... 天子幼弟符欒,十四歲前往涼州封地,十六歲親自出徵北羌,次年得勝被流箭射穿左眼。這樣心狠的大人物,大家心照不宣,蘇明嫵這朵嬌花落入他的手裏,怕是要被磋磨成玩物不止。 尤其是這個美嬌娥,心裏還掛念着她的小情郎,哪有男人能忍得? 雍涼王聞此傳言,似笑非笑點了點頭,好巧,他深以爲然。 婚後滿月歸寧那日,經過樓閣轉角。 “嬌嬌,與母親講,王爺他到底待你如何?可曾欺負你?” 符欒停下腳步,右邊長眸慵懶地掃過去,他的小嬌妻雙頰酡紅,如塊溫香軟玉,正細聲細氣寬慰道:“母親,我是他的人,他幹嘛欺負我呀...” 她是他的人,所以後來,符欒牽着她一起走上至高無上的位置。
53.8萬字8.18 5657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