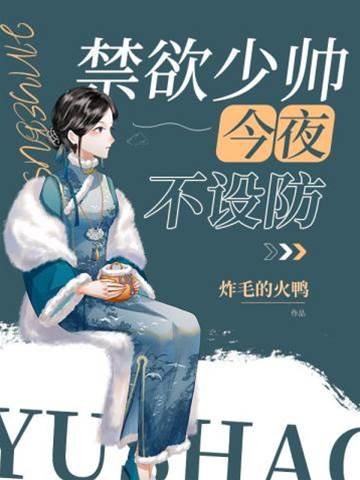《冷梟的專屬寶貝》 第68章 我今晚沒空
"那爺什麼時候回來?"想,趁著爺還沒有回來的時候,去和振宇哥說最後的一番話,一定會好好地保護他最後的東西!
夏清淺下樓之後,剛要出門,便被從廚房出來的權伯住了,"小淺,你這是要去哪裡啊?晚餐都準備好了。"
"權伯,你和瑪麗婭慢慢吃吧,我有事先出去了。"夏清淺說完就要邁出腳步了,可是走到門口的時候,門被打開了。
凝眉往後退了兩步子,爺和夜風都出去了,不會這麼快就回來了吧?
果然,門被緩緩打開,先進來的是穿筆西裝的北堂曜,他那黑黝深邃的雙眸,折出淡淡的芒,輕落在夏清淺的上。
甚打扮的夏清淺,化了一個淡妝,緻麗的五此刻顯得更加俗迷人,一頭黑髮直瀉兩肩,黑的針織開衫,既休閒又舒適,將那白的襯托如雪。
搭一件翻領襯,更顯溫文爾雅,低調的淺給帶來了完的淑氣息,明黃的腰帶將那纖瘦的影勾勒得更加勻稱好看。
看到的妝容,他的臉更是黑沉,顰眉沉聲問道,"你這是想去哪啊?"
不用問阿貴,都知道去看喬振宇了,他的心像是被什麼堵住一般,越發的沉悶。
"我先走了。"淡淡地說著,要奪門而去,誰料到,經過他邊的時候,的荑,被他地一握,力道之大。
"今晚有個晚會,你陪我去。"他清冷的語氣,不自覺的說出。不知道自己說出了這個邀請,選擇黑夜進墓園守著喬振宇,還是選擇跟著他走。
他心裡當然是希放下喬振宇,跟著他走。
Advertisement
"你邊並不缺人,且……我今晚沒空。"試圖掙扎著,卻未料到,愈是掙扎,他箍得愈。
"墓園已經過了拜祭的時間,你去了也是徒然。"北堂曜抑著心中的那氣,這個笨蛋,居然還想著夜晚拜祭喬振宇?一個死去的人,在的心目中真的那麼重要嗎?居然爲了喬振宇,將自己打扮了一番,他還從未見過願意爲他化一次妝。
夏清淺手一頓,微微著夜風,沒想到夜風也是點頭,才放棄去墓園的念頭,心裡一陣陣的失落。
北堂曜看了一眼,示意他將手中的東西遞給夏清淺。
"夏小姐,這是你今晚的禮服。"夜風將一個大大的禮盒遞給了夏清淺。
夏清淺目呆滯地看著禮盒,臉上的神也是淡淡的,順著北堂曜的意思,將那禮盒接過,然後回到了房間,把禮服穿上。
"夏小姐,您真!"傭人走過去,給夏清淺整理整理了禮服,讚歎道。
"謝謝。"夏清淺角兒微微翕著,而後走到北堂曜的跟前,仰起頭看著他,"那請問,我們什麼時候走?"
淡淡的語氣,更讓北堂曜莫名的生怒,吼道,"很委屈你是嗎?去不了墓園你至於這樣子嗎?你說我不懂得,那你呢?"
夏清淺怔怔,被北堂曜那盛氣凌人的氣息嚇得連連往後退著,一瞬不一瞬地注視著北堂曜。
北堂曜也往前走兩步,聲音依然是那麼清冷,"你還不是一樣活在過去,喬振宇已經泥土裡睡了四年了,四年了!你以爲你每天去看他,守著他,他就不會從地上爬起來了嗎?他不是吸鬼,他永遠都不會在存在了,他已經死了!"
Advertisement
他一定要將這個人從幻覺中拉出來,看著一副死氣沉沉,心裡好像只裝著一個死人的樣子,他的氣不打一出!他真的不敢保證,回去之後,真的會將全心投到工作之中?別忘了,可是他的人,腦子裡,誰也不可以裝,只可以裝著他一個人!
"不!"夏清淺輕眨雙眼,微長的眼睫也微微輕著,臉上一陣煞白,不可置信地搖頭道,"不會的,振宇哥還在,我依然覺到他的氣息,他不會離開我的。"
是的,喬振宇怎麼會捨得離開呢?他說過,一定會給幸福的,的幸福還未兌現,怎麼會可以將拋棄了呢?怎麼回呢?
振宇哥不是還留著一顆心臟陪著嗎?還有振宇哥的心,要努力尋找屬於自己的心,要找到一顆可以讓流淚的心。
北堂曜魯地抓住的雙肩,搖著的子,"你醒醒吧!昨天你不是很會說話的嗎?你是很牙尖利的嗎?怎麼別人一說到你的痛,你就畏了呢?原以爲你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沒想到……"北堂曜冷哼一聲,戲謔地說道,"還不是如此,你也只是一個可憐蟲罷了!"
他沉了半晌,凝視著夏清淺的眼睛,改了口吻,很輕,"笨蛋!你不是說了,曾經真正擁有過的,在心裡形完而抹不去的回憶嗎?"
夜風屏住呼吸,眼前一亮,爺將夏清淺的話記在了心裡?哎!都怪自己大,把一些不該說的都說出來,那爺應該也記住了夏清淺說他是混蛋的話吧……?
而夏清淺也甚是詫異北堂曜突然的轉變,眼眶泛酸,有種想要狠狠地抱住北堂曜,然後將臉在他的前,聽著那強有力的心跳聲。
Advertisement
"我命令你,馬上將以前關於的一切回憶,從你的記憶中刪除!一點兒也不允許你留下!"北堂曜不想自己在氣勢上輸了,那張剛溫和沒十秒的臉又變回了一貫的冷清。
在場的人更是驚愕,都以爲爺轉變了格,沒有想到,還沒到半刻,立刻又恢復了那張千年不變的冰雕,又冷又酷,真想讓人點火燒一把,讓那座冰雕融化了。
"憑什麼?"夏清淺又是在挑戰著北堂曜的底線,誰人都知道,北堂曜晴不定,孤傲清高,別人只要照做便是了,哪裡還有那麼多問題?
北堂曜抓住夏清淺雙肩的手,稍微用力,彼此聽到了在那雙大手下的骨頭,咯咯作響,夏清淺更是痛得咬牙,臉慘白。
剪眸中驀然涌起了兩簇微弱的火焰,北堂曜看在眼裡,片刻後纔將放開。
"你若是想喬振宇走的不安心的話,你儘管一廂願地做著一些記著一些無謂的東西,我會讓你嘗試一下痛苦的滋味。"他說著的時候,滿眼都溢著狠戾之,但是被他垂下來的眼瞼遮住了,沒有人看到,連夏清淺也錯過了那一抹強有殺傷力的狠戾。
如果被看到了,一定不會說出下面的話,"北堂曜,在這三年裡,你可以任意地折磨我,但是你無權干涉我的思想!"的手,微微收,了一個小拳頭。
知道,只要今晚一過去,就會遭到用無境止地辱、折磨。但,現在沒有必要他的窩囊氣,是有格的人,在不是他掌控的況下,任由他騎在的頭上呢?
雖然出卑微,但是現在不是封建社會,現在是法治社會,北堂曜縱使是全球首富,他也必須遵守法律,尊重人權!
Advertisement
"我就是權力,你說我還有沒有權力干涉你的一切?夏清淺,你別忘了,你若是敢逆我的意思,我讓你逆天生長!"從北堂曜的齒間出了冰冷而駭人的聲音。
靜默。
就連空氣也凝結了,沒有人敢說一句話,全都將視線落在北堂曜與夏清淺兩個對峙著的人上。
夏清淺嚇得全渾然輕著,脣瓣微微翕著,"我從未想過要逆你的意思,但是也請你弄清楚,現在是我的自由時間,請你不要太過分了!"還逆天生長,他還真的當自己是變形金剛啊?!
牙尖利啊,他暴出了這麼森的一面,不但沒有退,居然還敢頂撞回去,果真是好樣兒的啊!
北堂曜被夏清淺那頑固不冥的格氣得牙狠狠,正在暗暗地磨牙呢。
他怎麼就攤上了一個這麼不聽話的人兒呢?渾是刺,一次又一次變著法子刺傷著他,弄得他渾傷痕累累。
"那你現在馬上給我去將餐桌上的燕菜粥全喝了,免得今晚在晚會上捱,說我沒人道,不給你飯吃!"北堂曜氣得髮指,出巍巍的手指,指著準備好的晚餐。
"我沒胃口,也不!"夏清淺皺眉看著發怒的北堂曜,其實的心裡也正在衍生著一一的害怕。
沒胃口?不?這個笨蛋!都在牀上躺了一天了,說沒胃口就算了,居然說不!以爲是金剛啊,不用進食啊?他現在是關心的子好不好啊,居然不領。
在他發怒的前一刻的時候,權伯走了過來,擺擺手道,"飯菜都涼了,都去吃飯吧,吃完了高高興興地去參加晚會吧。"
權伯的年紀大了,作爲晚輩,多都會給幾分敬意,也不吵鬧了。
先是北堂曜轉便上了樓,夏清淺被權伯請到了飯桌前,乖乖地喝著燕菜粥,這麼高級奢侈的食,一輩子也不敢奢過,自從被北堂曜‘買‘去之後,他雖然總是無時無刻地折磨,但是在食住行上,著的都是這個世界最頂尖最昂貴最舒適的。
靜下心來,發現自己這些日子,確實是過分了些許,只要一對上北堂曜那張臭烘烘、冷邦邦的臉,都會莫名地想要將他的零件拆下來,重新組裝。
可是,不能,也不敢,只要他一說出一些冷嘲熱諷的話兒時,都想要去維護著自己的尊嚴,要讓北堂曜知道,並不是那種沒有格的子,不是弱的。
"丫頭啊,看得出,爺的心裡是有你的,你也不要和爺慪氣了,對彼此都不好。"權伯站在一旁,支著柺杖,"丫頭,人走了,你要放得下,何況,他也不希看到你這樣,你還年輕,目要往前看,別往回頭,懂嗎?"
猜你喜歡
-
完結558 章

隱婚老公太神秘
傳聞榮家二少天生殘疾,奇醜無比,無人願嫁,所以花重金娶她進門。而結婚兩年她都未成見過自己的丈夫,還遭人陷害與商界奇才宋臨南有了糾葛。她陷入自責中,宋臨南卻對她窮追不捨,還以此威脅她離婚。她逃,他追;她誠惶誠恐,他樂在其中。直到她發現,自己的殘疾丈夫和宋臨南竟是同一人……輿論、欺騙、陰謀讓這段婚姻走到了儘頭。四年後,一個酷似他的小男孩找他談判:“這位大叔,追我媽的人排到國外了,但你要是資金到位的話,我可以幫你插個隊。”他這才知道,什麼叫做“坑爹”。
98.8萬字8 106431 -
完結10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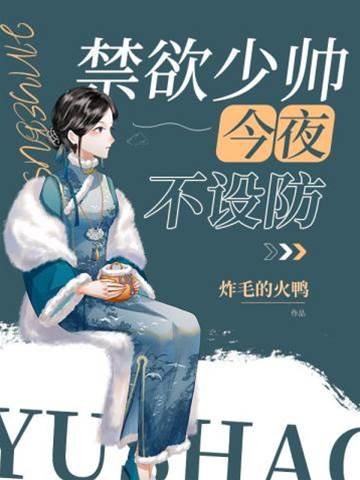
禁欲少帥今夜不設防
一朝身死,她被家人斷開屍骨,抽幹鮮血,還被用符紙鎮壓,無法投胎轉世。她原以為自己會一直作為魂魄遊蕩下去,沒想到她曾經最害怕的男人會將她屍骨挖出,小心珍藏。他散盡家財保她屍身不腐;他與她拜堂成親日日相對;直到有一天,他誤信讒言,剔骨削肉,為她而死。……所幸老天待她不薄,她重活一世,卷土而來,與鬼崽崽結下血契,得到了斬天滅地的力量。她奪家產、鬥惡母、賺大錢,還要保護那個對她至死不渝的愛人。而那個上輩子手段狠戾,殺伐果決的少帥,現在卻夜夜將她摟在懷中,低聲呢喃:“太太救了我,我無以為報,隻能以身相許了。”
193.2萬字8 20524 -
完結141 章

錯嫁瘋批老公後,我直接帶球死遁
夏鳶穿進一本瘋批文,成爲了下場悽慘的惡毒女配,只有抱緊瘋批男主的大腿才能苟活。 系統:“攻略瘋批男主,你就能回家!”夏鳶笑容乖巧:“我會讓瘋批男主成爲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瘋批男主手焊金絲籠。 夏鳶:“金閃閃的好漂亮,你昨天給我買的小鈴鐺可以掛上去嗎?”她鑽進去一秒入睡,愛得不行。 瘋批男主默默拆掉金絲籠,佔有慾十足抱着她哄睡。瘋批男主送給她安裝了追蹤器的手錶。 夏鳶:“你怎麼知道我缺手錶?”她二十四小時戴在手上,瘋批男主偷偷扔掉了手錶,罵它不要碧蓮。 當夏鳶拿下瘋批男主後,系統發出尖銳的爆鳴聲:“宿主,你攻略錯人了!”夏鳶摸了摸鼓起的孕肚:要不……帶球死遁?
26萬字8.18 283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