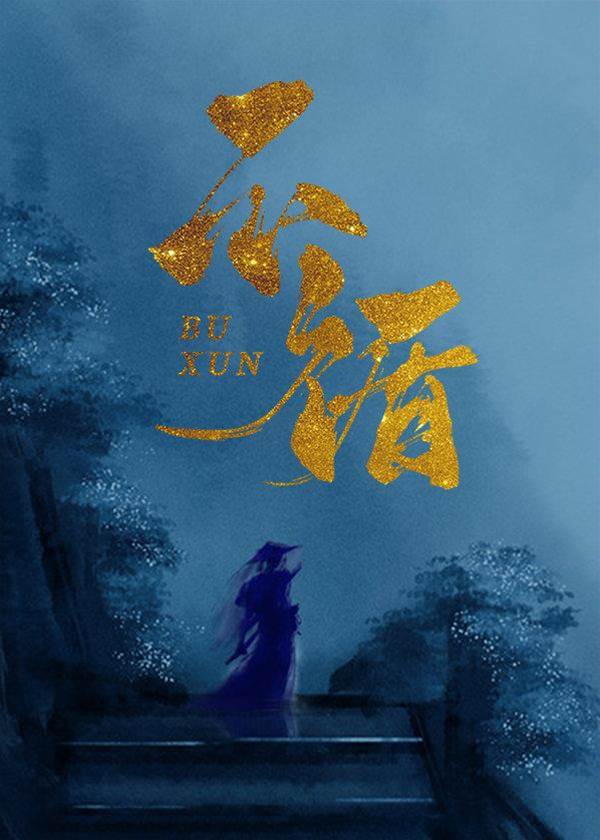《攝政王的嬌寵王妃醒來了》 第52章 遇襲
正在吃飯聊天的賓客們聞聲,紛紛朝戲臺上看過來,只見一個年輕的艷子正對著臺下泫然泣,惹人憐惜。
陳揚和鴻鵠聞聲,忽變了臉,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又不能發作,只能聽聽到底想說什麼。
「冰兒姑娘,你有什麼冤不如明日到本的府衙去鳴冤,本為你做主。」京兆尹大人葉貴先開口了。
這上京城的治安都是他的份之事。
一旁的葉夫人不悅地拉了拉葉貴的手,「老爺,您也不聽聽所為何事就誇下海口?」
這個歌姬選擇此種場合鳴冤,想必不是普通的冤。
「多謝這位大人和夫人垂問,」冰姬朝著葉貴夫婦磕了個頭,「冰兒要告永昌候陳揚他始終棄,明明許了妾夫人之位,可冰兒今日才知道……他竟有一位如花似玉的未婚妻!還騙冰兒來他的定親宴上唱曲兒……」
戲臺下的眾人開始頭接耳,原來是這位俊俏的永昌侯惹來的風流債,對人家唱曲兒的小姑娘瞎許諾不說,還騙人家來他的定親宴上唱曲兒,實在是太不厚道了。
眾人議論了一會兒,又紛紛不做聲,只靜靜等著看這位永昌候如何理。
「冰兒!」灰錦袍的男子氣憤地站起,月下長玉立,聲音卻焦急不安,「你我的事以後再說,今日當著諸位大人,你胡說些什麼?」
Advertisement
一旁的紅早已雙目圓睜,袖中的手指指甲扣在中,顯然是了殺心。
「誒,侯爺,」一位花白鬍子的錦袍老頭站起,看上去德高重,「這就是你的不對了啊,男人逢場作戲本來沒有什麼,可你也不能胡地許了人家夫人之位。」
「張尚書,長生沒有……」陳揚一時語塞,覺得腦瓜子被什麼叮了一下似的嗡嗡響個不停。
「長生,你也別推,今日當著大家的面,不如就說清楚,你到底能不能給人家夫人之位?」張尚書手心向下,做了一個安的作,示意陳揚坐下。
鴻鵠就在旁邊,陳揚自然是不能說什麼,只能朝著臺上的歌姬作揖道,「冰兒,此事算我不對。若是在下從前有什麼讓你誤會的地方,在此向你賠罪了,至於永昌候夫人之位,已經另有所屬。」
「好了好了,」張尚書捋著鬍鬚,趕打圓場道,「冰兒姑娘,既然侯爺已經向你賠罪了,你今日若是給老朽一個面子,此事就作罷吧。」
坐在後排的一位藍袍男子此時不耐煩地「嗤」了一聲,又翹起二郎。
最近這上京城的奇葩事太多了,程謙今日本來不想來赴宴,可為了追查一個邪祟的案子,追到了永昌候府附近,順道就進來看看,沒想到邪祟沒抓到,倒是看了一場好戲。
Advertisement
冰姬向張尚書點點頭,又委屈地朝眾人作揖道,「冰兒也並非要胡攪蠻纏,既然侯爺如此說,從此你我分道揚鑣、再無瓜葛。不過……冰兒本以為從此可以做永昌侯夫人,將妙音樓的差事也給辭了,如今奴一個弱子,連回鄉的盤纏都沒有……」
這是打算訛錢了。
「你!」鴻鵠忽然指著臺上,手中一道白暴怒而起,飛向戲臺上的子。
眾人還沒看清那是什麼,只聽見「嘭」得一聲,臺上的木地板發出一聲悶響。
冰兒嚇得哭了起來,卻是毫髮無傷。
「夫人息怒,冰兒惹了夫人生氣是冰兒不對,可也是侯爺他先招惹了奴家。」冰兒一邊朝鴻鵠賠禮,一邊幽怨地看了一眼陳揚。
灰錦袍的男子此刻正盯著簾后那個影看,腦中一片混。
他原本的猜測是攝政王妃對自己一見鍾,又不好意思直接來找自己,便趁著攝政王不在上京,扮作樂師進永昌候府……
按理說應該讓這歌姬離間了自己與鴻鵠,然後趁著夜替換了那歌姬爬上自己的睡榻才對,怎麼事的發展卻與預想的不太一樣?這位攝政王妃砸了永昌候府的名聲,難道就沒有下文?到底意何為?
陳揚心中暗暗思忖,王妃定是對自己因生恨,求而不得失了理智,下回自己只要再主一些,定會投懷送抱。
Advertisement
「鴻鵠姑娘,」鴻鵠與陳揚還未婚,葉貴的夫人便稱「鴻鵠姑娘」,「此事的確是侯爺欺騙人家在先,不止欺騙人家的,還讓人家來給咱們大家唱曲兒,這是利用了人家的啊,換誰心裏都不好!」
顯然是責怪鴻鵠剛才那一擊暗,雖然沒看清是什麼,但是眾人猜測是這位永昌候的未婚妻往臺上丟了個石子或是飛鏢之類的東西,想殺人滅口。
鴻鵠心裏火冒三丈,又不好發作,事已至此,只好沉聲道,「冰兒姑娘開個價吧!」
冰姬聞言,迅速用袖拭了一下眼角的淚珠,出兩隻蔥白手指,「不多,二十……金。」
「二十金?!」紅氣得要炸。
永昌候府本就是個空殼,潯城中還有一家窮親戚要養,陳揚來了上京更是花費巨大,二十金能抵得上他們幾個月的花銷了。
鴻鵠平時自己省吃儉用,這歌姬不過來唱了幾首小曲兒,開口就要二十金?
「鴻鵠……」陳揚想著息事寧人,在桌子下面拉了拉鴻鵠。
「別拉我!」鴻鵠氣憤地一振袖,瞪著那俊朗男子,眼神像要殺人。
「鴻鵠,我……」陳揚也沒想到事變這樣,一時不知該怎麼辦。
卻聽見後排一人冷笑道,「冰兒姑娘,你好大的口氣,你可知道二十金能買你唱多曲兒?」
Advertisement
趙霜輕輕撥簾一看,正是那個哪兒都一腳的衛尉卿程謙。
聽了藍袍男子的話,冰姬心裏「咯噔」一下。
若按上京的行,不算打賞,就算是自己最當紅的時候,一個月的收也不到二兩金子。二十兩金子能讓從早唱到晚,整整唱上一個月。
「這位公子可曾聽說過『義無價』?我們冰兒姑娘被人利用了,怎麼二十兩金子還嫌貴?」趙霜抱著木琴從簾後走出來,扶著冰姬起,「你們這些貴人仗勢欺人,若是不給,我們明日就公堂上見。」
陳揚仔細打量了一眼,雖然喬裝過,可他應該不會看錯,就是攝政王妃。不知怎麼,他忽然覺得心跳有些快。
猜你喜歡
-
完結1354 章

神醫嬌媳:寵妻狂魔山里漢
“美男,江湖救急,從了我吧!”情勢所迫,她反推了隔壁村最俊的男人。 ……穿越成小農女,長得有點醜,名聲有點差。她上山下田,種瓜種豆,牽姻緣,渡生死,努力積攢著功德點。卻不想,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勾走了她的心,勾走了她的身,最後還種出了一堆小包砸!
115.2萬字7.82 116552 -
完結789 章

重生王妃又闖禍了
“王爺!王妃把皇後打了!”男人冷眼微瞇,危險釋放,“都是死人?王妃的手不疼?”家丁傻眼,啥……意思,讓他打?“王爺,王妃把宮牆城門砸了!”某男批閱摺子動作不停,“由她去,保護好王妃。”“王爺,王妃被抓了!”“好大的狗膽!”屋內冷風四起,再睜眼,某王爺已消失在原地。自那之後,某妃心痛反省,看著某男因自己重傷,她淚眼婆娑保證,“夫君我錯了,下次絕對不會這樣。”然——好景不長。“王爺,本宮又闖禍了!”
138.1萬字7 263863 -
連載1606 章

有了讀心術後王爺每天都在攻略醫妃
21世紀醫毒雙絕的秦野穿成又醜又不受寵的辰王妃,畢生所願隻有一個:和離! 側妃獻媚,她各種爭寵,內心:我要噁心死你,快休了我! 辰王生病,她表麵醫人,內心:我一把藥毒的你半身不遂! 辰王被害,她表麵著急,內心:求皇帝下旨,將這男人的狗頭剁下來! 聽到她所有心聲的辰王憤恨抓狂,一推二撲進被窩,咬牙切齒:“愛妃,該歇息了!” 半年後,她看著自己圓滾滾的肚子,無語痛哭:“求上天開眼,讓狗男人精儘人亡!”
146.5萬字8 840282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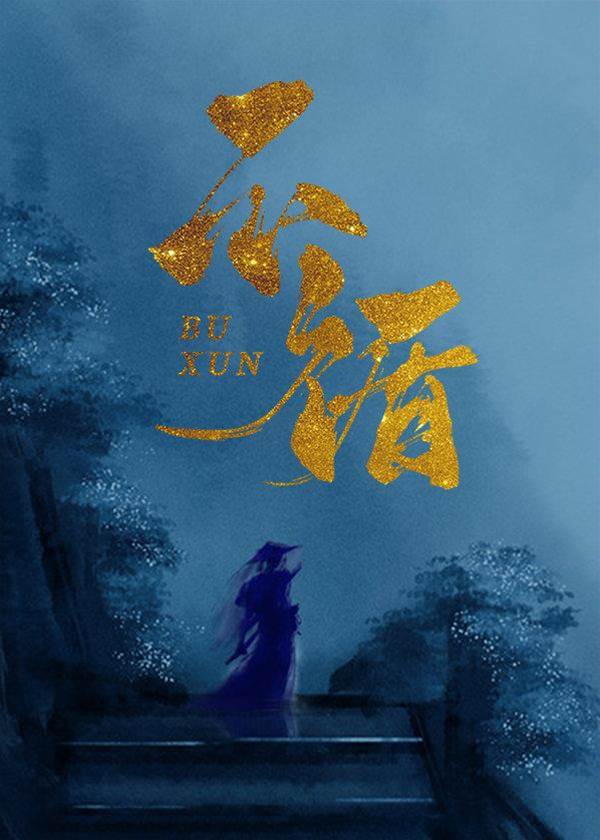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45844 -
完結137 章

招魂
-落魄的閨閣小姐X死去的少年將軍-從五陵年少到叛國佞臣,徐鶴雪一生之罪惡罄竹難書。即便他已服罪身死十五年,大齊市井之間也仍有人談論他的舊聞,唾棄他的惡行。倪素從沒想過,徐鶴雪死去的第十五年,她會在茫茫雪野裡遇見他。沒有傳聞中那般凶神惡煞,更不是身長數丈,青面獠牙。他身上穿著她方才燒成灰燼的那件玄黑氅衣,提著一盞孤燈,風不動衣,雪不落肩,赤足走到她的面前:“你是誰?”倪素無數次後悔,如果早知那件衣裳是給徐鶴雪的,她一定不會燃起那盆火。可是後來,兄長失踪,宅田被佔,倪素跌落塵泥,最為狼狽不堪之時,身邊也只有孤魂徐鶴雪相伴。 伴她咬牙從泥濘里站起身,挺直腰,尋兄長,討公道。伴她雨雪,冬與春。倪素心願得償,與徐鶴雪分道揚鑣的那日,她身披嫁衣將要嫁給一位家世,姿儀,氣度都很好的求娶者。然而當夜,孤魂徐鶴雪坐在滿是霜華的樹蔭裡,看見那個一身紅的姑娘抱了滿懷的香燭不畏風雪跑來。“不成親了?”“要的。”徐鶴雪繃緊下頜,側過臉不欲再與她說話。然而樹下的姑娘仰望著他,沾了滿鬢雪水:“徐鶴雪,我有很多香燭,我可以養你很久,也不懼人鬼殊途,我們就如此一生,好不好?”——寒衣招魂,共我一生。 是救贖文,he。
50.1萬字8 2237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