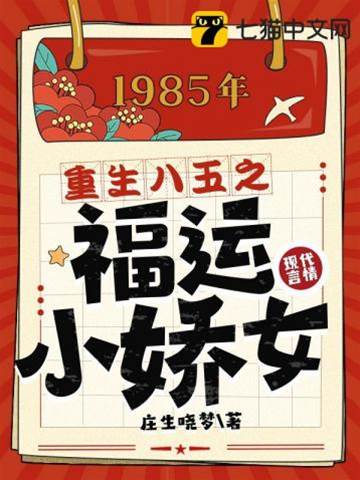《婚色幾許:陸先生入戲太深》 第96章 這是我太太
章志的兒雖然心氣高,長期在外面上學的緣故,比當地的同齡孩子更有主見,可畢竟也只是二十來歲的稚年紀,又在父母疼的健全家庭里長大,沒什麼心眼兒,哪裏能跟陸淮深這種在謀略上造詣頗深的人比較?
見陸淮深依然從容沉著,小姑娘氣得不行,不懼那人的目,指著他恨恨地說:「你怎麼說話不算話呢?」
陸淮深攤手:「我什麼時候說話不算話了?你給的信息太,我們無從下手。」
「你還想知道什麼?如果你們得到了你們想要的東西,拍拍手走人,我和我媽怎麼辦?」章志的兒學以致用,用陸淮深方才的話堵他。
確實走投無路了,那個電話里的人,打電話來威脅們閉,大伯又威脅們給錢,這麼下去,們錢也沒了,還有人危險,讓們母怎麼過呢?
那些人長期遊離在法律的邊緣,不怕死,不要命。
讓們這種普通人怎麼拿命去搏?
「不算笨,」陸淮深也不知是讚許還是諷刺,「你的目的是,想我們手讓你的大伯一分錢都拿不到,還能保證你們家的不泄,讓你媽不威脅。但這兩者之間本來就是悖論,我們要的,就是你們家的。」
小姑娘著,看向別,低聲道:「跟我們又沒關係,他死了都死了,現在我們國家又不興連坐制度。」說完又看向陸淮深:「我爸真正做過什麼事,我不清楚,我媽都是在我爸去世前兩天才知道,也不告訴我。但經常聯繫我爸的那個人肯定清楚。」
「聯繫你爸的人?」
「也是這幾天威脅我媽的人,如果告訴了你們想知道的,他們會報復的!」
江偌瞬間的覺彷彿撥開迷霧見青天,高隨也說過,江渭銘和江覲不會直接跟章志聯繫,一定有一個或多個替他們做事的中間人。
Advertisement
章志的兒所說的聯繫父親的那個人,有很大可能就是要找的和江覲有直接聯繫的人。
一開始來找章志的目的,就是為此!
陸淮深巋然不,看向那孩兒,「你怎麼就確定我們能幫上你?」
章志的兒雖然心繫母親那邊的況,仍然回答著陸淮深的問題:「不確定,猜的而已。那些人能給我爸那麼多錢,恩威並施,將我爸吃的死死的,來頭肯定不小,而你現在讓他們急得像熱鍋螞蟻,就像老鼠見了貓,就要自陣腳了,說明你至也是跟他們一個級別的人。」
「不錯,思路清晰。」陸淮深說完看向江偌,「你怎麼看?」
見陸淮深遲遲不給話,急之下道:「你可真是墨跡,這點事還要問這人,有沒有主見了?」
江偌心裏直詫異,看人下菜碟這話準沒錯,柿子撿的,大找的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兩人之間誰更有本事。
陸淮深倏然一笑,語氣有點兒涼,「怎麼,你瞧不起,還是瞧不起人?」
章志的兒梗著脖子犟道:「我可沒這意思,但是能拿主意麼?」
陸淮深告訴:「那你覺得這樣行不行,不答應,我就不幫。」
「你……」
江偌也不知道為什麼挑這種時候護的面子,心裏既彆扭又激,雖不知他是真還是假意,心意領了,拉拉他袖子說:「你何必跟一個小孩子計較?」
陸淮深眼神釘在那孩上,「教什麼什麼是尊重,別以為年紀小說話就不用負責不用過腦。」
江偌心想,你哪有資格說教別人?
章志的兒也是能屈能,知道這時候要求人,不能磕,立時就道:「行,我承認我剛才太衝了,說話的方式不對,不尊重人,我向你朋友道歉。」
Advertisement
「這是我太太。」
江偌完全搞不懂陸淮深了……
章志的兒微訝過後,「我向你老婆道歉!」
說著還要朝鞠躬,江偌忙站起來阻止,「不用了。」趕跳過這事,問陸淮深怎麼辦,讓他想想辦法。
……
房間里,章全和章志的妻子萬青吵得不可開。
萬青一口一個無能地,刺激得章全幾次朝手,因為今天有客人在,留下他打這人的痕跡,讓人發現了可不行。於是氣急了便將推倒在地上,反正窗簾拉上的,外面又看不見裏面。
而萬青也害怕別人發現自己的家醜,一直著聲音,章全更是為所為,直接掐住萬青的脖子。
「臭娘們兒,你給不給錢?信不信老子今天在這兒把你幹了,讓別人都來看看你這個剛死了老公就不守婦道的人!」
萬青因脖子被男人的手掐住,不流通,很快臉就漲得通紅,力氣也漸漸流失,驟然聽見這男人口中的污言穢語,突然卯足氣力,一腳往他的關鍵部位踹過去。
章全吃痛,夾,捂著雙手去護痛。
此時此刻,萬青的子會做的事不是逃跑,而是趁機拿起矮柜上的綠蘿盆栽就往章全頭上敲,盆栽的土盆並非土盆,是塑料的,敲在頭上上,不會要人命,但會讓人苦不堪言。
「臭不要臉,這種話你也敢說?你現在是連臉都不要了是吧,老娘今天替你爸媽教你做個人,你這個畜牲不如的!」
章全一開始護下面去了,生生挨了好幾下,下面的痛緩過勁兒來之後,也被打出脾氣,一把將萬青往牆上使勁摜去,失去理智地扯著的頭髮,將的頭使勁往牆上撞。
撞了兩下,萬青已經說不出話來,章全的兒在外面敲門,抖著嗓子說:「我錄音了,你放開我媽,現在就開門,不然我就拿著錄音去公安局,告你蓄意傷人!」
Advertisement
章全心裏一驚,終於恢復了些理智,一把去拉開門,誰知道外頭還站著兩個人,頓時臉都僵了。
陸淮深見他雙眼赤紅眼袋腫大,一副兇神惡煞的樣子,不由一皺眉。
江偌看了都驚了一驚,章全領歪斜,短髮凌,額頭上還有不知道被什麼東西刮傷的痕,模樣狼狽又兇狠。
陸淮深往裏看了眼順著牆壁坐在地上的萬青,對方額頭上還在流。
「非法威脅,搶奪產,蓄意傷人,先不討論夠你喝幾壺的問題,」陸淮深指了指坐在地上的兒,問章全,「如果告你,你有錢打司嗎?」
據章志的兒所說,章全就是個好吃懶做的無業遊民,中年離婚,兒子早年輟學在外打工久不歸家,這個章全連生活都要靠弟弟接濟,那輛大眾帕薩特也是看章志買了車,他眼紅,著章志出錢給他買的。
他哪兒的錢打司?
真面目被穿,章全也不多加掩飾,囂張至極地說:「不敢告我!」
「怎麼就不敢告你了?以為怕你揭發章志生前做過的事?」
萬青原本頭昏腦漲,聽見這話,一個激靈看向陸淮深,又看了看自己的兒,嚨又像被掐住了一般難。
章全凝著濃黑雜眉瞟了眼陸淮深,心說他怎麼知道的?
看了眼侄,瞬間就明白過來了。
章全手握拳頭就想朝侄臉上揮過去,他人高馬大,年輕時又長時間做苦力,那手掌比常人都要更加厚大,一個拳頭比章志兒那張臉的一半還大。
章志的兒在他抬起手的時候,一個閃往陸淮深後藏。
陸淮深說:「章志死都死了,他的所作所為,這對母不承擔任何責任,在他死前,們也毫不知,你揭發也沒用。你雖然是章志的親兄弟,但他沒有立囑,產繼承就得順位,他老婆孩子都在,你沒資格。」
Advertisement
章全咬牙齦,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呼吸促,一勁道集中在手上,揮拳就往陸淮深臉上砸去,還沒到陸淮深分毫就被他一腳踹進了房間了。
章全重重砸在地上,四仰八叉,陸淮深抬腳進了房間,江偌和章志的兒隨起后。
章志的兒反手關上了門,家醜不願外揚。
陸淮深轉轉手腕,垂眸盯著地上那人,「無用莽夫。」
萬青被兒扶起來,重新審視著陸淮深和江偌,忽然分不清對方是敵是友。
「崽崽……」
兒坦白:「是我找他們來的,我跟他們做了換,他們會幫忙,你只用告訴他們威脅你和爸爸的那個人是誰。」
萬青猛地搖頭,「不行!這些人跟黑社會沒什麼兩樣,違背他們的意思,出事了怎麼辦?」
「跟你這種思想局限的人說話就是累,你怎麼就不好好想想,既然他們的出現讓那個人如此張,」章志的兒指向陸淮深和江偌,「他們當然有辦法對付他,難道你要這樣擔驚怕一輩子嗎,這件事總要解決,爸爸都死了,就算幹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我們又不用承擔刑事責任。」
萬青雙目茫然地聽著,開始搖,但是還是說:「不行的……」
兒斥罵道:「懦弱!你想一輩子活在別人的威脅中嗎?我不想!我才二十歲,我的人生還那麼長,」握住母親的手,切切看著:「你難道忍心我今後的生活也如履薄冰,總是擔心什麼時候會被那些人毀掉嗎?我們不能逃避問題,要想辦法解決問題才行啊媽媽。」
猜你喜歡
-
完結80 章
和影帝的新婚日記
喬繪這輩子做過的最瘋狂的事情,就是在二十一歲這年閃婚嫁給了正當紅的影帝徐亦揚。婚後的生活平平淡淡。徐先生每天都會給她早安晚安吻,會在外出拍戲的時候不時向她匯報行程。但即便是最親密的時候,他的吻,也是溫柔內斂又剋製的。喬繪鬱鬱地向好友袒露心聲,“他寵我,就好像寵女兒一樣。”到底,還是差了點什麼。徐亦揚新劇殺青的那天,他和劇中女主演的緋聞喧囂塵上,無數c粉徹夜狂歡。喬繪在床上盤著腿,考慮再三之下,提出了分居的要求。這一晚,徐亦揚冒著臺風天的惡劣天氣連夜從外地趕回,全身濕透,雨水浸的他的眼尾通紅一片,“為什麼?”少女穿著居家的粉色小熊睡衣,小臉嚴肅,“我們咖位差距太大了,沒人會認為我們般配。我想,我們可能不太適合。”第二天,一張照片點爆熱搜。空蕩無人的街頭,向來穩重自持的影帝抱著他的新婚小妻子,吻得纏綿又悱惻。
22.2萬字8.18 18761 -
完結118 章
戒不掉的喜歡
俱樂部裏來了個兼職小醫生,長得漂亮,溫柔細致,還特會哄人。隊裏常有天真少年感歎:“以後,找女朋友就要找應歡這樣的,聽話,乖巧,還會哄人……” 隻有把人撩炸了的徐敬餘知道,應歡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真妖精。 職業拳擊手徐敬餘拿到81公斤級金腰帶後接受采訪,記者問:“聽說您每次賽前一個月為了保存狀態和體力,禁欲禁酒,這是真的嗎?” 徐敬餘臉上掛了彩,眉骨和嘴角滲著血,微笑看著鏡頭:“對。” 那會兒應歡就站在人群開外,一臉冷漠地看著他。 同來比賽現場看比賽的好朋友湊過來,好奇問:“真的假的?荷爾蒙爆棚的敬王
42.3萬字8 14548 -
完結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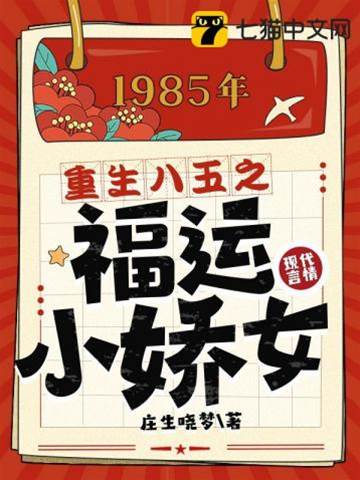
重生八五之福運小嬌女
前世,喬金靈臨死前才知道爸爸死在閨蜜王曉嬌之手! 玉石俱焚,她一朝重生在85年,那年她6歲,還來得及救爸爸...... 這一次,她不再輕信,該打的打,該懟的懟。 福星錦鯉體質,接觸她的人都幸運起來。 而且一個不留神,她就幫著全家走向人生巔峰,當富二代不香嘛? 只是小時候認識的小男孩,長大后老是纏著她。 清泠儒雅的外交官宋益善,指著額頭的疤,輕聲對她說道:“你小時候打的,毀容了,你得負責。 ”
70.5萬字8 19173 -
完結108 章

心動法則
原書名《你有權保持心動》朱珊和鄰居哥哥凌霄在國外登記結婚,此后四年,未聯系一次。為了調查父母當年的案子,朱珊偷偷回國,入職市電視臺成為一名菜鳥記者。朱珊從小討厭害怕凌霄,在得知此時的凌霄是一個風評不好、未有敗績的‘撒旦’律師后,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一起烏龍,朱珊被押去警局接受調查,因此不得不聯系自己名義上的丈夫,凌霄,并與之同住一屋檐下。強奸案,家暴案,殺人案……環環相扣,抽絲剝繭。真相會浮出水面,愛亦如此。我們,都會站在陽光下。記者的存在,以事實為根據,傳達真相,告知真相。律師的存在,不是為了維護正義,而是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心有所信,方能行遠。
32.6萬字8.18 380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