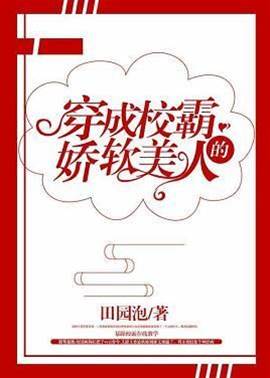《冷少的純情寶貝》 054章 欺負得徹徹底底
驀地,和他的視線在鏡子裡匯了。
手裡的梳子差點掉下來,是秦陸穩穩地握住了的手。
他的聲音有些沙啞,“看來,你還不是很累。”
的臉紅了紅,知道他話裡的深意,但又怕他真的要將弄得更累,只得將目移向他手裡:“買了什麼?”
他舉高手,“一些小吃。”
一些高檔的餐廳都是預訂的,所以這個時候都結束了,他去了一家有名的小吃店,買了些醬鴨掌,又買了幾樣配菜,當然,還有孩子最喜歡的茶。
他放在一旁的一個小餐桌上,然後抱著的子過去。
那潔嚇了一跳,下意識地抱他的頸子:“秦陸,我可以自己過去!”
他沒有說話,只是小心地將的子放到椅子上,然後有些意味深長地說:“累,就不要,不然明天該疼了!”
的臉蛋一下子紅了,當然知道他是什麼意思。
只得埋著頭苦吃,一會兒擡眼,看見他坐著笑地瞧著的小臉,臉一低,“秦陸,你怎麼不吃?”
他笑笑:“我已經飽了!”
有些生氣地將手裡的東西放下,“你不吃我也不吃!”
的小脾氣讓他有些意外,但同時也是愉快的。
他就拿著只剩下的半隻鴨掌啃了起來,就算是最俗的小吃,他吃起來,還是那麼優雅好看。
那潔看了半天,纔想起來,他,他,他竟然吃自己剩下的東西。
呆呆地不說話,他則笑笑地塞了個東西放在的裡,“吃東西,秦太太!”
他這聲秦太太讓紅了臉,低低地說:“媽聽見了,該說你渾了!”
秦太太是的嗎?媽纔是秦太太呢!
Advertisement
秦陸笑,著的小臉,“皮了是啊?都知道討婆婆的歡心了!那好,以後我你!”
他很有這麼貧的時候,但一貧起來,是那潔這樣的小姑娘招架不住的。
只得別過頭,啐了他一句:“我看你,和大牛他們是以類聚!”
他淡笑,只是笑裡藏著一抹不懷好意,指了指桌上,“快吃,吃完了早點睡!我明天部隊裡還有事兒!”
那潔繼續低頭啃,十分鐘後,一堆食兩人解決完了,秦陸將手一洗,替將十蔥花似的手指也得白白嬾嬾的,開始算起帳來。
“剛纔,是誰說我和大牛以類聚來著?”他抱著,來到萬惡的豪華大牀上,但是沒有放下,只是抱著,讓更是心慌。
垂了腦袋,很有眼地老實認錯:“是我說錯話了,行不行?”
唉,都會撒了,是他寵的。
但人,白天撒有用,晚上是不管用的。
“小潔,你說我不幹點和大牛一樣的渾事來,是不是對不起‘以類聚’這四個字啊?”他的手遊移在的小臉蛋上,讓的子都輕了。
抓他的軍服,低低地認著錯:“我錯了,不行嗎?”
都快要哭了,這時,真的覺到有些酸了,而且是那種人的,的疼。
想到他結實的在上的覺,雖然很心安,很舒服,但時間長了,也很重的。
有些委屈地扁起小,這才第二次,他就這麼不知節制,以後,是不是每天都不能睡好覺了。
看著小臉上彩的表演,秦陸失笑著將頭抵在的額頭上。
“你就將我想得那麼壞?”他握著的小手,將放在牀上:“我去洗個澡,你先睡。”
Advertisement
拉住他的手:“不是才洗過嗎?”
說完後,他定定地著,不說話。
那潔過了很久之後才悟了,目往下,爾後明白他爲什麼去洗澡了。
立刻鑽到被子裡,將自己包得嚴嚴實實的。
太丟臉了,竟然…問這麼蠢的問題。
好一會兒,纔敢地出半個臉來,抿著脣-男人的*都是這麼強嗎?
真的不知道,但又不敢問秦陸,生怕他再笑話。
秦陸出來的時候,就看見他的小妻子在牀上睡著了,只是呼吸凌了些,特別是在他躺到邊的時候。
他笑笑,決定不拆穿的小把戲。
手將的小子拉到自己懷裡,因爲吃了些食的原因,的子熱了些,暖洋洋的抱在懷裡好舒服。
秦陸第一次知道,人的子這麼可,加上總共就接過兩次,頭一次還那般劇烈,所以這上手上也沒有捨得停下。
那潔被他弄得快要哭了——想睡覺!
他這麼,哪裡睡得著啊!
秦陸側過子,手上的作沒有停,俊逸的面孔對著紅的臉蛋。
此時,房間裡的燈暈黃暈黃的,在他的面孔拉下一道長長的影,看起來邪魅而英俊得讓心跳加速。
的手攀上他的俊,小心地學著他的樣子輕移著,到他的脣邊時,卻被他突然張一口咬住。
嚇壞了,劇烈地了一下,眼輕擡,裡面是乞求。
秦陸勾脣一笑,“是你自己送上門的,不是嗎?”
嘟著小,不高興了。
秦陸一看,還生上氣了,於是摟著哄,“我不是和你開個玩笑啊?這也生氣?”
不說話,只垂著頭。
Advertisement
秦陸忽然明白了,他傷到了的自尊心了。
說到底,還是介意他們結婚的方式。
他清了清嚨,有些地說:“小潔,如果你總是記得這些,那我們永遠無法像是正常的夫妻那樣相!”
擡眼,怔忡著看著他。
他用了‘永遠’這兩個字——
“永遠,秦陸,我們會永遠在一起嗎?”真的不確定,因爲他的懸殊太大了,走進了秦家,現在覺得像是做了一場夢,而,會隨時從這夢裡醒過來。
他嘆口氣,將的子摟到懷裡,“傻瓜!”
低了頭,吻了吻的額頭,“你是我的救世主,我怎麼可能捨得放開你!”
他偶爾的貧讓不笑了起來,手捶打了他的口一下,忽然想起之前歐安的話來,有些猶豫,不知道該不該問。
但是不問,心裡總是覺得有些悶悶的。
秦陸當然知道的心思,讓平躺在他的手臂上,爾後他著天花板,幽幽地說著:“我和安安自小認識,其實打小的時候,我就發現我和別的孩子不一樣,但那隻限於一般的潔,還沒有到很嚴重的地步。”
他苦笑一聲:“那時,我沒有意識到這會影響到我以後的生活和婚姻,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病越來越重,我想邊的人都察覺了,只是不說出口罷了。”
那潔側著臉,目瞧著他的下,仔細地聽著。
此時,他的面孔因爲不太好的回憶而有些繃,不在被子下面握了他放在小肚子上的手。
秦沛側頭看了一眼,繼續說著:“後來,我和安安了,打小我就喜歡。”
他頓了一下才說:“希我這麼說,你不要介意,因爲那就是我的過去,過去,只能忘記,不能磨滅!”
Advertisement
在他懷裡輕點了下頭,小腦袋依在他的肩上。
秦陸摟著的手了,“和安安在一起,可以說是很開心的,那時是個十分可的姑娘,活潑麗,所有的人都喜歡,但我…”
他的臉上閃過一難堪,“人間不可避免會有接,會有親吻,但是我從來沒有*對這麼做,甚至在吻我的時候,吐了出來。”
那潔察覺到他並不想回憶這段往事,不喃喃地說:“秦陸不要說了,現在不是好了嘛!”
也不明白,爲什麼秦陸好了而沒有和歐安在一起,他們很相配不是嗎?
有些酸地想著。
秦陸哪裡猜不中現在心裡在想什麼,一個翻將到下,就是一陣暴風雨般的狂吻…
鬆開的時候,頭髮散,呼吸急促,小臉著豔麗的緋紅。
他則沒有繼續下去,而是點著的小腦袋,斥責著:“以後再胡想,就家法侍候!”
想起上次他捱了一下那傷口,的小臉一下子變得蒼白,“秦陸,你要用那麼的藤條打我?”
幾下,還不得將活活打死啊!
著他的眼神裡就著害怕的意味來,秦陸哭笑不得——
他都將寵這樣了,就是在歡*的最激烈的時候,他也都是顧及著承不住而沒有敢用全力,這會子,竟然以爲他是個打人的男人。
小丫頭,不開竅,得罰了。
於是湊過臉去,在的耳邊說了幾句渾話。
那潔的臉一下子紅了…天…原來,他說的家法是用那裡打!
“你下流!”一下子埋在被子裡,小臉燙得嚇人,就在他的小腹。
一抹熱氣隨著的靠近而從裡緩緩流淌著,秦陸扯了扯的頭髮,“小潔,出來吧!”
不肯出來,還越鑽越下,他無奈地深吸了口氣,才無力地吐出一句話來:“小潔,你到我的‘家法’了!再不出來,真的要侍候了啊!”
威脅加恐嚇功地嚇住了,驚了一下,立刻像只小兔子一樣跑出來。
臉紅紅的,秦陸瞧著,還是忍不住上前親了一口,將本來就的頭髮得更了些,“傻瓜!”
的心跳得飛快,他這樣,是不是有些喜歡?
擡起眼,又慌地移開。
秦陸笑笑,將拖回原來的位置,重新枕在他的肩上。
“那可不可以繼續講了?”仰起頭,香甜的呼吸就噴在他的頸側,他忽然間,覺得這時候說以前的事,是個特別掃興的事。
於是了的小鼻子,“想聽?”
猛地點頭,毫不覺得這樣子傻了。
唉,孩子還是這樣可些!
秦陸存心逗:“那有什麼獎賞呢?”
睜大眼,據理力爭,“我當你的聽衆,還要獎賞,你太過份了。”
WWW⊙ttκǎ n⊙CΟ
他側過子,似笑非笑地瞧著:“看來,你還是沒有被我迷人的*迷住,腦子還在運轉呢!”
一下子紅著臉,“秦陸,你壞蛋!”
說著,背過去。
秦陸在後面摟著的子,俊臉擱在的頸邊:“我哪壞了?”
說不出來,只得不說話,子也僵著。
他靠得太近,也不敢一下。
秦陸低低地笑著,“小潔,其實呢,男人都是壞的!”
猛地回頭,不敢相信地瞧著他的臉。
他,竟然會這麼說。
而且,秦陸和想象和記憶中的真的不一樣了,他現在就像個十分正常,對於來說,又十分陌生的男人那樣,有些壞,又有些邪氣。
讓招架不住。
畢竟只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對,從來沒有接過,也不太知道怎麼和一個年輕的男相,更何況是直接奔到本磊的男。
垂著臉,不敢看他。
他的聲音此刻人極了,出一隻修的食指勾住的小臉蛋:“小潔,一個男人如果不喜歡一個人,是不會對使壞的,這話,要記住了!”
怔怔地瞧著他的眼,此時,他正專注地瞧著。
一下子被那幽深的眸子吸引住了,不捨得離開。
兩人這麼對視了良久,才吶吶地問:“如果記不住呢?”
秦陸的脣緩緩上揚,然後目變得有些炙熱,“那就,想辦法讓你記得!”
猜你喜歡
-
完結1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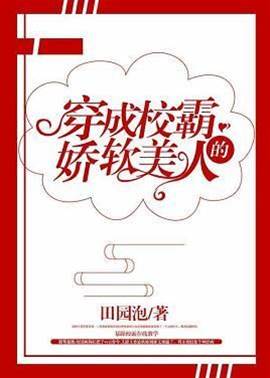
穿成大佬的嬌軟美人
作品簡介: 按照古代賢妻良母、三從四德傳統美德培養出來的小白花蘇綿綿穿越變成了一個女高中生,偶遇大佬同桌。 暴躁大佬在線教學 大佬:「你到底會什麼!」 蘇綿綿:「QAQ略,略通琴棋書畫……」 大佬:「你上的是理科班。」 —————— 剛剛穿越過來沒多久的蘇綿綿面對現代化的魔鬼教學陷入了沉思。 大佬同桌慷慨大方,「要抄不?」 從小就循規蹈矩的蘇綿綿臉紅紅的點頭,開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出格表演。然後全校倒數第一抄了倒數第二的試卷。 後來,羞愧於自己成績的蘇綿綿拿著那個零蛋試卷找大佬假冒簽名。 大佬:「我有什麼好處?」 蘇綿綿拿出了自己覺得唯一擅長的東西,「我給你跳支舞吧。」 ———————— 以前,別人說起陸橫,那可真是人如其名,又狠又橫。現在,大家對其嗤之以鼻孔。 呸,不要臉的玩意。
34.1萬字8 9592 -
連載403 章

時光與你皆傾城
一場錯愛,她忍受四年牢獄之災。四年後,她浴火重生,美得淩厲,發誓要讓他百倍奉還。隨著時間推移,真相一層層析出,當初的背叛,是刻意,還是誤會?他帶給她的,到底是救贖,還是更甚的沉淪……
73.7萬字8 8537 -
完結375 章

怪他過分沉淪
傳聞,蔣蘊做了葉雋三年的金絲雀。傳聞,她十九歲就跟了葉雋,被他調教的又乖又嬌軟。傳聞,葉雋隻是拿她當替身,替的是與葉家門當戶對的白家小姐。傳聞,白小姐回來了,蔣蘊等不到色衰就愛馳了,被葉雋當街從車裏踹了出來。不過,傳聞總歸是傳聞,不能說與現實一模一樣,那是半點都不沾邊。後來,有八卦雜誌拍到葉家不可一世的大少爺,深夜酒吧買醉,哭著問路過的每一個人,“她為什麼不要我啊?”蔣蘊她是菟絲花還是曼陀羅,葉雋最清楚。誰讓他這輩子隻栽過一回,就栽在蔣蘊身上呢。【心機小尤物VS複仇路上的工具人】
70.7萬字8 28297 -
完結153 章

後腰紋身
盛傳頂級貴公子淩譽心有白月光,但從他第一眼見到慕凝開始,就被她絕美清冷的麵龐勾得心癢癢,世間女子千萬,唯有她哪都長在他的審美點上,男人的征服欲作祟,他誓將她純美下的冷漠撕碎。某日,淩譽右掌支著腦袋,睡袍半敞,慵慵懶懶側躺在床上,指尖細細臨摹著女人後腰上妖治的紋身,力度溫柔至極。他問:“凝兒,這是什麼花?”她說:“忘川彼岸花。”男人勾住她的細腰,把她禁錮在懷裏,臉埋進她的頸窩,輕聲低喃:“慕凝,凝兒……你是我的!”他的凝兒像極了一個潘多拉盒子……PS:“白月光”隻是一個小過渡,男主很愛女主。
26.7萬字8 21016 -
完結430 章

人前人後
縱使千瘡百孔,被人唾棄。
69.9萬字8.18 84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