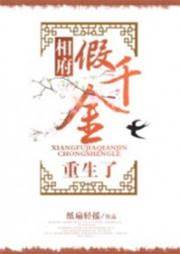《厭春宮》 第十六章 想她
蘇新撐著腦袋,甜甜說道:“那時姐姐你傷口染昏迷不醒,我強攔了貴妃娘娘的儀駕,本是報了必死的決心,卻沒想到貴妃娘娘那樣心善,竟不計前嫌,還賜給我膏藥。”
眸燦爛,又道:“娘娘可真是個大好人!不僅沒罰我,還贊賞我重重義,封我作棲宮主管院的大宮呢!”
越說越興,忍不住握了白若煙的手:“姐姐你說,我們是不是熬出頭了!”
白若煙的笑容倏地凝結在了空氣里。
這算什麼好事!
蘇新本是自己的助力,怎麼突然憑空被那惡毒貴妃三言兩語拉攏了去?
咬著牙,聲音有些恨恨:“那個貴妃娘娘不是什麼好相與的,你可別被哄騙了!”
蘇新嘟著,沉浸在幸福中,沒理會白若煙話里的憤恨,喃喃道:“我覺得貴妃娘娘好極了,這幾日我在棲宮里,覺得都好,外邊那些傳聞,多半是有心人嫉妒,刻意編排娘娘呢。”
“你——”白若煙氣得不行。
“對了姐姐,等我在那立住腳了,你也恢復好,我去向貴妃娘娘討個恩賜,說不定也能接你一起去棲宮呢,到時候姐姐就不用在這浣局做苦力活了!”
聽見那些周旖錦的好,白若煙只覺得異常刺耳。
蘇新自己不識好歹便罷了,居然還慫恿自己也去死對頭的宮里,真是可氣!
明明是自己的助力,卻跑到棲宮去,給別人做了嫁裳。
白若煙再也忍不住怒氣,大喊道:“不可以!你要是去棲宮當值,我們以后便不要做姐妹了!”
霎時間,蘇新的歡聲笑語僵在了半空中。
明的眼角忽的垂了下來,眸子里盛滿了不解與困。
Advertisement
白若煙愣了愣,這才意識到自己的失態,忙彌補道:“我、我只是想著棲宮危險,怕你有什麼困難……我只是舍不得妹妹……”
聲音越來越小,蘇新臉上的神也漸漸淡下去。
白若煙這麼不愿,難道是因為嫉妒自己得了好差事?蘇新不這樣想,心里悶悶的,臉上也黯然無了。
半晌,蘇新說道:“貴妃娘娘已經下令,我違抗不得,姐姐若是不愿意來,那我得空來看你也罷,左右不會再讓你如從前一般吃苦累了。”
二人又潦草聊了幾句,蘇新走出房門,手指著帕子,眼角紅紅的。
約覺得,自從白若煙高燒那次起,一切都變了。曾經那個善良又勇敢的好姐姐,現在卻時常是這樣一副刻薄凌厲的模樣,不由得讓心里發寒。
屋,蘇新走后,白若煙更是生氣難過。飲了一口桌上的冷茶,水里充斥著廉價的氣味,還有沒濾凈的茶渣,甚是難以下咽。
白若煙氣的一把將茶杯丟出去,磕在墻上,大喊道:“真是夠了!”
茶水四濺,染了草席。
穿越這麼久,日夜期盼著自己可以有朝一日能被皇上注意,封為后妃,錦玉食和帝王的無上寵,如今卻屢屢挫,困在這不見天日的昏暗下方里,承非人的折磨。
一切的一切,都怪那個倒霉貴妃,次次壞好事……
想到這,白若煙眼底閃過一陣冷。
蘇新被收攏了又如何,有著這樣一副天賜的容貌,就是無人可比的銳。蘇新不幫,靠著自己,也定能闖出一條道路來。
橫下心來,巍巍下了床,開始收拾起自己全部的家當來。
Advertisement
翌日,小福子剛換班下來,正在養心殿不遠的下房邊上,背靠一棵大樹乘涼。
他雖是皇上面前最得寵的大太監,但伺候魏景并不是容易活計,他得時時刻刻彎腰低頭,不得松懈。
念及此,小福子不了自己發酸的肩膀,想趁著換班的機會休息一會兒。
忽然,背后傳來一個子小聲的呼喚:“福公公!”
下房里本是不得喧嘩,小福子嚇了一跳,轉過頭去,看清面前子的容貌時,驚得是瞠目結舌。
“昭明皇后……”他里喃喃道,“撲通”一聲跪了下來。
“皇后娘娘,小福子給您磕頭了!”
白若煙楞在原地,看著激不已的小福子,他細長的眼睛瞪大,臉上的隨著下跪的作,顯得無比稽,不由得心訕訕。
本是想著,崔公公已被死,這條路走不通,只能鋌而走險,去找崔公公的干爹福公公試試運氣。
小福子還以為是昭明皇后沈秋月,磕頭不止:“皇后娘娘……”
白若煙連忙扶起小福子,笑道:“福公公,奴婢不是昭明皇后,公公認錯人了。”補充道:“奴婢是浣局的宮白若煙。”
小福子愣怔片刻,站起來,仔仔細細打量白若煙的面容。
世間怎會存在這樣兩個如此相像的人呢?他從小便陪在昭明皇后邊,即便皇后已經過世快要三年,他也絕不會認錯。
們二人不僅長得一模一樣,甚至連聲線都極為相似,若非白若煙確實穿著浣局的衫,他怎麼看都覺得這是昭明皇后還魂于世間。
小福子意識到自己方才的失態,轉而又擺出平日里大太監的姿態,維持住面上的驚訝,問道:“白若煙……你找咱家何事?”
Advertisement
看到方才小福子這一幕,白若煙更篤定自己的容貌十拿九穩,輕輕福了一福,從袖口掏出一個荷包,遞到小福子的手中:“奴婢在浣局人欺負,懇求福公公做主,給奴婢一條明路。”
小福子打開荷包,里面是幾兩碎銀子,已是白若煙全部家當。
小福子眉微挑,不腹誹這宮寒酸。平日里各宮小主求他辦事,都是塞金銀珠寶,就憑這點東西,就想求他為自己辦事,未免太不知好歹了。
但一抬頭,對上白若煙這張臉,他頓時又手足無措起來。
他伺候昭明皇后十幾年,對這張臉的敬畏戴已經是刻在骨子里了。
他收起荷包,正說道:“浣局的活計確實太苦了些,你想換個什麼差事?”
白若煙見他不拒絕,心了然,說道:“奴婢聽說,自從昭明皇后去世,福公公在后宮無依靠,當今掌權的貴妃娘娘也時常不給您好臉看,皇上邊獻討寵的下人那樣多,公公想過,未來如何在這宮里長久立足嗎?”
這一番話十分得罪,福公公不皺起眉來,厲聲道:“你想說什麼?”
“公公認得奴婢這張臉吧,”白若煙角帶了一抹輕笑,說道:“若是皇上見到,定會寵幸奴婢,只要公公愿意為我鋪一條路,將來我若飛黃騰達,定不會忘記公公今日之恩。”
小福子呆呆地著,沉默了許久。他并不是沒有想到這一層,甚至在他剛回過神來時,就已經開始盤算此事,但這話從這一小小宮口中說出,不免讓他心里惴惴不安,總覺得有什麼蹊蹺之。
“咱家倒是愿意提拔你。”他猶豫了半晌,還是答應下來,又細細地盤問了白若煙的底細,見只是出家世清白的貧寒人家,才漸漸放下心來。
Advertisement
“這些日子你且不要拋頭面,想見到皇上并非容易之事,”小福子思索片刻,“半月后的馬球會,咱家悄悄安排你去給皇上牽馬,屆時能否得寵,都是看你的造化了。”
二人一拍即合,白若煙笑意漸濃。
日鎏金,國子監里的紅楓已染上風萬種的鮮紅秋。
“做什麼呢?”蕭平遠遠看見魏璇擺了長椅在樹下,笑著走過去問道。
“閑來無事,作畫一張罷了。”魏璇握著筆桿的手略頓。
他穿著墨的緞子袍,袖口出銀鏤空木槿花的鑲邊,秋容淺淡,盛如琉璃的日過枝椏,斑駁地斜斜照在他面頰上,愈襯得他廓致,有些風流年的佻達。
當真是芝蘭玉樹,蕭平心道。怪不得他貧寒質子之,京城里卻有無數貴想通過他打探魏璇的消息,連自己妹妹蕭瑾都時時詢問他,那點喜歡小心思藏都藏不住。
罷了,這麼多年的,他深知魏璇人品格都是極佳,雖然蕭瑾自小被家里金尊玉貴寵著,這樣下嫁有些可惜,但能嫁給這樣的人,他這個做哥哥的也是放心。
“難得難得,給我瞧瞧。”蕭平好奇地湊過來,想看畫上的容。
魏璇才了得,只是困于份,從不輕易顯。往日里他缺錢打點的時候,便會托他變賣一些墨寶畫作,雖不知名諱,但在京城里,他的畫作一度炒到天價,冠絕天下,無數名門子弟爭相購買觀賞。
可剛撇了一眼,蕭平心頭便起了疑慮。
畫紙上,一只貍貓躺在海棠樹下,慢悠悠著爪子。小貓俏皮可,尾尖的絨輕巧地翹起,秀麗的眼角微瞇,渾然一副憨態可掬的模樣。
從前魏璇的詩詞畫作都端的是君子品,往往是高潔淡雅,可這副畫卻頗為靈巧生。
蕭平笑道:“想不到你畫這小貓,也是別有風趣。”
蕭平專心看畫,沒注意到魏璇的臉頰漸漸泛起微紅。
自打那日從棲宮回來后,周旖錦坐在海棠樹下品吃糕點的俏皮模樣便在他心頭揮之不去。
致的眼角微挑,盛滿了喜悅的悠然自得,慵懶靠在躺椅上,素襯著那玲瓏腰肢,漸漸蔓延到他心尖,說不清的閑婉靡、溫繾卷。
思緒正出神,忽然聽見蕭平喚他:“我記得這宮里的海棠樹,便是棲宮那畔最多。”
魏璇的手忽然一頓,猛的咳嗽起來,筆尖的墨迅速在紙上暈染開來。
猜你喜歡
-
完結1252 章
壞壞王爺放肆愛
鳳傾傾重活一世,才知“深情”未婚夫渣,“熱心”手帕交毒,而對她生死不棄的,卻隻有那個她最憎恨的攝政王夫君。嚇的她趕緊抱緊攝政王的大腿:“我乖,我怕,我……求和!”男人邪魅一笑:“好,榻上合!”
144.4萬字7.2 34694 -
連載2594 章

廢柴嫡女要翻天
她是現代美女特工,在執行任務中與犯罪分子同歸於儘,穿越到架空古代成了瞎眼的大將軍府嫡女。剛穿過來便青樓前受辱,被庶妹搶去了未婚夫,賜婚給一個不能人道的嗜殺冷酷的王爺。好,這一切她都認了,大家有怨報怨有仇報仇,來日方長,看她怎麼弄死這幫狗東西!隻是,說好的不能人道?這玩意兒這麼精神是怎麼回事?不是嗜殺冷酷嗎?這像隻撒嬌的哈士奇在她肩窩裡拱來拱去的是個什麼東東?
385.8萬字8.18 222591 -
完結2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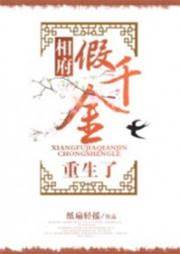
相府假千金重生了
蘇靜雲本是農家女,卻陰差陽錯成了相府千金,身世大白之後,她本欲離開,卻被留在相府當了養女。 奈何,真千金容不下她。 原本寵愛她的長輩們不知不覺疏遠了她,青梅竹馬的未婚夫婿也上門退了親。 到最後,她還被設計送給以殘暴聞名的七皇子,落得個悲慘下場。 重來一世,蘇靜雲在真千金回相府之後果斷辭行,回到那山清水秀之地,安心侍養嫡親的家人,過安穩的小日子。 惹不起,我躲還不行麼? 傳聞六皇子生而不足,體弱多病,冷情冷性,最終惹惱了皇帝,失了寵愛,被打發出了京城。 正在青山綠水中養病的六皇子:這小丫頭略眼熟? 內容標簽: 種田文 重生 甜文 爽文 搜尋關鍵字:主角:蘇靜雲 ┃ 配角: ┃ 其它: 一句話簡介:惹不起,我躲還不行麼? 立意:
39.4萬字8 3073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