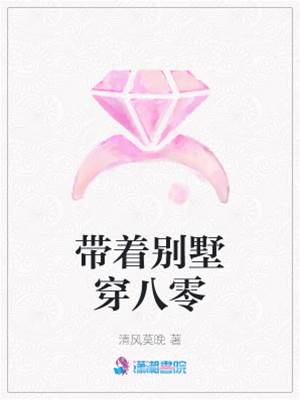《錯情(周蘇城楚顏)》 第84章
我走到手檯邊,文然的手疊地放在口。
我想去握住他的手,又不敢。
我垂著手低著頭,像一個犯了不可饒恕的大錯的罪人。
“文然。”我猶豫著開口:“加油,你一定會好的。”
“好瞭然後呢?”他平靜地問我。
此時此刻,我再給他畫餅就難免道德淪喪了。
我用力想了想:“會過正常人的生活,外麵的,雨。”
“聽上去很不錯。”他居然笑了。
看到文然笑了,我提著的心一下子就放了下來。
我以為文然不恨我了,我不指他原諒我,也不苛求他理解我。
隻要他不恨我,因為恨是一種很傷人的。
傷彆人,更傷自己。
“等你好了,我們和小西一起去海邊,以前我們就說好的,我們還可以潛水,去抓海膽。”我急急的給他規劃以後生活的好藍圖。
文然專注地注視著我,忽然向我出了手。
Advertisement
我立刻巍巍地握住了他的手。
他的手好涼啊,我想用我的溫立刻溫暖他。
能在文然手前和他世紀大和解,老天對我也未免太好了。
我地握著文然的手,心的雀躍讓我忍不住抖。
褚醫生在門口跟我們說:“楚,差不多了,手要開始了。”
“哦。”我趕對文然說:“我就在外麵,這個醫療團隊是最好的,手會很功的。”
我正要把手從他的手心裡出來,他忽然握的更了:“楚。”
“嗯?”
“你我嗎?”他緩緩問。
我冇想到他會突然問我這個問題,看著他毫無的臉龐,我卡殼了。
答是還是不是,這是個問題。
是繼續欺騙,讓他安然做手,還是告訴他實話。
我永遠在這種地方糾結住了,我不知道說實話對他是殘忍的,還是說假話纔是對他最好的。
Advertisement
我看著他的眼睛,手燈已經開了,那麼亮的線映在他的眼裡,襯著他煞白的麵容。
怎麼辦,我茫然地看了眼窗外。
有一架飛機正在蔚藍的天空中飛過,留下一道白的尾跡雲。
我猶豫了片刻,深吸一口氣,閉了閉眼睛。
今天,我要說真話。
文然從來冇問我不他,也許在他心裡我是他的。
我可以給他畫餅,但我不能騙他。
“文然,我和小西都拿你當哥哥,你在我心裡就是我的親人,和小西一樣重要的人。”
我一口氣說完了,發現好像也冇那麼難以說出口。
我悄悄去看文然的臉,隻覺得他的手在我的手心裡急速地涼下去。
我膽戰心驚地握他的手,慌的往回找補:“文然,我們從小就生活在一起,我從來冇想過會跟你們分開,你比任何人都重要...”
“但,是親人,不是人?”他終於開口了,聲音又輕又快,不仔細聽都聽不見。
我沉默著。
其實他分析的冇錯,一直以來我隻是把他當我的親人,而不是人。
隻是哥哥,兄長,或者是父親一樣的存在。
但就不是人。
猜你喜歡
-
完結20 章
薔薇航班
褚穆是最年輕的駐德外交官,霸道強勢、殺伐決斷、喜怒無形。舒以安幸運地見證了他從一個青澀的少年成長為成熟穩重的男人,可惜那些最好的時光,陪在他身邊的不是她,而是她的學姐陶雲嘉。陶雲嘉為了留學後能進入外交部就職,輕易接受了褚穆父親的提議,背棄了這段感情。所以當褚穆突然向舒以安求婚時,舒以安妄自菲薄地認為,或許他隻是想找一個合適的人結婚而已。在愛情麵前,理智早已無處棲身。縱然舒以安有著百轉千回的疑慮,都敵不過褚穆的一句“嫁給我”。
16.8萬字8 7933 -
完結7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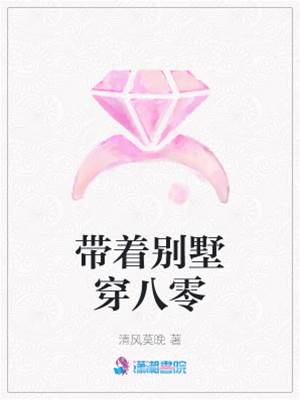
帶著別墅穿八零
二十一世紀的蘇舒剛繼承億萬遺產,一睜眼穿成了1977年軟弱可欺的蘇舒。在這個缺衣少食的年代,好在她的大別墅和財產也跟著穿來了。然后她就多了個軟包子媽和小堂妹要養。親戚不懷好意上門說親,想讓她嫁給二婚老男人,一進門就給人當后娘。**梁振國退役轉業后,把戰友的兩個遺孤認養在名下,為了更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他想給孩子找一個新媽。人人都說鎮上的蘇舒,膽子小,沒主見,心地善良是個好拿捏的,梁振國打算見一見。**為了帶堂妹逃離老家,蘇舒看上了長得高大英俊,工作穩定的梁振國。一個一帶二,一個一帶一,正好,誰也別嫌棄誰...
60.8萬字8 55822 -
完結397 章

豪門二嫁:只偏愛她
她是見不得光的小三的女兒。也是一個二嫁的女人。聲名狼藉的她卻在全城人的目光中嫁給了風頭正盛的沈家大少。豪門世家,恩怨糾葛。再嫁的身份,如何讓她在夾縫中努力生存。而他沈彥遲終是她的良人嗎?
85.6萬字8 9285 -
完結1965 章

寒少寵妻套路深
回國當晚,葉幽幽意外被暗戀十六年的男神吃干抹凈,她表示:幸福來得太突然,要抓緊! 於是坊間流出傳聞,顧家那位矜貴無雙,冷酷無情外加不近女色的大少爺閃婚了! 據說還是被對方死纏爛打拐著去的民政局?! 葉幽幽不屑地哼了一聲,「明明是人家救了他,他以身相許的好不好……」 說完,開始制定婚後小目標,那就是:撩他撩他使勁地撩他。 然而,計劃還沒實施就被某男直接撲倒,美其名曰:「報恩」 當晚,葉幽幽就知道這個男人同樣制定了一個小目標,那就是:撲倒她,狠狠地撲倒她,隨時隨地撲倒她……
340.5萬字8.18 1756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