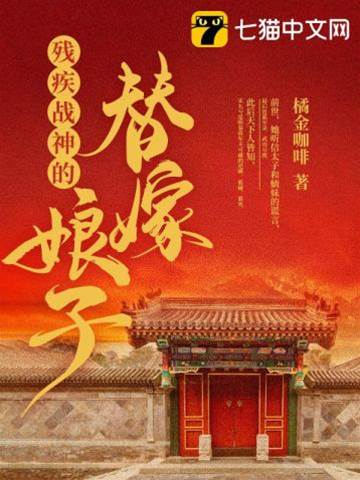《穿書打工手札》 第96章 第96章
此時此刻的柳莊, 早已人去樓空。孟氏父子二人,三日前便離了豫州,料想彼時他們便帶走了慶王。
徐子牧悔不當初, 當日他見到孟寒后,他就該立刻回來稟報上聽,哪怕是尋了李小將軍,悄悄報信也行。
他怎麼會料到, 李佑白竟會真的來了豫州。
他來得怎麼如此之快!
徐子牧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悔不當初, 嗚咽著將孟氏父子如何在流放途中假死, 如何逃說了個遍。
說著說著,他方覺手上漸沒了知覺,流不止, 他會不會就這麼死了。
他的話音越來越低, 他真的就快痛暈過去了。
可李佑白顯然不打算就此放過他,那一柄利劍還牢牢地釘在他手背上。
徐子牧撐著最后一口氣說:“孟寒還說南越人抓到了一個太醫,手里有本醫經, 可證,可證皇室統不正, 慶王……”他不覺冷汗涔涔,斷斷續續道,“慶王不是皇帝親骨, 但是有了敕令在手, 又可移花接木, 外人, 外人或可以為陛下也……”饒是小命不保, 下面的話, 徐子牧也不敢再說下去了。
孟氏與南越人勾結, 擄了慶王,早就不要命了。
現在回想起來,他們說的那個醫,同他看的敕令,說不定也是假的。
當日他太蠢,太害怕了,就這樣被他們唬住了。
徐子牧追悔莫及,熱淚滾滾。
頭頂上卻傳來李佑白的聲音,問:“孟氏可說了要去哪里?”
徐子牧忙道:“去池州,渡過暗河,往南越去。”
李佑白霍地拔出了地上的長劍,濺三尺,徐子牧痛呼一聲,暈了過去。
李佑白不再看他,扔掉了滿是跡的長劍,冷然道:“徐子牧通敵背義,按律當斬,今日決。”
Advertisement
“是。”
堂上哭聲驟停,堂外的冷月照舊高懸。
*
周妙睡得不沉,院外馬蹄聲響起的時候,便倏地驚醒了。
連忙翻而起,隨手扯過一件長衫,徑自往窗前走去。
推開窗張,黑暗之中,約可一隊人馬自莊園大門進來。
探頭又看,侍從提燈去迎,朦朦朧朧間,見到了李佑白。
他一黑,翻下馬,走了兩步,抬頭也見了窗邊的。
他腳步微頓,緩緩走到廊下,周妙適才看清他黑氅下擺深沉,仿佛是。
周妙不由地倒一口涼氣。
還沒開口,只聽李佑白道:“不是我的。”頓了頓,他又微微蹙眉道,“你還沒睡麼,你先睡罷。”說罷,轉而朝另一側的長廊而去。
周妙著他的背影,微微一愣,雖然只是短暫一面,可覺得李佑白的心實在是說不上好。
難道這整整三日,他都沒找到慶王?
周妙想追去問個究竟,可是眼下的李佑白一副冷淡得不愿多談的模樣。
但好在,他已經回來了。
周妙手合上了窗,悶悶地躺回了床上。
閉上眼想睡,可半天都睡不著。
正當準備起,去問個明白的時候,門扉一響,扭頭一看,來人正是李佑白。
他換過了袍,只著素白中和黑綢,肩上披著白氅。
上再不聞腥,唯有溫熱的水汽。
周妙驚訝地見他徑自揭開錦被,躺到了榻上。
原以為他今晚不會理了。
“陛……”
一開口就被李佑白突兀地打斷。
他按住了的雙頰,彈不得,可這一吻除了纏綿,分明還有其他說不清道不明的復雜緒。
整整三日不見,或許是有些想念。
Advertisement
的舌發麻,渾愈發沉重,仿佛有崇山峻嶺幾乎要得不過氣來。
周妙忽覺今夜的李佑白尚還于一種“”的狀態中,不曉得他這三日間究竟做了什麼,可是料想也不是什麼歲月靜謐的好事。
他上除了溫熱的潤氣息,其實已再無旁的氣息。
可是,周妙還是力地推開了他,盯住他的眼睛,問道:“你殺人了?”
李佑白一愣,面不改道:“未曾。”話音剛落,他又急不可待地吻住了的。
周妙恍恍惚惚間,卻覺心稍定。
直到李佑白著的耳朵含糊低語一句。
周妙不臉一變,道:“我不。”
李佑白卻已牢牢握住了的右手腕,勸道:“好妙妙,投我以桃,報之以李這個道理,你懂不懂。”
“我不懂。”
李佑白低笑一聲,附耳又道:“好妙妙,你幫幫我。”
那語調輕,聲似靡靡,周妙愣了愣,鬼使神差地,忘記了要掙。
月下,李佑白的神和若泠泠水,他溫熱的額頭上了滾燙的臉頰。
他的鼻息近在耳畔,周妙一面覺得憤不已,一面卻又覺得他此刻的神尤為新奇,宛如林中野收起尖利爪牙,忽而出了自己而脆弱的肚皮。
任人予取予求。
薄云被風卷去,月華澄凈,投進軒窗的一時亮,一時暗。
不知過了多久,周妙真的累了,將慶王拋在了腦后,昏昏睡去。
*
隔天,他們便啟程往池州行。
車行極快,沿途幾無停留。
戰事吃,南越人一舉攻下了拓城,池州轉眼已是陷了戰火。
拓城不是一座大城,但城中的數千流民往北齊齊涌向池州府,而簡青竹被困在了拓城。
Advertisement
怕極了,不曉得事為何忽然往最壞的形變化。
在船上時,儺詩云沒為難,他們一路沿漣水疾行,到了池州才換作陸行。
只是此際南越人強攻了拓城,儺詩云并沒有再帶著再往南越而去,反而將強留在了拓城。
簡青竹想走也走不,突遇戰事,更是不由己。
阿果還在他們手里。
儺詩云說,阿果也要來池州了。
簡青竹哭無淚,起初只是想悄悄地帶著阿果離開,走得遠遠的,遠離皇權,遠離紛爭。
可是如今的池州,儼然是爭斗的中心。
簡青竹在拓城等了三日,終于見到了阿果。
他看上去比之大半月前,瘦了也黑了。他的目依舊呆呆傻傻,但是見到的時候,竟然將認了出來。
“簡太醫。”他喚道。
簡青竹撲將過去,正想檢查他有沒有傷時,卻被儺詩云的護衛生生扯開。
儺詩云道:“人,你也見到了。那一本你從四十二所拿到的醫書也該出來了。”
簡青竹輕抖,向儺詩云。
儺詩云揚笑道:“簡太醫難道忘了?你們一家人難道就白白死了?你不想報仇麼?”
簡青竹閉不說話。
儺詩云大笑道:“你是糊涂蟲麼?事到如今,難道你還不知道誰是你一家的仇人?”
四十二所這些年可沒幫孟仲元料理差事。
簡青竹雙目通紅,怒瞪向。
儺詩云復又道:“你那大哥與昭儀私通,死在宮里,不冤。孟仲元指使人輕而易舉地殺了他。難纏一點的是你爹,對不對,他是不是發現了其余別的不得了的事,還寫進了醫札。”
簡青竹立刻想到了翻到的缺了書頁的醫札,上面前后書頁,的確是阿爹的筆跡。
Advertisement
開口問:“在你手里?”
儺詩云笑道:“在孟公公手里,可是孟公公太不小心了,被孟侍郎藏了去。”
簡青竹瞪大了眼:“那你知道阿果他……”
“他不是大菱皇帝的骨,對不對?”儺詩云眨了眨眼,“李佑白是不是,也不是?”
簡青竹心頭狂跳,口中急道:“你們為何還要打著阿果的旗號……”篡權奪位?
儺詩云大笑兩聲:“那可不是我們的主意,是你們大菱人的主意,他們想扶持個小皇帝,自是愚蠢至極,于南越而言,大菱越越好,沒有皇帝比有皇帝更好。”
簡青竹再是愚鈍,也明白了過來。南越人本不是想扶持阿果,而是要讓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越是和李佑白斗得死去活來,南越越是安全。
簡青竹頭苦,啞聲道:“那你說,是誰害了我爹爹?”
儺詩云卻搖了搖頭,挑眉道:“我怎麼知道?”
簡青竹怒道:“你!”
儺詩云又笑了笑,語氣輕佻:“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你二哥簡青松是誰殺的。”
簡青竹再不上當,閉上了。
儺詩云一字一頓道:“他就是李佑白殺的。”
“你胡說!”簡青竹當即反駁道。
“哈哈哈,為什麼不是他?”儺詩云笑道,“簡青松去了錦州,除了李佑白,無人知曉,他派了人四下去尋,難道不能一找到,就順水推舟地殺了他,再惺惺作態騙你啊?。”
簡青竹搖頭:“他沒有理由殺我二哥。”
儺詩云湊到臉前,緩緩說道:“你真的想不出理由麼?簡家人在宮里死得蹊蹺,李佑白心眼多,心也是黑的,殺人不眨眼,說不定你一出現,他就猜到了簡家人不能留活口,而你太蠢,就先從你聰明一點的二哥殺起……哈哈哈哈!”
簡青竹捂住了雙耳,大道:“你住口!”
作者有話說:
猜你喜歡
-
完結717 章

嫡妃驚華:一品毒醫
她本是侯門貴女,奈何痴心錯付,大婚之日家破人亡屍骨無存!再睜眼時,她是將門臭名昭著的落魄嫡女,處境艱難。涅槃重生,除小人,斬奸臣,平瘟疫,復仇之路她遇神殺神佛擋殺佛!王侯將相皆拜倒在她裙下,連退了婚的未婚夫都不肯放過她。本以為註定孑然一身,卻不想被一個壞到極致的傢伙纏上,他將此生唯一的柔情和真心給了她,還是不能拒絕的那種!「傳令下去,王妃柔弱不能自理,欺她者殺無赦!」眾人回想起因自家王妃而被抄家滅門的侯府相府,不由得瑟瑟發抖,王爺,您別開玩笑了……
136.4萬字8 25939 -
完結52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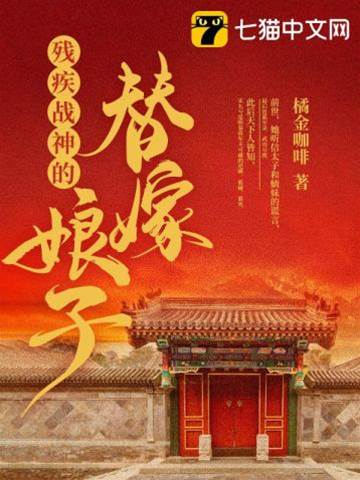
殘疾戰神的替嫁娘子
【重生+男強女強+瘋批+打臉】前世,她聽信太子和嫡妹的謊言,連累至親慘死,最后自己武功盡廢,被一杯毒酒送走。重生后她答應替嫁給命不久矣的戰神,對所謂的侯府沒有絲毫親情。嘲笑她、欺辱她的人,她照打不誤,絕不手軟。傳言戰神將軍殺孽太重,活不過一…
97.6萬字8 30589 -
完結87 章
我要這美貌有何用
沈纖纖冰肌玉骨,美麗無雙。機緣巧合下,憑借美貌成了晉王的“真愛”。 晉王外表清冷,演戲卻是一流,人前對她一往情深,人後話語毫不留情:隻是作戲而已,不該動的心思不要亂動。 沈纖纖:明白,放心,包您滿意。 作為晉王拒絕皇帝賜婚的擋箭牌,沈纖纖盡職盡責扮演好一個美豔醋精真愛的角色,隻等機會合適就帶著金銀珠寶遠走高飛。 不成想,晉王重傷,命在旦夕,一道聖旨下來,她成了晉王妃。
31.8萬字8 22740 -
完結155 章
重生后成了皇叔的掌心寵
燕寧一直以為沈言卿愛慕自己才把自己娶進門,直到沈言卿一碗燕窩讓她送了命,她才恍然大悟,自己不是他的白月光,撐死了只是一顆米飯粒。沈言卿的白月光另有其人,清艷明媚,即將入主東宮。重頭來過,燕寧哭著撲進了楚王鳳懷南的懷里。鳳懷南做了三十年皇叔,神鬼皆俱無人敢親近他。僵硬地抱著嬌滴滴依戀過來的小丫頭,他黑著臉把沈家婚書拍在沈言卿的臉上。“瞎了你的狗眼!這是本王媳婦兒!”上一世,她死在他的馬前。這一世,他給她一世嬌寵。
79.5萬字8.18 61600 -
完結280 章

天命毒后
【重生+醫術+金手指+男強女強+爽文】 她宋蒹葭本是北辰國最尊貴的鸾皇郡主,回門當日夫君與庶妹無媒苟合,姐妹同侍一夫淪為笑柄。 婚後更是被庶妹算計,失了孩子,被妾室困於後宅極盡折磨兩年。 眼睜睜看著家族慘遭滅門,國家易主。 一朝重生,大權在握,渣男賤女都要付出應有的代價,前世種種恩怨她都要一一扳平。 她親手擊碎仇人的帝王夢,將前世之苦全數奉還。 於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開始了行俠仗義,護民護國的道路,他們與權貴鬥,與世道鬥,擊破亂局,開太平盛世。 只是除了滔天恨意,她好像還欠了一個人的情。 【我南疆兒郎一生只求一人,所以不管上窮碧落下黃泉,我都會護著你的】 【我豈有不信之理。 】
63.5萬字8 111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