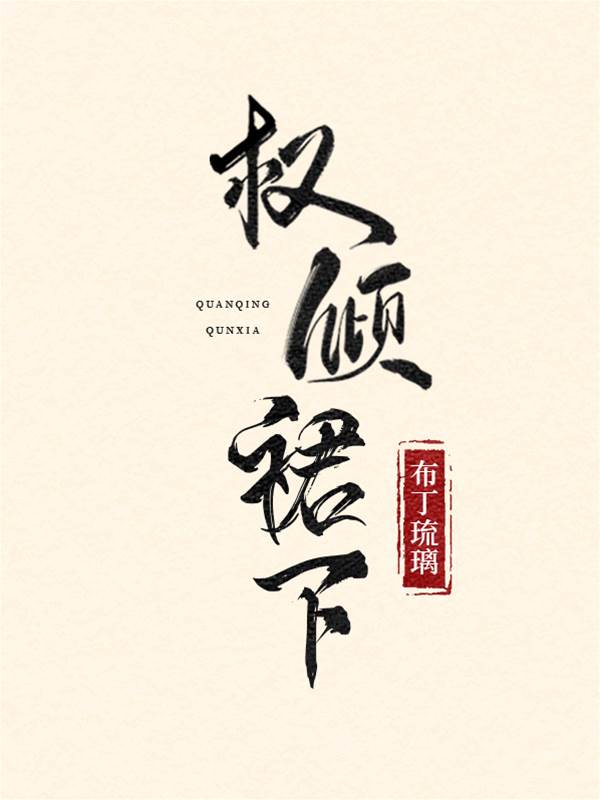《裙下臣》 第31章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
太和殿。
代表皇權的司禮監太監站在左側,閣大臣和朝廷重臣站在右側。
面對空的龍椅,大家早已經習以為常。
皇上自繼位就沒怎麼上過朝,近兩年更是直接不去了。
起初言還會罵一罵,習以為常之后便順其自然了。
今早馮初起來,便覺得右眼皮跳得厲害。
可能是昨夜沒睡好,他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想關于李眉嫵的事。
還是不由自主的擔心,想來不過是被了服,在雪地上凍暈了,總該不會想不開自殺。
畢竟李眉嫵的出不是世家小姐,沒有過禮儀教養的熏陶,對辱沒有那麼錐心刺骨的難挨。
本就是做奴才的,平常若是罰被打板子,太監和宮都一樣,還不是要掉子趴在長椅上挨打。
在這皇宮里,除了天子,誰有尊嚴可言?
悄悄走神,剛才朝堂上的槍舌戰沒仔細聽,掉了很多信息。
才回過神來,便聽見閣首輔大臣吳謙正在歷數、兵部尚書孫丙的罪行。
“前有西南軍營里逃出來的暴徒,竟跑到皇宮里刺殺皇上。
后有西北匈奴來犯,連下幾座城池,眼看就要打到京城來了。
你這個尚書大人當得好哇!若是無能趁早了這服,我大銘王朝從不缺將相良才!”
吳大人的戰斗力一直都是可以的,罵得孫丙面紅耳赤,卻也啞口無言。
戶部尚書王恩山趁機補刀,“孫大人怎麼舍得這服?
孫大人代表的,可不是名門族孫家的臉面,還擔負著貴妃娘娘的盛名。”
孫丙實在聽不下去了,“后宮不得干政,前朝也別總把主子扯進來。
Advertisement
男人之事,總把娘娘拉進來,也不害臊!”
“如今正值用人之際,訌也不能解決問題,吳大人切莫意氣用事,大家都是為皇上分憂。”閣大學士徐勸了句,又將目轉向馮初。
“馮公公可有將此事稟告給皇上?”
馮初慣于在朝堂之上一言不發,因為他需要說得話,他的黨羽總能替他完。
言多必失,謹言慎行。這是他干爹孟淵教他的第一樁要事,比功夫和書畫還重要。
眼前徐點到自己名字,馮初不能再沉默,因為徐不僅是皇上的老師,也是自己的老師。
十幾年前,皇上還是王爺的時候,馮初作為伴讀,陪朱振一起拜讀在徐膝下。
如今馮初寫得一手好字,畫得一幅潑墨山水圖,都是徐的功勞。
“以為孫大人能平息,還未上報給皇上。”
馮初在批閱奏折的時候,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匈奴年年在邊境燒殺搶掠,冬天更甚,搶了東西好過年。
都是一些未開化的蠻夷,能什麼氣候,馮初一直沒把那些草原匈奴放在眼里。
只是沒想到這次,他們不在西北打劫,還打到中原來。
“馮公公怎可欺上瞞下,越俎代庖?待匈奴兵臨城下,如何跟萬歲爺代?”刑部尚書鄭容,作為新科狀元,新上任三把火,初生牛犢不怕虎,當場懟了回去。
他既不太懂場規則,也不愿像其他人那樣,對一個太監恭敬有加。
“現在報給萬歲爺,若是驚了龍,鄭大人擔待得起嗎?”戶部尚書王恩山冷笑一聲。
“臣自苦讀圣賢書,卻不想跟臣同朝為!”被懟之后的鄭容,更加惱火。
Advertisement
自小就被稱為神,從小到大沒過什麼挫折。
靠著讀書走上仕途后,才發現大銘王朝爛到了骨子里,皇上不上朝,竟由太監弄權。
“何為臣?”王恩山視著他。
不懂得審時度勢的鄭容,也沒打算退,直接指著司禮監的方向,“馮初!本朝第一大臣。
還有你,戶部尚書王恩山,助紂為!
爾等架空皇權,天人共憤!”
馮初聽見他這話有點想笑,不過輕咬著,還是忍住了。
若自己真是臣,這個新科小狀元鄭容、早已經死一萬次了。
微微打量了一眼鄭容,雖然不太懂趨炎附勢,不懂旁人慣于看馮初的臉,是出于對皇上的敬畏。
司禮監代表的是皇權,馮初是萬歲爺的人。
連這個道理都不懂的鄭容,卻反而引起了馮初的注意,狀元八是讀書讀傻了,不諳世事。
不過無妨,大銘王朝不能盡是些奴婢膝之徒,也需要鄭容這樣的清流,以正綱紀。
馮初準備重用他,不過不是現在。
“好了,吵來吵去,何統?”閣大學士徐實在不愿,朝堂之上,變婦人罵街的地方,隨即站出來維持秩序。
徐如今、年過古稀,作為三朝元老,皇上也得給幾分薄面。
鄭容依舊不把他放在眼里,“徐大人仗著舊時教導過馮初,便護短。
就算馮公公是早前在王府伺候萬歲爺的,又如何?奴才就是奴才。
我大銘王朝何時、讓一個奴才攪風云了?”
銘朝自古以來,都有敬老尊賢的習俗,鄭容在朝堂之上大放厥詞也就算了,如今連滿頭華發的徐、也被他歸臣一類。
Advertisement
要知道當年宮變,是徐力挽狂瀾,才使得江山穩固……只不過那個時候,鄭容還沒出生。
這下子不管是清流派,還是孟淵派,紛紛指責鄭容狂妄。
吵來吵去,馮初就這般靜靜聽著,思量著、若是孫丙退敵無能,當派誰去剿匪。
他是才之人,即便猶如鄭容那般,不太懂事的狀元,他依舊有容忍度,只可惜狀元不常有。
“依我看,匈奴不就是想要糧草珠寶和人嗎?我大銘王朝國庫充盈,賞他一些又何妨?眼下讓匈奴退兵才是重中之重。”戶部尚書王恩山話音剛落,立刻遭到圍攻。
孫丙:“王大人莫非跟匈奴私通?好一個送糧草珠寶和人,糧草你自掏腰包置辦,珠寶拿你夫人的,人送你兒去和親,您看如何?”
王恩山:“若不是孫大人剿匪不利,我大銘王朝何至于如此?尸位素餐還這般放肆,果真臉皮比宮墻厚。靠貴妃娘娘的帶關系,當上兵部尚書,就是不一般!”
“王大人話糙理不糙。”小狀元鄭容向來對事不對人,遇見跟自己意見一致的,立刻忘了,自己剛才還罵人家是臣這回事。
“匈奴都是不知激,不知敬畏。
自古以來,只有匈奴向我大銘俯首稱臣,如何讓我大銘向匈奴納貢?
若了匈奴的要挾,讓皇上和列祖列宗面何存?”
徐嘆了口氣,“鄭大人言之有理。
依老夫見,匈奴的胃口可不僅僅是人和珠寶,他今日打劫要人我們給人。
明日打劫要江山,我們難道還將江山拱手讓人?”
站在馮初旁邊的司禮監掌印太監姚牧,也是孟淵的干兒子之一,沉默半晌,也發表了自己觀點,“諸位大臣都是朝廷棟梁,憂國憂民。
Advertisement
而我等作為奴才,只想著替萬歲爺分憂。
莫不如依王大人所言,先給匈奴以人和珠寶安,至不要讓匈奴打到紫城來,以免驚了萬歲爺。
待到匈奴退回到西北,再從長計議,到那時是練兵,還是選將,不遲啊。”
互相掐架進尾聲,眾人都將目轉向馮初,等他決策。
知他的意思就等于皇上的意思,因為每一次,即便皇上跟馮初意見相左,也架不住馮初進言相勸,最后還是聽馮初的。
朱振跟馮初很早就認識,兩個人一塊在王府度過了很多年月。
朱振作為先帝的侄子,能坐上皇位,馮初立下了汗馬功勞。
朱振和馮初的分,自然不是朝廷上這些大臣能比的。
猜你喜歡
-
完結441 章

將軍,夫人又要爬牆了
秦家有女,姝色無雙,嫁得定國公府的繼承人,榮寵一生繁華一生。可世人不知道,秦珂隻是表麵上看著風光,心裡苦得肝腸寸斷,甚至年輕輕就鬱鬱而終了。重活一世,秦珂還是那個秦珂,赫連欽也還是那個赫連欽,但是秦珂發誓,此生隻要她有一口氣在,就絕對不嫁赫連欽。
83.1萬字8 22482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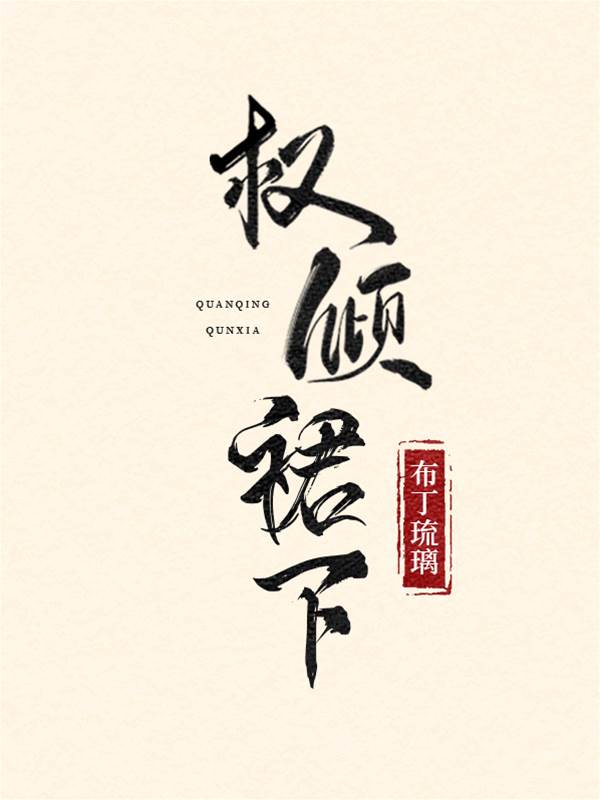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512 -
完結142 章

陛下今天也很好哄
蕭知雲上輩子入宮便是貴妃,過着千金狐裘墊腳,和田玉杯喝果汁,每天躺着被餵飯吃的舒服日子。 狗皇帝卻總覺得她藏着心事,每日不是哀怨地看着她,就是抱着她睡睡覺,純素覺。 是的,還不用侍寢的神仙日子。 蕭知雲(低頭)心想:伶舟行是不是…… 一朝重生, 爲了心心念唸的好日子,蕭知雲再次入宮,狗皇帝卻只封她做了低等的美人,還將破破爛爛的宮殿打發給她。 蕭知雲看着檐下佈滿的蛛絲,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誰知人還沒進去呢,就有宮人來恭喜婕妤娘娘,好聲好氣地請她去新殿住下。 蕭知雲(喜)拭淚:哭一下就升位份啦? 男主視角: 伶舟行自小便有心疾,他時常夢見一個人。 她好像很愛他,但伶舟行不會愛人。 他只會轉手將西域剛進貢來的狐裘送給她踩來墊腳,玉杯給她斟果汁,還會在夜裏爲她揉肩按腰。 他嗤笑夢中的自己,更可恨那入夢的妖女。 直到有一天,他在入宮的秀女中看見了那張一模一樣的臉。 伶舟行偏偏要和夢中的他作對,於是給了她最低的位分,最差的宮殿。 得知蕭知雲大哭一場,伶舟行明明該心情大好,等來的卻是自己心疾突犯,他怔怔地捂住了胸口。 小劇場: 蕭知雲想,這一世伶舟行爲何會對自己如此不好,難道是入宮的時機不對? 宮裏的嬤嬤都說,男人總是都愛那檔子事的。 雖然她沒幹過,但好像很有道理,於是某天蕭知雲還是大膽地身着清涼,耳根緋紅地在被褥裏等他。 伶舟行(掀開被子)(疑惑):你不冷嗎? 蕭知雲:……去死。 伶舟行不知道蕭知雲哪來的嬌貴性子,魚肉不挑刺不吃,肉片切厚了不吃,醬味重了會嘔,葡萄更是不可能自己動手剝的。 剝了荔枝挑了核遞到蕭知雲嘴邊,他神情古怪地問道:是誰把你養的這麼嬌氣? 蕭知雲眨眨眼(張嘴吃):……
22.6萬字8 229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