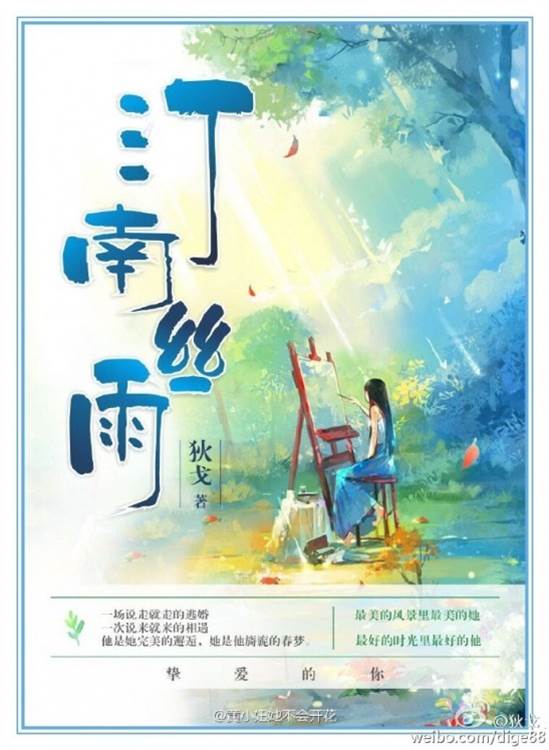《不露聲色》 第117章 第 117 章
小男孩是呼嘯而過的老相識。但是跟唐淼是第一次見。小男孩說完這話的功夫,幾個人已經看著他笑了起來。齊遠看著小男孩,在他說完后,點頭道。
“行啊。”
“我們聽聽有沒有進步。”
“也有段時間沒有見你了。”
確實。自從去年夏天見過幾次之后,后來呼嘯而過要麼忙,要麼有事,沒怎麼在這兒聚過餐,也就沒怎麼見過這個小男孩了。
齊遠這麼說完,小男孩沖著他笑了一下。笑完后,小男孩又看了一眼賀嘯。而在他看向賀嘯時,賀嘯也在看著他。他看過來后,賀嘯也沖著他笑了一下。
看到賀嘯的笑,小男孩也是笑了起來。笑起來的同時,他低下頭,手指撥過了琴弦。
小男孩比去年長大一歲了。他去年是第一年出來唱歌,唱得不怎麼樣。呼嘯而過幾個人第一次到他的時候,他唱得磕磕,沒有人愿意為他買單。
第二次見的時候,小男孩就有了明顯的進步,最起碼能唱一首稍微簡單點的歌了,吉他也比第一次練得多。
而一年沒見,這次再聽他唱歌,他的進步已經是非常大了。
小男孩也就是年的模樣,還沒到變聲期,聲音清澈而空靈。他嗓音基礎條件不錯,再加上選了一首歌手的歌,唱得時候配合著吉他簡單的音,倒是有了些別樣的味道。
小男孩比第一回的時候,已經放開很多了。所以嗓音也打得比較開,唱著的時候,周圍幾桌的客人也看了過來,大家安靜地聽著,偶爾和同桌的人對視,然后贊賞地想點點頭。
一首歌也就兩三分鐘的時間,很快唱完。唱完之后,大排檔的喧囂與吵鬧中,男孩的聲音停止,消失,一下將大排檔的喧囂與吵鬧的聲音又重新襯了出來。
Advertisement
周圍幾個人在小男孩唱完后,紛紛給予了掌聲,甚至也有給錢的。小男孩過去笑著謝過接過了,而后重新回到了呼嘯而過他們這桌前。
小男孩重新回來,齊遠笑著說:“唱得很好。”
“一首歌什麼價?”齊遠問。
齊遠這樣問完,小男孩沖他咧一笑,道。
“一碗面。”
小男孩這麼說完,桌上幾個人笑起來,而林燁也已經拿了椅子讓他在他和賀嘯旁邊坐下了。在小男孩坐下的時候,齊遠從座位上起,笑著說。
“行嘞,我去給你要面。”
說話間,齊遠去找大排檔的老板了。
小男孩過去坐在了林燁和賀嘯的中間。在坐下的同時,他將吉他放在了賀嘯那一邊。這樣放下后,賀嘯看了一眼他的吉他,而后將吉他拿了起來。
吉他又用了一年,又舊了一些,但是格外有味道。賀嘯抱著吉他,抬手給擰了擰琴弦,調了調音。
在他做著這些的時候,齊遠也已經要了面回來,老板上了面過來,小男孩拿了筷子,一邊吃面,一邊看向了賀嘯。
“您要唱嗎?”小男孩吃著面,眼睛里帶著雀躍的。
他第一次聽賀嘯唱歌時的場景,還留存在他的記憶里,璀璨地發著。他不知道賀嘯的份,但是很喜歡聽賀嘯唱歌。某種程度上,賀嘯第一次唱歌時他看到的樣子,也讓他有了一定標榜的榜樣。
小男孩這麼說完,賀嘯抬眸看了他一眼,笑了笑。
笑過以后,賀嘯濃黑的眼睫重新垂下,與此同時,他修長而又骨節分明的手指過了已經調好音的吉他的琴弦。
霎那間,吉他琴弦聲起,在找到了一個調子以后,賀嘯抱著吉他,就那樣彈了起來。
唐淼坐在賀嘯的一旁,看著他彈吉他。
Advertisement
賀嘯會很多種樂。不鍵盤,吉他,貝斯,甚至架子鼓他都能來。而知道歸知道,親眼看到還是另外一回事。
賀嘯的氣質很沉靜。在他彈鍵盤的時候,他冷白的手指在黑白鍵之間靈巧的變幻,你會覺得他天生就是適合彈鍵盤的。
而當你看到他彈吉他的時候,又會有另外一種覺出現。他的手指修長分明,每一手指的骨節都是那麼漂亮致,就這樣的手指,指尖劃過吉他的琴弦。在吉他的音箱里,流水一樣的聲音連貫而又有規律同時好聽地響起。
你又會覺得他天生就是彈吉他的了。
賀嘯彈了一首曲子。
一首陌生,平淡,溫,帶著些月般皎潔明亮的曲子。
這首曲子,開始時候就是很簡單的音符切,到了中途,帶著些迷霧般的朦朧與曖昧,再到了后面,就是清晰的,飽滿的,清甜的,明亮的,一片坦途的。
這并不是一首很復雜的曲子。甚至說過于單調和簡單。而且他也只是彈了曲子,并沒有唱歌,沒有歌詞的加,讓這首曲子顯得更為平淡。
而雖然平淡,卻又并不平凡。里面的每個音符,像是都完整地卡在了聽者心中那個凹槽上,嚴合的讓人被這首曲子拉進它所描述的故事與畫面中。
所以,在賀嘯彈完最后一個音節,手指平落在吉他的琴弦上時,帶來了比剛剛小男孩唱完歌之后,更為長久的寧靜。
賀嘯平了琴弦的余音,將吉他重新放下,這時,桌上的人也反應了過來。
他們剛才在小男孩過來前,討論的就是過幾天歸途演出的歌單。賀嘯說要在原有的基礎上加一首,幾個人想著應該就是新歌。
而新歌他們是沒有聽過的。賀嘯這樣彈完,齊遠看向他,笑著問道。
Advertisement
“新歌?”
賀嘯:“嗯。”
“怎麼沒歌詞啊?”吉邦說。
賀嘯剛才只彈了吉他,給他們聽了曲子,并沒有唱歌。說實話,外行人聽熱鬧,行人聽門道。就剛才這一首,幾個人從里面聽出了和賀嘯以往的編曲截然不同的風格與味道。
這首曲子單聽都是好聽的,加上歌詞之后,產生的化學反應會倍遞增。
甚至說,幾個人單聽了曲子就已經格外的期待了。
吉邦這樣問完,賀嘯說:“還沒寫完。”
“歌詞還沒寫完?”吉邦說,“先前你都是歌詞比曲子快的。”
也確實是這樣的。
歌曲其實很看靈。一般來說,賀嘯會先寫出曲子的開頭,然后會將歌詞寫出來,最后再將曲子收尾,然后進行整首歌的編曲,再然后就是四個人錄歌。
吉邦這樣說著的時候,一旁一直沒有說話的小男孩突然開口說了一句。
“這首我聽過。”
幾個人正聊著呢,小男孩突然這樣說了一句。吉邦先回頭看過去,齊遠和林燁也一并回過了頭去。
“就是上次我們見面,這個哥哥拿了我的吉他,沒有唱歌。他在開頭彈了一段,就是這首剛才的開頭。”小男孩看著幾個人說。
他這麼一說,幾個人神稍稍有了些變化。平時歌聽得多,一些旋律也是聽過就忘,尤其整日和賀嘯在一起。
而被樂隊外的人單獨這麼一提醒。
他們就想起來了。
特定的人,特定的場景,特定的時間,筑基一樣地回憶搭建而起,里面的細節也就隨著搭建而起的記憶一并復蘇了。
“對。”齊遠先是想了起來。
去年差不多也是這個時候。那天他們約了在這里吃飯,第二次到了小男孩,然后給小男孩買面吃面的時候,賀嘯也是拿了他的吉他。
Advertisement
但是那次,賀嘯只抱著吉他彈了一小段。就是一小段開頭。彈了那些以后,他就停了下來。小男孩當時還問他,不唱了嗎?
他說不唱了。
那個時候,大家其實都并沒有過分的去在意這件事。賀嘯想唱歌或者不想唱歌,往往都是隨心而來的。
而這半截曲子,自從那之后,也從沒有再聽他彈過了。
他們以為這半截曲子,和平時賀嘯寫過一半就放下的曲子差不多。而沒想到,他不是放下了,而是費了一年的時間,將它完整地寫出來了。
“哇。這樣說的話,你還是先寫的曲子啊。度一年啊。”吉邦說。
說到這里,吉邦又道:“現在說起這個,我也想起來了。當時聽了這一段,我后來還跟林燁說過,這一段和你平時的作曲風格不太一樣。你平時都是比較遼闊自然的,這首曲子前面明顯有些朦朧和曖昧,我倆還說這會不會是歌……臥槽?這就是歌?”
吉邦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絮叨到了后面,他福至心靈一樣反應過來,喊了這麼一句。
而他喊完,已經徹底呆在了那里,同時看向了賀嘯。
要是以前的話,或許吉邦還不會往這方面想。但是現在想想,從去年的時候,賀嘯和唐淼認識,然后沉寂了一年,兩人到現在攜手回來。
就像是這首曲子一樣,從去年開始,中間停頓了下來,而現在最終是寫了出來。
“阿嘯。”吉邦眼神震驚地看著賀嘯,說。
“這是你第一次寫歌。”
吉邦這樣說完,旁邊林燁笑起來,道:“那肯定啊,這也是阿嘯第一次談。”
林燁這麼說完,一旁齊遠跟著笑了笑。而在其他兩個人笑著的時候,吉邦卻又有另外的覺了。
賀嘯上有一種堅定與獨屬。
這種堅定和獨屬,都是給唐淼的。
這是一種悄無聲息又令人炸的浪漫。
“真是令人的。”吉邦說。
吉邦這樣說完,又想起什麼來一樣,他看向賀嘯,睜大眼睛道。
“這樣一想,你這歌從去年夏天就開始寫了。”
“原來你在那個時候,就對唐淼圖謀不軌了。”
猜你喜歡
-
完結638 章
買一送一:首席萌寶俏媽咪
盛安然被同父異母的姐姐陷害,和陌生男人過夜,還懷了孕! 她去醫院,卻告知有人下命,不準她流掉。 十月懷胎,盛安然生孩子九死一生,最後卻眼睜睜看著孩子被抱走。 數年後她回國,手裡牽著漂亮的小男孩,冇想到卻遇到了正版。 男人拽著她的手臂,怒道:“你竟然敢偷走我的孩子?” 小男孩一把將男人推開,冷冷道:“不準你碰我媽咪,她是我的!”
116.1萬字8.18 310839 -
完結75 章

一見到你呀
1. 向歌當年追周行衍時,曾絞盡腦汁。 快追到手的時候,她拍屁股走人了。 時隔多年,兩個人久別重逢。 蒼天饒過誰,周行衍把她忘了。 2. 向歌愛吃垃圾食品,周行衍作為一個養生派自然向來是不讓她吃的。 終于某天晚上,兩人因為炸雞外賣發生了一次爭吵。 周行衍長睫斂著,語氣微沉:“你要是想氣死我,你就點。” 向歌聞言面上一喜,毫不猶豫直接就掏出手機來,打開APP迅速下單。 “叮鈴”一聲輕脆聲響回蕩在客廳里,支付完畢。 周行衍:“……” * 囂張骨妖艷賤貨x假正經高嶺之花 本文tag—— #十八線小模特逆襲之路##醫生大大你如此欺騙我感情為哪般##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那些年你造過的孽將來都是要還的##我就承認了我爭寵爭不過炸雞好吧# “一見到你呀。” ——我就想托馬斯全旋側身旋轉三周半接720度轉體后空翻劈著叉跟你接個吻。
21萬字8 9512 -
完結43 章

我的愛生生不息
雲知新想這輩子就算沒有白耀楠的愛,有一個酷似他的孩子也好。也不枉自己愛了他二十年。來
4.3萬字8 13074 -
完結6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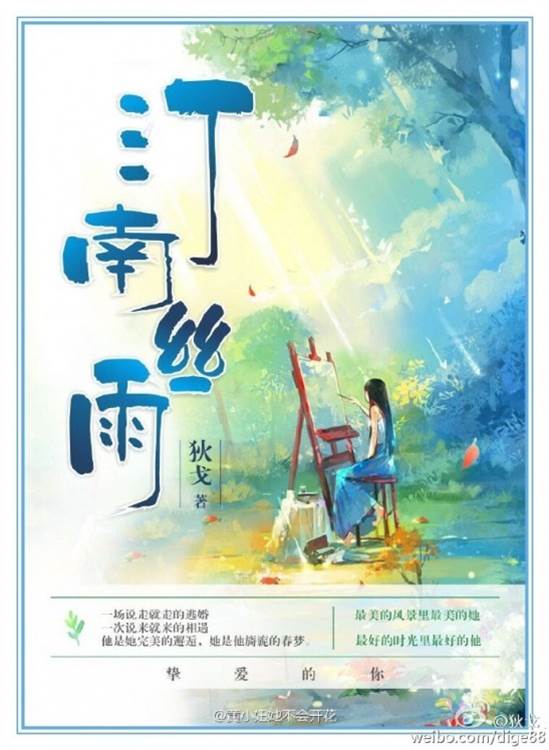
汀南絲雨
通俗文案: 故事從印象派油畫大師安潯偶遇醫學系高才生沈司羽開始。 他們互相成就了彼此的一夜成名。 初識,安潯說,可否請你當我的模特?不過我有個特殊要求…… 婚後,沈醫生拿了套護士服回家,他說,我也有個特殊要求…… 文藝文案: 最美的風景裡最美的她; 最好的時光裡最好的他。 摯愛的你。 閱讀指南: 1.無虐。 2.SC。
16.9萬字8 9132 -
完結222 章

退婚后被殘疾大佬嬌養了
真千金回來之後,楚知意這位假千金就像是蚊子血,處處招人煩。 爲了自己打算,楚知意盯上了某位暴戾大佬。 “請和我結婚。” 楚知意捧上自己所有積蓄到宴驚庭面前,“就算只結婚一年也行。” 原本做好了被拒絕的準備,哪知,宴驚庭竟然同意了。 結婚一年,各取所需。 一個假千金竟然嫁給了宴驚庭! 所有人都等着看楚知意被拋棄的好戲。 哪知…… 三個月過去了,網曝宴驚庭將卡給楚知意,她一天花了幾千萬! 六個月過去了,有人看到楚知意生氣指責宴驚庭。 宴驚庭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在楚知意麪前伏低做小! 一年過去了,宴驚庭摸着楚知意的肚子,問道,“還離婚嗎?” 楚知意咬緊牙,“離!” 宴驚庭淡笑,“想得美。” *她是我觸不可及高掛的明月。 可我偏要將月亮摘下來。 哪怕不擇手段。 —宴驚庭
60.5萬字8 334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