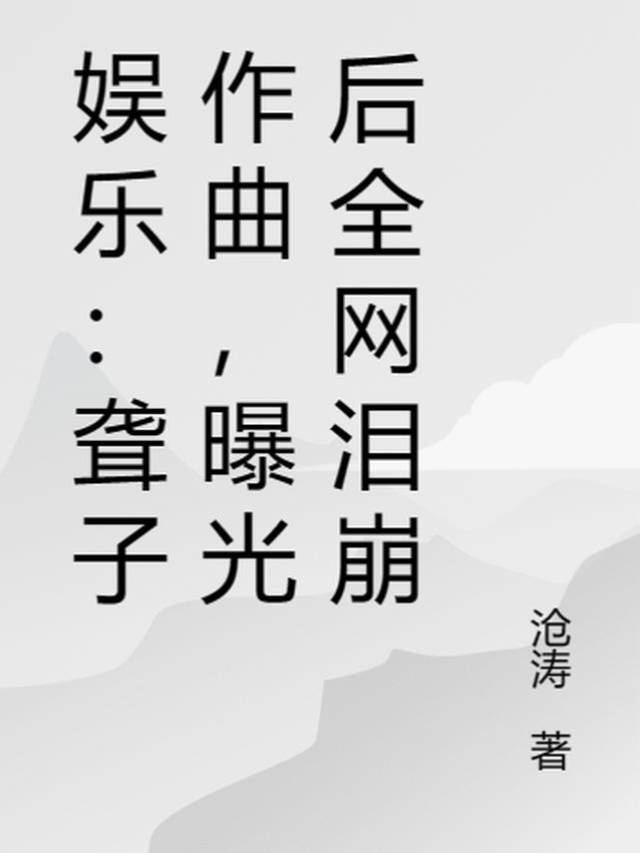《檸檬汽水糖》 第46章 汽水
我接住你
從飯店出去后,周安然都還一直在想他這句話。
飯店離livehouse不遠,他們沒有打車,打算一路步行過去。
周安然低頭跟著他后,心里還在不停揣他剛才那句話。
許是他剛才看的目太過專注溫,讓幾乎生出一種“他那句話是說給聽的”的錯覺。
可他高中連名字也記不住,大學再遇至今,也堪堪才過了一個月。
就算多想,也只敢猜他是不是也對有了一點朦朧的好。
“很喜歡”這種程度,想都不敢想。
那會不會是,他在跟說他另有很喜歡的人?
好像也不太可能,依他的格,要他真的另有喜歡的生,不可能和走這麼近,他不會舍得讓對方誤會傷心。
那就還是僅僅是在跟說祝燃?
周安然想得出神,也沒注意到前方有一個小臺階要下,一腳踏空后,才慌察覺,重心已經有些穩不住。
下一瞬,后腰被一只溫熱有力的大手摟住。
驀然撞進男生的懷抱中,屬于他的清爽氣息鋪天蓋地將包裹。
周安然怔怔抬頭向他,目和他帶笑的視線上。
“又在想什麼?”陳白問。
懷里的生像是還呆愣著,還是那副乖得讓人一看就想欺負的模樣。
陳白稍稍低頭,聲音也微微低:“跟我走路就這麼無聊,分心到路都不看了?”
周安然回神,忙搖搖頭:“沒有。”
生方才還瓷白的小臉迅速染上一抹薄紅,偏圓的杏眼干凈又漂亮,里面有沒藏住的一點慌與張。
很像那年在學校小超市,他給遞可樂時的那副模樣。
“周安然。”陳白又了一聲,“你怎麼還跟高中一樣――”
Advertisement
周安然心里重重一跳。
一樣什麼?
一樣還是很喜歡他嗎?
他還是發現了?
陳白緩緩接上后一句話:“一逗就害?”
周安然松了口氣,又沒全松。
能覺到臉正在發燙,所以不敢否認,但也不敢直接承認,因為害二字,好像就已經足夠暴些什麼了。
模棱兩可地小聲反駁一句:“有嗎?”
又輕又的一聲鉆耳朵中,生睫得厲害,又長又卷,連同剛才那道嗓音一起,像是兩把小刷子似的,在陳白心里撓了兩下。
反應過來的時候,他空著的那只手已經抬了起來。
“沒有的話――”陳白結滾了滾,手漸漸靠近那張薄紅的小臉,“臉怎麼這麼紅,耳朵也紅?”
周安然說不出話來。
旁邊的街面上還算熱鬧,霓虹燈閃爍,時而有行人從旁路過,眼神會在他們上短暫駐足片刻。
周安然都沒注意,連呼吸都屏住,只看見男生那只修長好看的手離臉頰越來越近。
三寸。
兩寸。
一寸。
心跳從沒這麼快過,又像是快懸到嗓子眼,期待與張織,有什麼像是滿脹得要溢出來。
發慌發悶的覺,像心悸。
然后那只手在離只剩不到一寸的位置堪堪停了下來。
周安然幾乎能覺到他手上的溫度。
陳白垂眸,看著白皙的小臉已經從薄紅轉緋紅,睫得比剛才還厲害,眼睛里像沁了水。
他手指了,最后轉過來,只用手背很輕也很克制地在臉上了下。
如他預想中一般又又燙。
陳白心臟像是也被燙了下,嗓音低得發啞:“我那天怎麼就完全沒看出來。”
旁邊大路上一輛紅的跑車張揚的疾馳過去,重金屬搖滾樂震天響。
Advertisement
周安然只聽清了他前三個字,心跳還快得發慌,指尖揪了揪外套下擺,臉上還殘留著剛才他手背落上來時的覺,像是給了勇氣。
“你那天什麼?”
陳白卻將手放了下來,很輕地朝笑了下:“沒聽清算了,反正也還不是時候。”
周安然:“……?”
什麼還不是時候?
陳白虛摟在腰上的手這時也松開,聲很低,聽著格外溫:“走吧。”
周安然不知怎麼,可能是心跳還得厲害,也沒再追問,只低頭輕輕“嗯”了一聲。
周安然跟他走進livehouse的時候,臺上的俞冰沁沒在排練要表演的那兩首英文歌,正在唱一首沒聽過的粵語歌,等彩排完和他們一起吃夜宵時,才知道這首歌《無條件》。
往里走近,周安然看見祝燃正坐在他們上次坐的離舞臺最近的那張卡座上。
在周安然印象中,他話一直不,下課的時候好像總是在一刻不停地在跟人說話,此時卻分外安靜,連手機也沒玩,只專注地看著臺上的人。
是以前從沒見過的模樣。
陳白輕著作拉開他后那張卡座的椅子,聲音也輕:“我們坐這邊?”
周安然正好也不想過去打擾祝燃,點點頭:“好。”
周安然坐下時,還覺得臉上被他過的地方在發燙,緩了許久的心跳,才終于能凈下心聽歌。
不知過了多久,聽見旁邊的人忽然又一聲。
“周安然。”
周安然側了側頭。
陳白看著:“上次有幾句話忘了和你說了。”
周安然眨眨眼。
上次?
上次來這間livehouse嗎?
“什麼話啊?”
他們兩人的位置是并排的,許是怕打擾到其他人,男生忽然靠近許,清爽的氣息一瞬又撲面而來。
Advertisement
周安然呼吸停了一拍。
“你很優秀,也不膽小,世界上也沒有哪條法律規定了所有人都必須要格外向――”陳白定定著,眼眸在黯淡線依舊顯得格外亮,聲音很低而堅定,“你不需要羨慕任何人。”
周安然隨意搭在桌上的指尖倏然收。
很難形容這一刻的覺。
當然知道格外向在很多久況下都更占優勢,很多時候也不喜歡自己這麼向,但如果格可以輕易變換,那也不必有外向之分。
也不是沒掙扎過,試圖改變過,但都需要用緒作為代價來換。
但是喜歡了很久的男生跟說“世界上也沒有哪條法律規定了所有人都必須要格外向”,跟說“你不需要羨慕任何人”。
這一刻,好像忽然就跟自己和解了。
向就向吧,盡力不讓這種格影響想做的事就行。
陳白忽然又開口:“而且――”
說了兩個字卻又停下來。
周安然平緩了下呼吸,這才很輕地接了句:“而且什麼?”
陳白仍看著,像是意有所指:“也許有人就喜歡你這種類型呢。”
后面俞冰沁再唱了什麼,周安然一句也沒再聽進去。
直到臺上幾人結束排練,livehouse重新安靜下來,才恍然回神。
俞冰沁和其他人一起把吉他放到舞臺后方,從臺上走下來后,先在祝燃邊上停了停:“怎麼一個人坐?”
一下來,祝燃就站了起來。
俞冰沁個子高,祝燃只大約比高半個頭的樣子。
周安然難得在他臉上看到了許張,然后就見他手一指邊上的男生:“陳白不準我跟他坐一塊兒。”
俞冰沁又走到他們卡座前,臉上依舊沒什麼明顯表,但仔細看,還是能看出一很淺的笑:“你怎麼又欺負他?”
Advertisement
陳白不不慢地瞥了祝燃一眼:“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欺負他了?”
俞冰沁像是也就隨口一說,目又轉向這邊。
周安然乖乖跟打招呼:“俞學姐。”
俞冰沁“嗯”了聲,忽然起了臉頰:“然然臉怎麼這麼紅,你也欺負了?”
后一句話明顯是對陳白說的。
周安然心跳又掉一拍。
有點想轉頭看他,又覺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好明顯。
然后聽見男生聲音在旁邊響起,比剛才多了點笑意,意味深長的語氣:“不算是欺負吧。”
周安然:“……?”
他這話里的曖昧意味實在明顯。
俞冰沁后幾人齊齊朝看過來,臉上都帶著點打趣的笑容。
周安然只覺臉好像又更燙了幾分。
樂隊鍵盤手就是上次在ktv最開始他“校草”和他打招呼的那位學姐,鐘薇,鵝蛋臉,短發頭,氣質也颯。
此刻鐘薇就靠在俞冰沁肩膀上,笑著看向陳白:“聽沁姐說你這段時間一直在跟學吉他,已經會了一首歌,要不要趁今天機會正好彈給我們聽一下啊?我還想看帥哥彈吉他的。”
樂隊幾個男生不干了。
“我們天天彈吉他你看不見啊。”
“鐘薇我跟你說,你這算是人攻擊了啊。”
“就是。”
周安然終于忍不住偏頭去看他一眼。
他什麼時候跟俞學姐悄悄學了吉他啊。
男生斜靠在椅背上,臉上帶著點漫不經心的笑意,語氣也懶洋洋的,像在開玩笑:“那不行,帥哥可不輕易彈吉他給別人看。”
鐘薇也沒生氣,只八卦地又瞥了眼周安然:“我當然知道我沒這個面子,就是不知道周學妹有沒有,看我能不能蹭個機會。”
周安然:“……?”
目一下又收回來。
雖然知道鐘薇是因為剛才他曖昧那句話,才這樣打趣,周安然心還是稍稍往上提了許。
安靜一秒。
男生聲音緩緩響起:“下次吧,還沒學會。”
“哎……看來今天是沒這福氣了。”鐘薇嘆氣。
周安然一顆心又落回來。
低著頭,肩膀也有一點點垮下來。
鐘學姐剛開始是說他已經學會了。
是鐘學姐有信息差,還是他不想彈給他們聽,所以找了托詞。
周安然抿抿。
好像又開始揪著一兩句話就胡思想起來了。
但是,很喜歡一個人的話,好像就是忍不住會對他說的每一句話去做閱讀理解。
俞冰沁聲音響起:“我們去吃夜宵,你們幾個去不去?”
“當然去。”祝燃立即附和。
陳白語氣還是懶懶散散的:“你們先走,我們等下再去。”
?
我們?
是說嗎?
周安然有點懵,不由又偏頭朝他看了眼。
剛好看見男生側頭也朝這邊過來,他下朝這邊輕輕一揚,明明是在回俞冰沁的話,目卻落在臉上沒再移開:“有話跟說,你鑰匙借我。”
周安然指尖蜷了蜷。
他還有什麼話要跟說啊?
路上那句只聽見三個字的話嗎?
“哇噢~”鐘薇推了推樂隊其他幾個男生,“快走快走,別打擾人家學弟學妹。”
俞冰沁又很淺地笑了下,從口袋把鑰匙拿出來,揚手丟給他:“不許欺負人家。”
陳白手接過:“我盡量。”
周安然:“……?”
俞冰沁一行人出去后,livehouse又重新恢復安靜。
周安然手撐在座椅上,掌心開始有點發汗。
“想聽嗎?”男生聲音很低地響起。
?
周安然側了側頭,有點沒明白:“聽什麼?你要跟我說的話嗎?”
他要跟說什麼啊。
怎麼說之前還要征求意見似的。
陳白忽地笑了下,又沖舞臺揚了揚下,“我彈吉他,想聽嗎?”
周安然一怔,眼睛稍稍睜大:“你不是說還沒學會嗎?”
“騙的。”年語氣里約又帶出幾分狂勁兒,“我怎麼可能不會。”
周安然心跳又快了一拍。
“聽就跟我去臺上?”陳白問。
周安然重重點了下頭。
上臺后,周安然一路跟他走到舞臺后方。
陳白沒其他人的東西,就只拿了俞冰沁那把吉他,隨手把繩子掛在肩上,然后又走到臺前,在舞臺邊緣坐下。
猜你喜歡
-
完結2195 章
首席的獨寵新娘
一場別有用心的陰謀,讓她誤入他的禁地,一夜之後卻被他抓回去生孩子!父親隻為一筆生意將她推入地獄,絕望之際他救她於水火。他是邪魅冷情的豪門總裁,傳聞他麵冷心冷卻獨獨對她寵愛有佳,可一切卻在他為了保護另一個女人而將她推向槍口時灰飛煙滅,她選擇帶著秘密毅然離開。三年後,他指著某個萌到爆的小姑娘對她說,“帶著女兒跟我回家!”小姑娘傲嬌了,“媽咪,我們不理他!”
431.7萬字8.33 195062 -
連載2623 章

閃婚夫妻寵娃日常
顧時暮是顧家俊美無儔、驚才絕艷的太子爺兒,人稱“行走荷爾蒙”“人形印鈔機”,令無數名門千金趨之若鶩。唐夜溪是唐家不受寵的大小姐,天生練武奇才,武力值爆表。唐夜溪原以為,不管遇到誰,她都能女王在上,打遍天下無敵手,哪知,遇到顧時暮她慘遭滑鐵盧…
448.4萬字8.18 139421 -
完結1277 章

偏執小舅,不許掐我桃花!
整個海城的人都以為,姜家二爺不近女色。只有姜酒知道,夜里的他有多野,有多壞。人前他們是互不相熟的塑料親戚。人后他們是抵死纏綿的地下情人。直至姜澤言的白月光回國,姜酒幡然醒悟,“我們分手吧。”“理由?”“舅舅,外甥女,有悖人倫。”男人冷笑,將人禁錮在懷里,“姜酒,四年前你可不是這麼說的。”一夜是他的女人,一輩子都是。
173.8萬字8.46 39115 -
連載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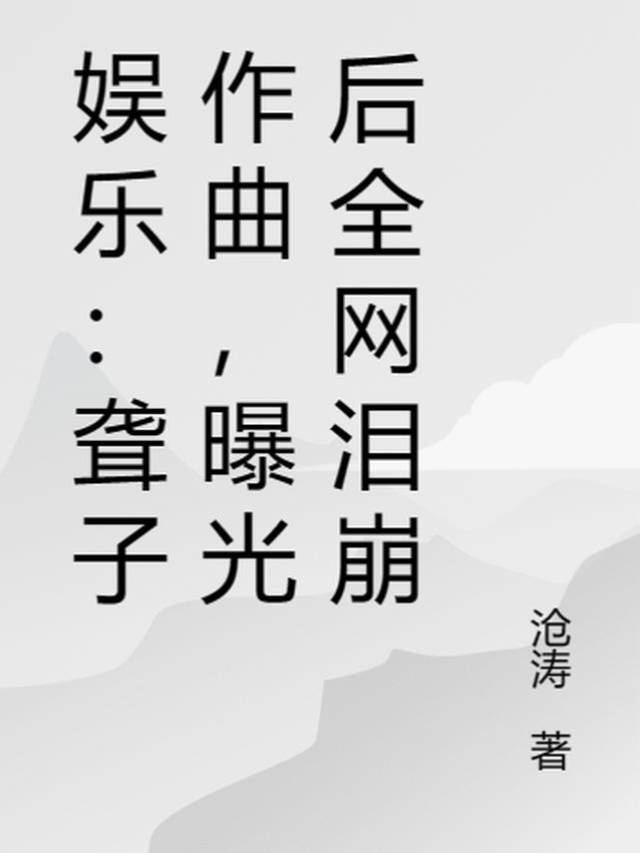
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
微風小說網提供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在線閱讀,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由滄濤創作,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最新章節及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就上微風小說網。
23.8萬字8.18 56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