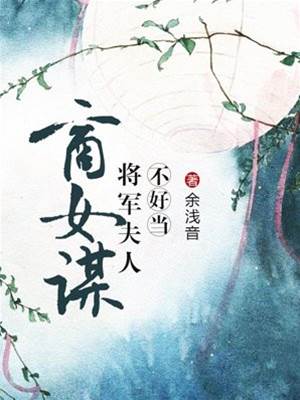《逐鸞》 第65章 第 65 章
天未名,荔知便宮點卯了。
守城的將士看過的腰牌,下一揚,示意可以通行。
進了宮門,就必須步行。荔知下車的安門,到的署徒步需要兩炷香時間門,是最近的路線。
系為皇后服務,屹然是一個小版的朝廷。的衙,看上去和普通衙門沒多區別,只是細微之多了些溫婉和優。
荔知的職是正六品司正,隸屬于宮正司,主要工作是輔佐上峰宮正,監督戒令宮和嬪妃——但大多數況下,宮正司對嬪妃的違之舉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畢竟,誰能說得準明日得寵的是誰呢?
由于主要工作的對象是宮,所以在宮正司任職,能獲得至絕大部分宮的尊敬和討好。
荔知上任一天,迅速清了頂頭上司馬宮正的喜好。
馬宮正再過兩年便出宮了,事頗為圓,看樣子只想安穩過完這最后兩年。宮正之下,是司正,除了荔知還有一名司正,由于荔知的出現很可能讓升任宮正的事出現變化,這位司正對不冷不熱。
第一天上任,宮正司本的工作沒什麼好說的,除了忙還是忙。
不悉宮規的小宮無意之中違背了宮規,被有心之人狀告到宮正司;兩個或是一群宮之間門產生糾紛,要宮正司主持公道;低位嬪妃得罪高位嬪妃,高位嬪妃便將宮正司當槍使,用莫須有的罪名去懲戒低位嬪妃……這樣的事,荔知第一天上任便見識了不。
從天不亮就進宮,一直到傍晚下值,始終沒有時間門吃一口飯。
宮中,是唯一一個可以宿在宮外的,若好心道別,反而顯得有意炫耀,令人心中起不平波瀾。所以荔知只和馬宮正告了退,無聲無息走出宮正司。
Advertisement
原路返回安門,下馬的石碑前已經列了一排迎接主子回家的馬車或是駿馬。找到自家馬車,正要上車,停在旁邊的馬車窗戶卻忽然開了,一張白皙高冷的面容了出來。
“……殿下?”荔知口而出。
謝蘭胥坐在馬車里,神淡淡地看著。
“上來。”
謝蘭胥的馬車夫連忙要為準備馬凳,謝蘭胥卻從車門探出子,直接向出了手。
荔知握著這只手,稍一用力便上了馬車。
坐進馬車后,荔知驚訝道:“阿鯉,你怎麼會在這里?”
“順道。”謝蘭胥睨了一眼,似乎在說問了個愚蠢的問題,“我也在宮里任職,你忘了麼?”
荔知啞口無言。
大理寺的署確實在宮里,但皇宮分前朝和后宮,他在前朝任職,下值了走春雨門回郡王府最快,要想在安門前和“偶遇”,只可能是下值了走春雨門出宮,然后再繞一大圈,回到安門前。
但謝蘭胥都說了順道,難道還能穿他特意來等的不?
荔知只能十分配合地笑道:“是我忙暈了頭……”
“看得出來。”謝蘭胥說,“走罷。”
“去哪兒?”
“瑯琊王府。”
就這樣,剛剛下值準備回家的荔知在皇城門口被攔截,莫名其妙地,就來了瑯琊王府。
瑯琊王府前是個崔朝的大將軍府,將軍獲罪抄家后,這棟違制的奢華宅邸一直閑置,直到燕朝時,被改造為王府,賜給了謝蘭胥。
同荔宅水鄉一般溫多的風格不同,瑯琊王府的調以肅殺沉穩為主,各房各院也是以星宿的名字命名,謝蘭胥一樣未,全都保留了下來。
荔知從大門一直走到正院,除了門房沒見一人,普通富戶也有十幾人伺候,更不用說皇室中人。
Advertisement
進了正院,荔知才看到婢的存在。還是那兩張悉的面孔,桃子和西瓜。
忍不住詢問,卻得到謝蘭胥簡單三個字:“習慣了。”
他領著荔知走進臥房,和其他地方給的覺一樣,謝蘭胥的臥房也是空的,只有最簡單的家,讓不由想起了鳴月塔時的竹園。
謝蘭胥帶著在屋子里轉了一圈,也沒說話,轉完便走出了臥房。
荔知后知后覺,生出一個不可思議的念頭——他不會是在帶參觀新家吧?
猜得沒錯,謝蘭胥幾乎帶逛完了整個瑯琊王府。
最后又回到了主院。
這時,食桌上已經擺好了熱氣騰騰的茶,一個四層的八角螺鈿食盒。
“吃罷。”謝蘭胥率先在食桌上坐了下來。
“這是……”荔知愣了愣。
“看你臉,今天應該沒有吃東西。”他神平靜道,“府里沒有庖丁,我讓人去酒樓里買的招牌菜。”
出宮后,荔知已經得腹痛了,但一直忍著沒說,想等回府說再隨便吃點填飽肚子。
以為自己將這點不適藏得很好,沒想到謝蘭胥早已經看在眼中。
不是看在眼中。
“你嘗一嘗,看吃得慣麼。”謝蘭胥說。
荔知揭開食盒,謝蘭胥的目鎖定在上,留神著的反應。
食盒最上一層,擺滿致的點心,有金的合意餅和白葡萄,餞青梅,杏仁佛手。第二層,則是各式前菜,有白綠相間門的口蘑白菜,也有看上去就鮮辣開胃的麻辣和涼拌小黃瓜;第三層是主菜,澤金黃的烤鴿讓人食指大,蓮藕排骨湯,芳香撲鼻。最后一層,則是主食,既有餑餑,也有香稻飯。
四層食盒揭開來,荔知已經開始不由自主咽口水。
Advertisement
拿起長箸,毫不猶豫地夾起了烤鴿的大。
鴿出乎意料地遞到謝蘭胥的邊,荔知笑瞇瞇地看著愣住的謝蘭胥,說:
“阿鯉,張——”
謝蘭胥沒反應過來,下意識便聽話張開了。
荔知喂給他鴿,像是完了什麼大事,心滿意足地又夾起一筷鴿子,這回才放自己口中。
謝蘭胥回過神來,默默咀嚼著口中的鴿子。
“好吃麼?”荔知偏頭看著他。
謝蘭胥點點頭。
“……我也覺得好吃。”荔知笑了,“可能是因為有阿鯉在吧。”
荔知舀了兩碗飯,遞給謝蘭胥一碗,是要他陪自己吃飯。
謝蘭胥流于表面地拒絕了一回,被荔知用一塊蓮藕堵住了,然后便乖乖陪同用飯了。
用完夕食,夕也沉了地底,取而代之的是一皎潔的彎月,高高懸掛在京都的天空中。
京都的夜空總是混混沌沌的,繁星雖有,但并不明亮。
更別提鳴月塔那般貫穿天空的銀河。
兩年前的荔知,絕對想不到自己有一天會想念鳴月塔的天地。
捧著一杯熱茶,正在廊下眺夜空,旁的謝蘭胥忽然開口:
“兩日后是冬至,朝廷放假一日。”
這沒頭沒尾的一句話讓荔知接不上去,只能糊弄了一聲“嗯?”
“我聽說,”謝蘭胥繼續慢慢道,“冬至要吃羊火鍋,否則來年死無全尸。”
荔知:“……”
哪里來的歹毒說法?東宮特嗎?
“我府中無人會做羊火鍋。”謝蘭胥面憂郁。
……懂了。
荔知笑著說:“我本來就打算請你在冬至那天來我宅上吃羊火鍋和年糕,火鍋要人多一起吃才熱鬧。阿鯉不會不給我這個面子吧?”
Advertisement
“既如此,”謝蘭胥從善如流,“那就叨擾了。”
謝蘭胥喝了一口手中的熱茶,說:
“般般請我吃火鍋,我也請般般看一場熱鬧。作為晚上的開胃前菜。”
“什麼熱鬧?”
……
謝蘭胥所說的熱鬧,一般人真想不到。
朱靖出殯當日,正好是冬至節假。申時剛過,荔知便來到朱府門口。朱家老爺至三品禮部尚書,掌科舉之路,自然多得是人想要和他拉上關系。
朱府門前,人山人海。
若不是門口掛著白燈籠,說是盛大的壽宴也不為過。
荔知向門口登記的管家了禮包,說明了份,輕輕松松地了朱家大門。
和朱家并無關系,但上趕著來吊唁的人不止一人,荔知混在其中,并不突兀。
一邊往里走,一邊尋找謝蘭胥的影。一個悉的影住了,是謝蘭胥邊的婢桃子。
在桃子的帶領下,荔知找到涼亭中的謝蘭胥。
也不知道他是怎麼找到這樣一個地方的,僻靜低調,卻又能從錯的游廊和掩映的樹枝中,窺探到靈堂那邊的景況。
謝蘭胥坐在亭子里,神淡然,荔知習以為常地握住他出的手,謝蘭胥輕輕一拉,將帶往邊坐下。
“那就是朱家老爺,禮部尚書朱清海。旁邊那人,想必不用我介紹了。”謝蘭胥眼神所指,是靈堂前一位鶴發皮,眾人簇擁的老人。
在朱清海旁,是特意穿得很是素淡的敬王謝敬檀。
朱清海神憔悴,雙眼紅腫,傷心之意不似作假。不知謝敬檀對他說起什麼,他悲從中來,提起袖口拭奪眶而出的眼淚。謝敬檀安地輕拍他的肩膀。
“這就是你說的熱鬧?”荔知問。
“想看熱鬧,得先替我辦一件事。”謝蘭胥說。
荔知就知道,無事不登三寶殿,謝蘭胥怎麼可能無緣無故帶來看朱家出殯?
聽了謝蘭胥的要求,荔知這才明白他這是在有的放矢,怪不得要帶來呢。
兩人暫時分頭行。
荔知慣會討人喜歡,謝蘭胥給的任務對來說并不難。
半個時辰后,在朱靖的靈前上了一柱香,正打算離開靈堂去向謝蘭胥報告,一個小廝忽然驚慌失措地沖進靈堂:
“老爺,不好了!柴房燒起來了!”
“什麼?!”朱海清大吃一驚,“還不快讓人滅火!”
聽說府中走水,來吊唁的賓客都驚慌失措地往外跑。
柴房和靈堂都在前院,若是火勢控制不住,燒來靈堂是極有可能的事。就連朱海清自己都知道此事不可疏忽,小心起見,連忙護著敬王往院外撤退了。
荔知正想走,謝蘭胥不知從哪兒冒了出來。
“阿鯉!快走,柴房走水了——”
謝蘭胥不慌不忙地應了一聲:
“我知道。”
荔知忽然間門明白了柴房忽然走水的原因。
一邊頻頻回頭查看有沒有人突然走進靈堂,一邊屏息凝神看著謝蘭胥毫不避諱地推開了朱靖的棺木。
“你在做什麼?”荔知難以置信。
“看死人。”謝蘭胥抬頭瞥了一眼,“你看麼?”
荔知:“……”
多謝,但不必了。
眼見著遲早有人要進來查看靈堂狀況,荔知不斷催促,謝蘭胥終于合上了棺木,狀若平常地和荔知一起走出靈堂。
朱府家丁都在忙著滅火,朱海清和謝敬檀第一時間門轉移去了安全的地方。
沒有人注意到從靈堂中遲遲走出的二人。
“你看到了什麼?”荔知問。
“大理寺的驗尸結果說,朱靖死于后腦重敲打導致的頭骨碎裂。棺中朱靖的死相卻是口大張,面紺紫,眼球凸出。脖子上明顯的十手指印痕。”
“你是說,朱靖是被人掐死的?”荔知驚訝道。
“如果朱靖是被掐死的,”謝蘭胥說:“白秀秀一個弱子,如何能夠掐死一百八十斤重的朱靖?”
這個問題讓荔知陷深思。
“這就有趣了。”謝蘭胥微笑起來。
兩人在混中走出朱府,坐回馬車后,謝蘭胥取出一張素帕反復拭剛剛過棺木的手,淡淡道:
“說吧,你都發現了什麼。”
猜你喜歡
-
連載1364 章

神醫嫡妃世無雙
雙潔+虐渣爽文+男女強+萌寶。 醫學界天才大佬南晚煙,一朝穿成草包醜女棄妃。 剛穿越就被渣男王爺打成了下堂妃,所有人都嘲諷她活不過三天! 不想她卻帶著兩個可愛萌寶,強勢歸來,虐的各路渣渣瑟瑟發抖! 至於渣男王爺,和離! 他冷嗬:“求之不得!” 可等到她帶萌寶要走時,他卻後悔了,撕掉和離書! “冇這回事,這是保證書,疼王妃愛女兒,三從四德好男人。” 她咬牙:“顧墨寒!” 他跪下:“娘子,我錯了……”
251.4萬字8 988516 -
完結4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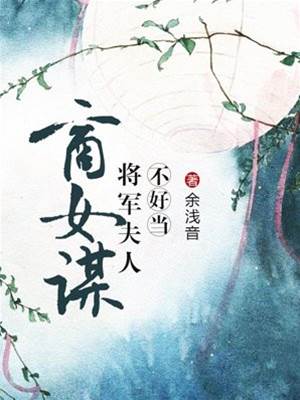
商女謀:將軍夫人不好當
一朝穿越,成為當朝皇商之女,好在爹娘不錯,只是那姨娘庶妹著實討厭,真當本姑娘軟柿子好拿捏?誰知突然皇上賜婚,還白撿了一個將軍夫君。本姑娘就想安安分分過日子不行嗎?高門內院都給我干凈點兒,別使些入不得眼的手段大家都挺累的。本想安穩度日,奈何世…
81.5萬字8 35794 -
完結142 章

三十六陂春水
朱晏亭是聲威赫赫的章華長公主獨女,身世顯赫,嬌矜無匹。從小就是內定的皇后,引眾女艷羨,萬人矚目。可自從她母親過世后,境遇一落千丈。在家無依無靠,皇帝表弟還一直想悔婚。遲遲沒有定親事,活生生將她從一則美談拖成了一則笑談。…
40.7萬字8 8988 -
完結407 章
暴君納妃當日我孕吐了
(提醒偏古早虐心文,介意勿入。)文瑾跟了大暴君傅景桁七年。人前她是深受寵愛的龍寢伴讀,背后卻被人嘲笑無名無份,只是一個被御駕玩弄的賤婢。多年伴寢,始終沒有換來三宮六院中一席安身立命處,反而換來他一句“朕要納妃了,你明日去跪迎。”當日新妃子下轎,左一句“騷狐貍味兒”,右一句“人家要君上抱進去”。矯情勁兒讓文瑾當場孕吐。“嘔……”所有人都覺得她御前失儀,瘋了。文瑾卻摸摸小腹,狗男人,到你后悔的時候了。她拎包袱帶球走人,從此踏上一條獨自美麗的巔峰路子。手刃弒母仇人,教養年幼姊妹弟兄,做買賣當富商,無數青年才俊爭相給她腹中孩子做后爹。傅景桁盯著她八月孕肚質問,“你不是說過非朕不嫁的嗎,如何懷了別人的種?”她云淡風輕,“玩你玩膩了,狗皇帝。”他遣散佳麗三千,屈膝跪地,紅了眼眶,“不玩了。來真格的。嫁給朕做皇后”她微微一笑,“想當后爹?排隊”傅景桁環視眾人“讓一下,朕插個隊。”
89萬字8 467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