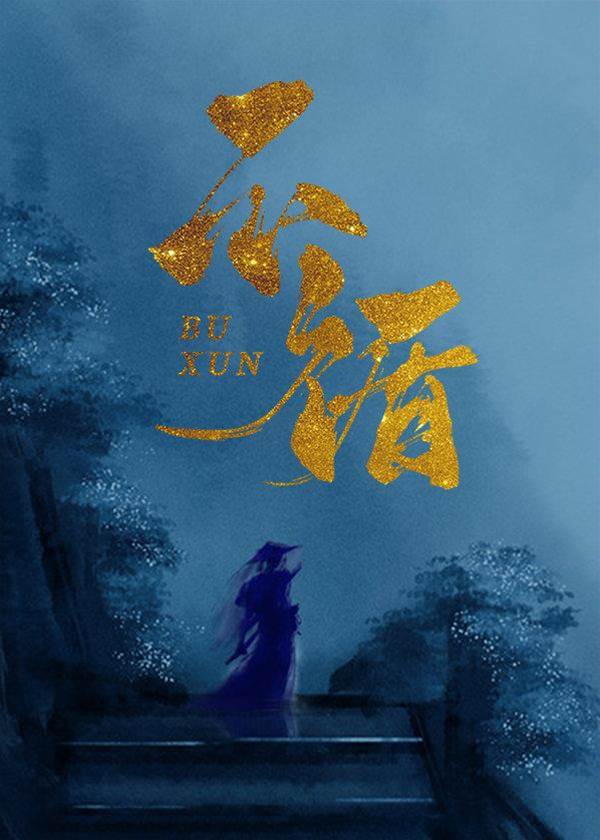《得罪未來帝王后》 第61章 第 61 章
眾人的視線從謝彌的臉上,慢慢地轉到了沈夷的臉上。
沒想到在外強勢不羈的襄武王,在家里居然是個腳蝦。
也不知道不食人間煙火的沈郡主到底有多厲害,居然把堂堂襄武王馴這樣,瞧瞧給人家小王爺嚇得,真是好手段!
沈夷被看的,臉上比沈南拂還燙。
長這麼大,出風頭常有,出洋相還是頭一回,臊的滿臉通紅,努力安焦躁不安的謝彌:“你說什麼呢?我何時說過不要你?”
搞得跟把謝彌給待了似的,討厭!
不敢讓謝彌再張,轉頭看向昭德帝,沉聲道:“陛下,我們家小王爺和沈南拂互不相識,甚至未見過幾回,是心思歹毒,蓄意構陷我們小王爺!此事絕不能姑息,還陛下嚴懲!”
哎呀,潺潺說他是‘我們家小王爺’,謝彌耳朵不好意思地紅了起來,慢慢咧開角,歡喜得不知如何是好。
可憐沈南拂一番唱作俱佳的賣力表演,謝彌就沒往那里瞄一眼,真是拋眼給瞎子看了。
事已經鬧到這個份上,若是不襄武王府,沈南拂哪里還有活路?
咬了咬牙,垂死掙扎地起袖,出兩段雪臂上的青紫淤痕,冷笑道:“若真是構陷,臣上的這些痕跡又是哪里來的?方才小王爺宴上消失不見了一段時候,又是去了哪里?敢問王妃是否能解?”
這痕跡懂眼的人一瞧就是男歡好所留,而且謝彌方才飲了不酒,的確出去了一段時間,醉酒倒有可能,何況沈夷和沈南拂的確相似,有子會拿名節開玩笑的。眾人微怔了下,目不由帶了些猜忌。
謝彌面發冷,正要開口,沈夷只知道間接死自己母親沈南拂定然是不可信的,下意識地護著謝彌,搶先一步開口:“方才出去的人那麼多,難道就憑小王爺也出去了,就能證明他是與你私會去了?”
Advertisement
沉聲道:“我信小王爺。”
謝彌目落在上,再容不下旁人,他心尖熱流滾過,燙的他眼眶酸脹。
沈南拂眼皮猛地一:“王妃既信小王爺,何不問問小王爺方才出去做了什麼?莫非王妃不敢?!”就不信謝彌能說出沈景之的事!
謝彌正要說話,門外傳來沈景之的聲音:“小王爺和我在一。”
沈南拂不可置信地睜大了眼。
他淡淡看向沈南拂:“小王爺酒后不適,我陪著他出去散了散,你還有什麼問題嗎?”剛才的事兒涉及宮妃,沈景之自然不好明說。
沈南拂見他出面作證,臉慘白的厲害,一下委頓在地上。
他是沈夷親哥,又是出了名的寵妹狂魔,他都出來作證謝彌清白,旁人這下再無疑慮,忍不住在心中暗罵沈南拂歹毒,為了攀高枝,竟使出這樣下作的手段!
就這般蛇蝎子,還是江南明珠,還好意思和沈夷并稱雙姝?呸!
江談其實還準備了證人證,但見沈景之一出來,他便知道大勢已去,很是果斷地丟卒保車,這時候只垂眸不語,連保一下沈南拂的意思都沒有。
沈景之對誰設的局心知肚明,只是眼下證據不足,不好當場發作,便只對著昭德帝拱手:“沈南拂只為一己私,便敢肆意妄為,構陷一地郡王,還請陛下做主,發落了。”
昭德帝靜默片刻,先未看沈南拂,帶著冷厲的眼風狠狠地從江談上刮過,這才抬了抬手,喚人把癱在地的沈南拂拖了下去。
他本有意借著這場送別宴和謝彌和緩一下關系,結果鬧的這麼難看,誰都沒心思再宴飲了,昭德帝走了個過場,匆匆宣布宴散。
待出了樓船,昭德帝看了眼垂手侍立的江談,淡淡道:“近來北戎頻頻擾邊境,你為太子,也不好在建康安富貴,去劍南邊界歷練歷練吧。”
Advertisement
太子是一國儲君,派太子去正在打仗的邊關,這也算是奇聞了,偏江談一言未發,淡漠地應了個是。
昭德帝對他當真失頂,連看也不看一眼,徑直甩袖而去。
......
沈夷和謝彌回到馬車,就憋不住氣了,拉著謝彌一通分析:“方才沈南拂分明是了江談指點,蓄意要壞你名聲!”
謝彌心不在焉的:“嗯嗯。”
攥了攥拳頭:“江談肯定不只是為了拈酸吃醋那點事,他必然還有別的打算,之前路上遇到的盧氏子,說不定也是他安排的!你要是一怒殺了盧氏子,必然得罪世家,要是忍不發,那肯定得小人侮辱!”
謝彌沒在意說了什麼,只一雙眼睛不住往臉上瞟:“你說得對。”
沈夷緒高漲,越說越氣:“那什麼盧家子,仗著祖蔭才能混吃等死罷了,也敢來下你的臉,氣死我了!”
想到盧氏子話里話外罵謝彌出低賤,人又土鱉,簡直氣不打一來!憤怒地拍桌:“明兒我就把料子取出來,給你做五六十好裳,你一天三頓換著穿,看那群人還敢不敢狗眼看人低!”
其實謝彌老是被這些浮浪世家子鄙視也不是沒緣故,他雖然有錢,但平時也不怎麼收拾自己,服攏共就這幾,佩飾也就幾樣,全靠材和貌撐著,所以在他和沈夷定親之后,常有膏粱子弟拿這點在背后笑話他。
除卻幾新郎喜服,他最近一次做新裳,還是來建康之前,為了見神采奕奕地見沈夷,特意趕制了幾,要不是為著這個,他一年也做不了三五。
家里有間專門放裳的小院,他的裳就夠塞個角落,其余全沈夷的裳首飾,想起這個就郁悶。
Advertisement
心中惡氣略出了一半,才發現謝彌心不在焉的,忍不住了他腦門一下:“你啞了?怎麼不說話呀?”
罵人的時候沒個捧哏的,真是憋死人了!
謝彌仿佛才回過神來,慢吞吞的:“哦...”他抿了抿,帶了點期待看,又不確定地問:“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
沈夷被他問的怔了怔,想也沒想就道:“我們是夫妻啊。”
謝彌急了,他聲音急促,著點慌:“大街上你護著我,只是因為我們是夫妻?方才你當著那麼多人的面說信我,也是因為我們是夫妻?你因為別人算計我發火,要給我做新裳,也只是因為夫妻的緣故?!”
“如果是別人和你做夫妻呢?如果是那姓寧的和你親呢?你也會對他一樣好?”他深吸了口氣,賭氣似的狠狠別過臉,冷冷道:“若只是因著這個,你以后不必管我了,我也不稀罕。”
沈夷不知道他又在擰個什麼勁,但對他這個假設很不喜歡,不悅道:“我為什麼要和別人做夫妻?向我提親的人多了去了,我又不喜歡他們。”
謝彌原本垂下的眉眼瞬間揚起,眼尾竟飛揚起了起來,他飛快地轉過頭。
他心頭仿佛有一只橫沖直撞的猛,幾乎讓他不能正常開口,他張合了幾下,終于問出了耿耿于懷這麼久的:“那你喜歡...”
“你啊。”
沈夷很自然地回答,就好像一呼一吸,一飲一啄那麼自然,甚至不需要經過思考。
謝彌覺自己整個人都漂浮起來,仿佛趴在云端,臉上又燙又,簡直不知該如何是好。
潺潺也喜歡他。
不是激,也不是容,而是真真切切的喜歡。
Advertisement
他嗓音又帶了點哽咽,竭力鎮定地道:“我也,我也...我也是,不,我喜歡你比你喜歡我更多。”他臉上仍漲熱,卻還是抬眸直視著:“永遠如此。”
什麼喜歡不喜歡的,死人了,說完之后,臉上才有點發燒,掏出帕子來,借著汗的作遮擋自己暈紅的臉頰。
瞧見謝彌的臉紅了一個大番柿,臉紅的比還要厲害,心里一下子就平衡了。
甚至有膽子逗謝彌,慢慢地靠向他肩頭,在他耳邊慢騰騰地吹了口氣:“不能拿說說,得看你怎麼做。”
角翹了翹:“以后看你表現了。”
做?
謝彌心激,毫無防備的,了。
自大婚那日失敗的同房之后,沈夷嫌棄他嫌棄的要死,每回他略有親近的意思,不是瞪眼就是扁,謝彌卻食髓知味的,早要憋死了。
眼下氣氛正好,那他是不是可以...
謝彌唔了聲,不自在地了耳朵:“大街上呢,咱們回家再說這個。”
沈夷:“?”
謝彌剛到家里就裝不下去了,抄起就回了寢屋,托著的腰把放到了床榻之上。
他呼吸急促,眼睛眨也不眨地瞧著:“你之前給我的那些書,我都看完了。”
沈夷想了想,才反應過來他說的是那些避火圖,不好意思地哦了聲。
謝彌記很好,理直氣壯地道:“你之前說了,等我看完那些就跟我好,你說話不能不算話啊!”
沈夷不了跟他這麼大喇喇地討論這個,捧著發燙的臉,嗔道:“你先去洗漱!”
謝彌知道病多,幸好后面就修了一溫湯池子,他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畢。
磨磨蹭蹭地洗漱完,見他難得乖順,又豎起三手指,昂著下:“咱們得先來約法三章,你不準太用力,也不準時間太長,我要是喊停,你就得停下來,記住了嗎?”
謝彌眸閃了閃,佯做乖巧地嗯了聲:“你說什麼就是什麼。”
由于天太暗,沈夷沒看清他后搖晃的狼尾,十分天真地信了他的鬼話。
抿了抿,低著頭小聲道:“那,那你把蠟燭吹了吧。”
猜你喜歡
-
完結195 章

半城風月
她來自鐘山之巔,披霜帶雪,清豔無雙,於"情"之一事,偏又沒什麼天賦,生平最喜不過清茶一杯,看看熱鬧. 都說她年少多舛,性格古怪,其實她也可以乖巧柔順,笑靨如花. 都說她毒舌刻薄,傲慢無禮,其實她也可以巧笑倩兮,溫柔可親. 不過—— 她·就·是·不·樂·意! 直到那天,她遇見了一個少年. 半城風月半城雪,她一生中的所有風景,都因他而輝煌了起來. …
42.6萬字8 4584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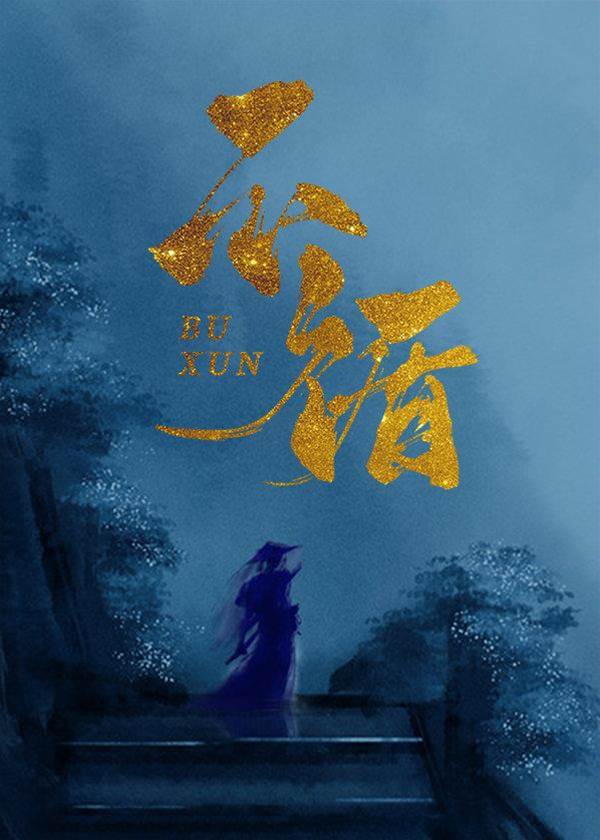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45845 -
完結727 章

繡南枝
前世遭渣男陷害,她被活活燒死,兄父剖肚點燈,她恨。再睜眼,重回家族危亡之際。她染血踏荊棘,走上權謀路,誓要將仇敵碾碎成沫。素手執棋,今生不悔。看蘇家南枝,如何織錦繡,繡江山……
123.6萬字8 2372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