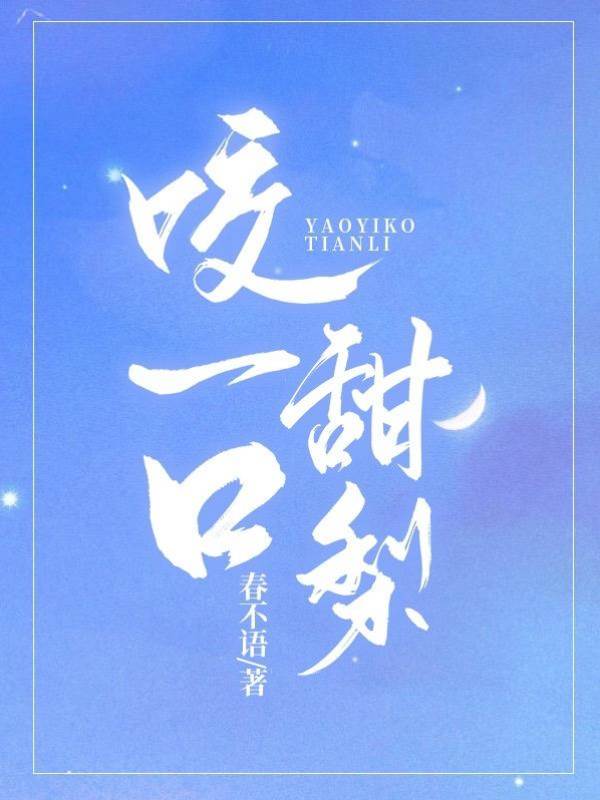《冬宜》 第123章 日常(1第)(捉蟲)
送走紀凌薇和肖樺他們這些嘉賓,溫見琛和裴冬宜回到別墅。
抱著裴鴛鴦里外走了一遍,看看他們有沒有落下東西,結果發現還真的有。
肖樺的藍牙耳機,謝薇媛的單反相機儲存卡,寧濤的手機數據線。
“好家伙,一家落一樣,趕讓他們都回來。”溫見琛開玩笑道。
裴冬宜笑得不行,把裴鴛鴦放下來,掏出手機把東西拍下來,發到群里,大家要地址,明天給他們寄過去。
裴鴛鴦跟在他們旁邊,東張西,仿佛有些不安,喵喵了好幾次。
“寶貝,不是大家都不見了,是他們回家去了,我們下次去找他們玩,ok嗎?”裴冬宜蹲下來,捧著它的臉解釋道。
裴鴛鴦喵了聲,一頭扎進懷里。
溫見琛覺得奇怪,“……它這是什麼意思?”
“它發現家里了很多人,以為大家都不見了。”裴冬宜解釋道,又將它抱起來,“它很聰明的。”
溫見琛忍不住笑起來,手將大貓抱過來,rua了它一把,“過兩天就習慣了。”
從樓上面向后花園的房間的臺看下去,當初布置的月亮燈依舊在兢兢業業地散發著芒,但夜寂靜,別墅里靜悄悄的。
那些熱鬧的過往仿佛歷歷在目,裴冬宜難掩惆悵之,“還是趕回去吧,這里太安靜了,我不太舒服。”
從熱鬧沸騰的朋友相聚回歸平靜如水的日常,就如同由奢儉,是件有些困難的事。
溫見琛微微一笑,告訴:“我明后天值班。”
“嗯?怎麼連著值兩天?四十八小時?”裴冬宜一愣,惆悵瞬間被拋到腦后,“難道明天要我一個人收拾行李嗎?”
“換班了。是只有你一個人監工。”他將裴鴛鴦放下來,手摟住往他們臥室走,“你得人過來,將行李搬回天街府,然后看看別墅的布局,有不喜歡的地方,約設計師過來看看怎麼改。”
Advertisement
“不改了吧,都好的,反正我們也不會經常在這邊住。”裴冬宜覺得麻煩,索拒絕。
溫見琛聽了就逗:“萬一我們心來,想過來二人世界,鴛夢重溫呢?”
“那就直接溫啊。”裴冬宜笑嘻嘻地反問,“那麼大一個臥室,還不夠你溫嗎?”
此時隨著嘉賓們的離開,別墅里的攝像機已經被全部拆除,雖然了那些黑的鏡頭有些許不習慣,但更多的是自在,因為這意味著別墅徹底了他們的私人空間。
做什麼都不用害怕一不小心就被錄下來了。
溫見琛低頭,在二樓的欄桿邊和擁吻,的背后就是燈明亮璀璨的水晶大吊燈,線映在的臉上,襯得面孔愈發晶瑩剔。
他抬手輕上的臉,低聲的名字:“秋秋。”
裴冬宜睫一,低低地嗯了聲。
然后聽見他問:“你想怎麼鴛夢重溫?只要臥室就夠了嗎?”
裴冬宜臉孔瞬間漲紅起來,被他這麼一提醒,才發現自己剛才那句話其實是有歧義的。
“不、不是……我……”支支吾吾的,話都說不全,抬手抓住了溫見琛的手掌。
到他無名指上的那枚戒指,那是他們的婚戒,男戒的中間鑲嵌著一枚公主方鉆石,呈菱形擺放,兩側對稱抹鑲一顆小圓鉆,看起來很低調,又有一點小酷。
溫見琛見低著頭像在躲閃什麼,心里暗自好笑,愈發想要逗。
于是故作正經地點點頭,“確實,在臥室就夠了,不然怎麼能鴛夢,做夢做夢,不睡怎麼行。”
被他這麼調侃,裴冬宜更不好意思了,連忙手去堵他的,“……閉!不許說了!不然要你好看!”
Advertisement
“你怎麼要我好看,揍我一頓還是怎麼樣?”溫見琛眉開眼笑,仿佛對這件事興趣很大,一邊問一邊拖著往臥室走,里還說,“來來來,讓我見識見識。”
裴冬宜甩了兩下,沒能甩他的手,只好回頭喊裴鴛鴦救命。
裴鴛鴦它是個憨的呀,雖然聽不懂媽媽說的什麼,但它聽得懂媽媽它名字了,媽媽的聲音又很慘的樣子,可惡,媽媽被欺負了!
在爸爸和媽媽之間,裴鴛鴦還是選擇媽媽的,于是它小跑過來,縱一躍,本來想跳到溫見琛頭頂上去薅他頭發,結果它對自己最近的重估算錯誤,力不足,最后只掛在溫見琛的背上,用爪子勾著他的服。
背后多了一個十幾斤重的秤砣,溫見琛那一個無語,咬牙切齒地罵:“裴鴛鴦你膽了是吧!給我下來,不然明天就吃貓火鍋!”
裴鴛鴦:“嗷嗷嗷——”
它的爪子勾在了溫見琛的服上,這回換它可憐兮兮地向裴冬宜求救了。
裴冬宜忍俊不,上前將沉甸甸的大貓解救下來,再一看溫見琛的服,都已經被抓得了,不嘆口氣:“不能穿了。”
溫見琛一把拉住,出猙獰的笑意:“那正好,債母償,我好好跟你說說要怎麼賠我。”
說完就把人拉進了臥室,裴鴛鴦想進去,剛探進去半個頭,就被溫見琛彎腰用手往外一推,門在它面前關上了。
裴鴛鴦嚎了聲:“喵嗚——”
沒人搭理它,只有小狗迪克跑上來,聞聞它,像是在問你怎麼了。
它甩了甩尾,在臥室門口躺了下來。
夜深人靜,臥室里燈昏暗,只聽見人低聲的抱怨:“你快點,我撐不住了!”
Advertisement
然后是男人帶著笑意的調侃:“小裴老師力不行啊,以后需要多多加強鍛煉。”
“啊——”
人的尖細細的,有些尖銳,攪了粘稠的空氣,伴隨著男人的深呼吸,又平復下去。
浴室的花灑開始工作,嘩啦啦的水聲中傳出細碎的/,的背后是漉的瓷磚,前是步步的男人。
裴冬宜這會兒心里都快哭了,哀哀地喚一聲,央求他:“不要了好不好……裴鴛鴦的債你讓它自己還去啊……”
溫見琛被這話逗樂了,大手微微向下,拍了拍的,嘖了聲,“我不讓它還,就想讓你還,再說了,哪有人還個債還半途而廢的?”
頓了頓,語氣里又帶上了一些警告的意味:“你可抱了,要是摔下去,摔到了尾椎骨要去醫院的話,丟臉的可是你自己。”
“啊啊啊——溫見琛你混蛋!嗚嗚嗚——”
“乖乖,你真是了。”
這樣的葷話也就只有這種時候能毫無心理負擔地說出口。
裴冬宜聽得渾燥熱,得腳趾頭都弱起來,一個勁催他快點。
溫見琛都被氣笑了,一口咬在上,“你可閉吧,我要真是快了,你就該哭了。”
不知道男人不能說快嗎!
裴冬宜是委委屈屈地睡著的,一覺醒來整棟別墅靜悄悄的,只有一個人在,旁邊的床鋪已經涼了,溫見琛早就出門去上班。
這樣的安靜多讓有些不習慣,下樓之后看著比平時空曠許多的客廳,愈發有種熱鬧過后的寂寥。
發了一會兒呆,也沒心去弄早餐,隨便喝了杯溫水,就開始打電話人來收拾屋子和行李。
何姐領著人來的,看他們樓上樓下地打包東西搬搬抬抬,仿佛又熱鬧了起來,裴冬宜這才覺得舒服了點。
Advertisement
“二。”何姐。
裴冬宜扭頭,笑著道:“不是在老宅,不用這麼多規矩,何姐你也是看著溫見琛長大的,像大哥大嫂那樣我秋秋或者冬宜就好,有什麼事嗎?”
何姐誒了聲,了聲冬宜,問:“花園里那兩個燈,要不要搬回去?我看漂亮的,放在這邊可惜了。”
裴冬宜問道:“搬回去有地方放嗎?”
對天街府的房子,印象還不如這棟別墅的深,還真不太清楚哪里有地方放這兩個月亮燈。
何姐解釋道:“咱們家臺很寬敞的,現在種了很多花,還封起來了房,靠邊就可以放這兩個燈,晚上肯定很好看。”
裴冬宜順著的話想象了一下,也覺得好看的,但笑著搖搖頭,“不了,這兩個留在這里吧,家里我再買兩個好了。”
這兩個燈是他們一起去逛家居市場買回來的,還搭了遮帳篷,他們經常晚上在這里坐下來,一邊喝飲料一邊閑聊,和的燈記錄了很多歡笑和私語,不想破壞掉它。
何姐沒說什麼,點頭應了,轉繼續去檢查還有沒有東西落下的。
花了一天功夫,終于將東西都搬回天街府,不搬不知道,居然比去時行李還多出好些。
裴冬宜第二天又花了整整一天,才將自己和溫見琛的帽間整理好,原本因為他們不在家而有些空的帽間,瞬間又變得滿滿當當起來。
“這下就熱鬧啦。”何姐樂滋滋地說了句,給端過來一盤切好的西瓜。
裴冬宜忍不住笑了聲,問沈笑怡最近怎麼樣,工作習不習慣,何姐說:“好著呢,我看有干勁的。”
收拾好東西,何姐就回去休國慶假期了,家里只剩裴冬宜和一貓一狗。
對于這座婚后就沒住過幾天的房子,裴冬宜心里其實是好奇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轉悠,到尋找溫見琛的痕跡。
他喜歡的咖啡,他的服,他常看的書,他的健材,忍不住去想,他從前獨居時,他的住是什麼樣的。
如今這些東西里摻雜進了的東西,比如喜歡的抱枕,喜歡的窗簾,還有裴鴛鴦的貓窩和貓爬架,從落地窗出去,眼前是璀璨的一線江景,后是溫暖的家。
跑去書房,盤坐在他的人工學椅上,給溫見琛打視頻電話,問他:“你在做什麼呀?”
“剛收完病人。”溫見琛靠在辦公室的窗邊,舉著手機,看到那邊的背景,失笑道,“去書房了?小裴老師這麼勤快,這就開始學習了?”
裴冬宜笑得靦腆,“不是啊,我來試試你的椅子舒不舒服,順便看看你有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藏在這里。”
溫見琛嗤笑,“是啊,書房有個大,我有支鋼筆的筆帽不見了,應該是黑的,上面有一顆小碎鉆,還刻有我的名字寫,你找吧,找著了給你一份大獎勵。”
裴冬宜對他的獎勵毫無興趣,但還是答應幫他找找,掛了電話后還給他點了宵夜,然后捧著手機覺得自己真是天下第一賢妻。
當然,最后筆帽沒找到,窩在書房里一邊吃零食一邊看綜藝。
第二天一早溫見琛回來,怕吵醒,特地從書房這邊的門進去。
一進去就愣了,大貓和小狗在椅子上蜷著一團,桌上還放著平板電腦和半包吃剩的香芋片。
好家伙,這是拿書房當影音室了?
裴鴛鴦這時醒了,見到他回來,剛要喵,就被他一手住臉,“噓——不許,會吵到媽媽睡覺,安靜點,乖啊。”
裴鴛鴦眨眨大眼睛,用頭頂蹭蹭他手心,不出聲了。
他躡手躡腳地穿過書房和臥室連通的過道,進臥室,一眼便看見大床上隆起的一個包。
“怎麼又把被子蓋住頭。”他嘀咕了一聲,走過去,單膝跪在床上,手將人從被子里撈出來,看見睡得紅撲撲的臉。
似乎他的作驚擾了的睡意,眼睫了兩下,眼睛睜開一條,嘟囔著問了句:“溫見琛,是你回來了嗎?”
“是我回來了。”溫見琛應道,低頭在眼睛上親了親,“快繼續睡吧。”
裴冬宜含含糊糊地嗯了聲,眼睛又閉上。
這都快上午十點了,還困這樣,有些人啊,說了晚安以后肯定還刷了好幾集電視劇。
猜你喜歡
-
連載1965 章

左先生寵妻百分百
她是能精確到0.01毫米的神槍手。本是頂級豪門的女兒,卻被綠茶婊冒名頂替身世。他本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專情總裁,卻因錯認救命恩人,與她閃婚閃離。他從冇想過,有一天,她會用冰冷的洞口指向他的心臟。“這一顆,送你去給我的孩子陪葬!”她扣下食指……
164.4萬字8 184421 -
連載2383 章

錯嫁纏婚:首富老公乖乖寵我
為了救父親與公司,她嫁給了權傾商界的首富,首富老公口嫌體正直,前面有多厭惡她,后來就有多離不開她——“老公寵我,我超甜。”“嗯......確實甜。”“老公你又失眠了?”“因為沒抱你。”“老公,有壞女人欺負我。”“帶上保鏢,打回去。”“說是你情人。”“我沒情人。”“老公,我看好國外的一座城......”“買下來,給你做生日禮物。”媒體采訪:“傅先生,你覺得你的妻子哪里好?”傅沉淵微笑,“勤快,忙著幫我花錢。”眾人腹誹:首富先生,鏡頭面前請收斂一下?
219.6萬字8 148201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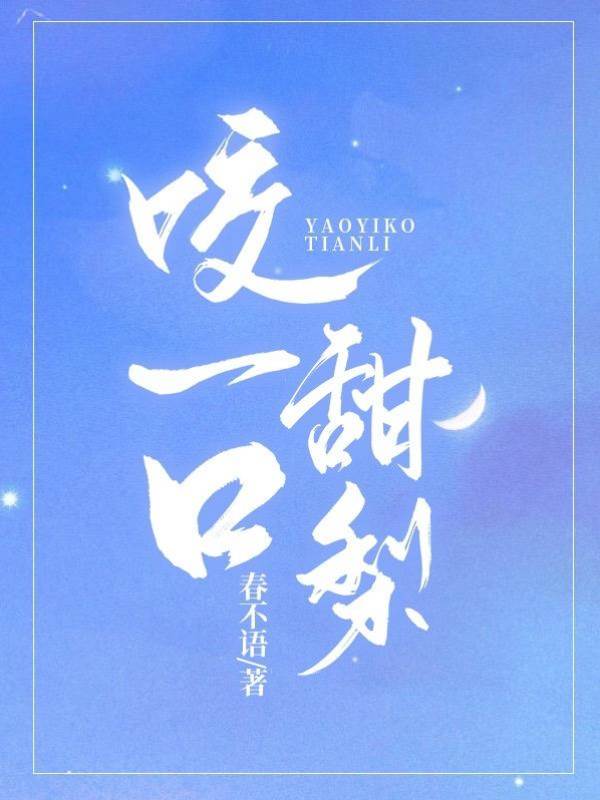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86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