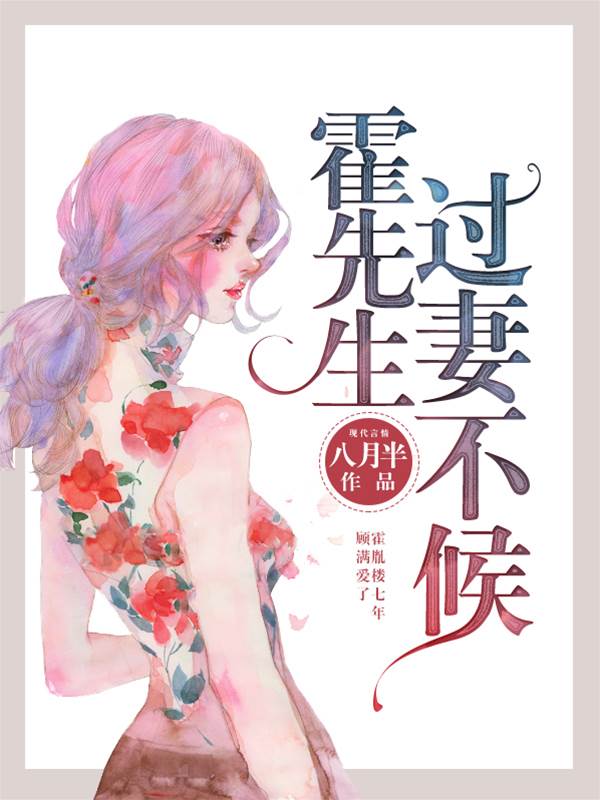《穿成年代文男主的小后媽[六零]》 第101章 第 101 章
顧淮是個理智縝的人,在這一點上,他比裴錚更像裴寂安的親兒子。
所以當他剛和家人過完十六歲生日,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出現在一個陌生的地方,邊有一個陌生男人正語氣焦急地和他說話時,顧淮冷靜下來,不聲地聽著男人說話。
“老大,算我求你了,咱們真沒必要鋌而走險犯法,有一千種方法整治許月華,你為什麼非要用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法子?”
男人長相兇狠,說話的表更是狠,提起許月華的時候恨得咬牙切齒。
許月華?顧淮對這個名字沒有毫的印象,聽到男人說犯法時他微微皺眉,淡聲說:“你先出去吧。”
顧淮唬人的表和姿態都是從老頭子那里學來的,一般人都會被他這副樣子唬住,果然,男人雖然不甘心還想再勸說,最后到底閉了,不敢再言語。
“是,老大。”兇狠男子很是恭敬地彎腰,而后退了出去。
顧淮從椅子上起,環顧四周的環境。
這是一間纖塵不染的辦公室,大理石地面鑒照可人,實木桌子上擺放著整齊的文件夾,顧淮出其中一份翻開,一目十行看完。
結尾的日期——1999年。
落地窗外高樓大廈林立,車水馬龍,遠是蜿蜒流淌的江水,這樣的繁華城市,是十幾年后的華國。
顧淮意外又不意外。
他母親陸濃曾寫過一本關于未來的話書,書中描繪的大千世界和新奇事伴隨著顧淮度過了年,在資、文化匱乏的年代里,顧淮的眼界從不曾局限在一隅之地。
“咳咳咳咳……”
顧淮克制不住地咳嗽起來,他下意識從口袋里掏出一塊手帕捂住,房間里盡是悶咳聲,咳了許久,顧淮扶住桌子坐到椅子上。
Advertisement
“這個……”顧淮手打量這雙蒼白青筋畢的手,手帕上有滲出。
緩了好一會兒,顧淮起推開辦公室的隔間,走進衛生間。
鏡子里的人面蒼白,被染紅的和著稠麗的五在蒼白面的映襯下,像一把鋒利的尖刀,直直刺人的眼睛。
是他也不是他。
鏡子里這張臉和顧淮長得一模一樣,卻比他本人很多,像是十幾年后完全長開了的他,西裝革履,氣質郁森然,可惜看上去命不久矣。
難道十幾年后的他是這個鬼樣子?
顧淮又抑制不住地咳嗽起來。
這時,辦公室里的電話響起來,顧淮捂著回到辦公室接起電話。
“顧淮,是我。”電話里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
“大哥?”顧淮對裴錚的聲音很悉,即便是隔著電話線,他也能立馬分辨出大哥的聲音。
電話里好一陣沉默,顧淮以為裴錚那邊斷線了,又了一聲,“大哥?”
“顧淮,你又在耍什麼詭計?”
這句質問的話令顧淮也沉默了,他反應過來,十幾年后他和大哥的關系很可能不再像從前那樣親無間了。
顧淮很想知道這十幾年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卻沒辦法問出口。
“你找我什麼事?”顧淮一陣悶咳后,盡量讓自己的語氣聽上去冷淡。
電話那頭的裴錚顯然對這個態度的顧淮更悉,“過兩天是陸阿姨的忌日,你進不去墓地,在門口等著,我帶你進去。”
“你說什麼!?誰的忌日?”顧淮豁然起,口悶疼不已,發出一連串的咳嗽。
“顧淮!”裴錚皺眉,以為顧淮仍舊賊心不死,想把陸濃單獨遷墳出來,警告道,“這件事已經爭了多年了,我最后一次告訴你,遷墳你就別想了,當初老頭子親自吩咐的與你媽合葬,那里是國家公墓,連我都沒有權利把你媽遷出來。你別忘了,我自己親媽還在外頭。”
Advertisement
裴錚旁觀了一輩子也沒懂老頭子的想法,說他在乎陸濃,陸濃活著的那幾年,老頭子幾乎不著家,回了家也是在書房里睡,他甚至沒有見過兩人同房過。
說他不在乎陸濃,陸濃死后,老頭子守了一輩子,沒和誰再結過婚,他親媽等了老頭子一輩子,老頭子連看一眼都不屑。
臨死時,唯一的要求就是將自己與陸濃合葬,死都不要分開,活著的時候卻如同陌路。
裴錚不懂,他也沒法和顧淮解釋,實際上他倒是理解顧淮,畢竟顧淮的父母生前是恩的,陸濃郁郁寡歡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顧叔叔亡。
電話這頭,顧淮從裴錚的幾句話里分析出他媽和養父都去世了,兩人合葬在一起,而“他”一直想把親媽單獨遷出來。
一陣巨大的失落和恐慌緒襲來,比看到十幾年后的自己咳時更令他害怕。
他沒有母親了。
這十幾年里到底發生了什麼?父母早逝、和兄弟反目仇……
顧淮很快問道:“吳姥姥和小夏呢?們去不去?”
“誰?吳姥姥小夏是誰?”裴錚瞇了瞇眼,顧淮今天實在不對勁。
“……沒什麼。”顧淮輕呼一口氣,意識到事并沒有他想的那麼簡單。
裴錚不認識吳姥姥和小夏,他的語氣不像是撒謊,什麼況下裴錚會不認識兩個朝夕相幾十年的人?
失憶或者吳姥姥和小夏兩個人本不存在。
常識告訴顧淮是頭一種,可是直覺卻告訴顧淮是后一種。
平行世界嗎?媽媽曾經給他講過的平行世界的故事。
他到了一個不屬于他的世界。
為了印證自己的猜想,顧淮穿上大外套,起向外走。
剛出辦公室,一個穿搭得的人攔住顧淮的去路,“老板,接下來的行程是去醫院復查,您現在要去嗎?我現在就安排司機。”
Advertisement
顧淮眉眼一:“不必了,先送我回家。”
人聽后連忙去打電話給司機,顧淮朝大樓外走去,一路上遇到的人都會停下來問候顧淮。
走到大廈門口,一輛黑的轎車停在門口,車上的司機走下來,替顧淮打開后車門。
車上,顧淮狀似和司機閑聊,實則打聽自己目前的境況。
司機心里也在犯嘀咕,他老板平時不會多說一句廢話,說一不二的,什麼時候喜歡聽一個司機講話了?
打死他也猜不出老板換人了,于是司機只好乖乖任由老板套話,他倒想說幾句好聽的假話糊弄老板,但一及到老板若觀火的眼神,司機一個哆嗦就把實話說了。
顧淮從司機這里套了很多,包括他考上了世界頂尖大學,創辦了自己的公司,父母早亡,沒有任何家人朋友,沒有吳姥姥和小夏,和裴錚是不死不休的死對頭,對裴家的事諱莫如深,沒人知道他曾經是裴家的養子……
知道這些就已經足夠了,顧淮輕咳著說,“不用回家了,送我去我母親所在的墓地吧。”
沒有家人的房子只不過是一住所而已。
“哎,好的。”司機從后視鏡里小心翼翼看了顧淮一眼,心想原來是老夫人的忌日快到了,怪不得老板奇怪。
到了墓地,顧淮被站崗的保安攔下,那人顯然是認識顧淮的,一見到顧淮當著他的面給裴錚打電話。
保安將電話遞給顧淮,顧淮接過來,電話那頭傳來裴錚惱怒的聲音,“顧淮,你聽不懂人話嗎?我說過兩天,意思是兩天以后,你現在就去是什麼意思?要我現在就去陪你嗎?”
顧淮長這麼大第一次聽到大哥朝他發火,蠻新奇的,他也很想見見平行時空的大哥,于是說:“好啊,你來吧。”
Advertisement
那頭的裴錚噎住,好半晌才開口說,“你等著。”
換做平常任何時候,裴錚定然是不會搭理顧淮的小把戲的,他在部隊里一堆事,沒功夫理會顧淮的挑釁,可再過兩天是陸濃的忌日,陸濃再怎麼說也是裴錚的繼母。
顧淮是陸濃的親生兒子,一個兒子想早一點看母親,無可厚非。
大概過了一個小時,裴錚來了。
他從車上下來,上穿著迷彩常服,手里拿著一束花,氣勢不比這個歲數的裴寂安差到哪里去。
可顧淮關注的不是這些。
大哥老了。
這是顧淮最直觀的,他的大哥向來臭屁,是個意氣風發的青年人,可如今大哥的頭發上有了白,臉上有了皺紋,比顧淮印象里的大哥老了將近二十歲。
顧淮張了張,到底沒有把那聲大哥出來。
“走吧。”裴錚惜字如金,只給了顧淮一個眼風,從保安手里接過名冊簽過名后帶著顧淮進墓地。
顧淮沉默跟上他。
兩人七拐八拐走到一墓前,裴錚蹲下用手了墓碑,將花束放在上面。
顧淮看著墓碑上的照片不已,跪了下去。
裴錚很能看到失態的顧淮,這人智多近妖,分分鐘令人恨得牙,而他仍是一副優雅從容的面孔,想起舊怨,裴錚忍不住刺了顧淮一句。
“這回倒是老實。”
顧淮沒有反刺回來,裴錚自己倒覺得了點什麼似的。
見顧淮一個勁兒盯著墓碑上的照片發愣,裴錚不知為何有些可憐他,外人看來年有為,三十幾歲就富可敵國的顧淮,和自己爭了一輩子、斗了一輩子的顧淮,最初的愿也只不是想將他的母親遷墳出來和親生父親合葬而已。
也許是今天的顧淮太過不一樣,上了咄咄人的氣勢,也許是電話里那兩句久違了二十多年的大哥,裴錚難得想說說心里話。
舊人故去,到頭來裴錚發現自己藏在心里的這些話,竟不知道朝誰訴說,大概也只剩下顧淮一個人了。
“你是不是很難理解老頭子的做法?”裴錚輕聲說,“我也不理解,人都說生當同寢,死亦同,但他們從不曾相過,我怎麼想也想不明白老頭子為什麼非要和你母親合葬。”
“我明白。”
顧淮看著照片里笑得毫無霧霾的陸濃會心一笑,這張照片他知道,父親藏了半輩子的照片,時他帶著小夏玩捉迷藏,無意中破解了書房里的保險柜,從中翻出了母親的這張照片。
那天父親先于母親回家,因為這張照片,他和小夏一整個夏天有吃不完的零食。
長大后顧淮才懂這張照片藏著什麼樣的心思。
想不到到了平行時空,還是能見到它。
不難猜,這個平行時空的裴寂安同樣也深著陸濃。
生當共寢,死當同,真好,不管在哪個時空,他們始終都在一起。
“你明白?”裴錚意外看向顧淮,顧淮的表告訴他他真的知道一些自己不知道的事。
“是誰說的他們不曾相過?”顧淮用袖子替父母拭照片。
裴錚默然又驚悚,這是他第一次見到顧淮對老頭子態度尊敬,竟然和對待他母親的態度差不多。
而顧淮的話又是什麼意思?他父親和顧淮的母親何時相過?
可若是不相,又怎麼解釋老頭子要求合葬的行為?
“他們有沒有相,你我不是最清楚嗎?你恨我恨裴家,歸到底,皆是因為他們不負責任的結合。”
年時的裴錚不了冷冰冰的家,一走了之,離家多年在外打拼,而小的顧淮只能留在那個家里,過著和他小時候一樣的生活。
甚至比他更不如,裴錚到底是裴家脈,旁人看碟下菜也不會欺負他,顧淮不一樣,沒了母親,老頭子又向來信奉有本事就還回去那套,可想而知顧淮的年會有多慘。
這也是多年來裴錚容忍顧淮的原因,他心里對顧淮總是愧疚的。
顧淮想要說話,口的悶疼阻止了他,一陣咳嗽過后,手心沁出一抹刺眼的紅。
“你……咳了?”裴錚知道顧淮不好,但沒想到竟然這麼糟,壯年咳。
猜你喜歡
-
完結171 章

拒嫁豪門,少奶奶又逃了
參加男朋友家族聚會,不過他哥哥好像…… 蘇小小獨自穿過走廊拐角的時候,突然被男人拉進漆黑的房間里強吻了。 男主:「這就是你說的重逢?」 女主:「別在他面前求你了」
49.2萬字8.33 18026 -
完結1020 章

我閃婚了個億萬富翁
被催婚催到連家都不敢回的慕晴,為了能過上清靜的日子,租了大哥的同學夜君博假扮自己的丈夫,滿以為對方是個普通一族,誰知道人家是第一豪門的當家人。……慕晴協議作廢夜君博老婆,別鬧,乖,跟老公回家。
176.1萬字8.18 310249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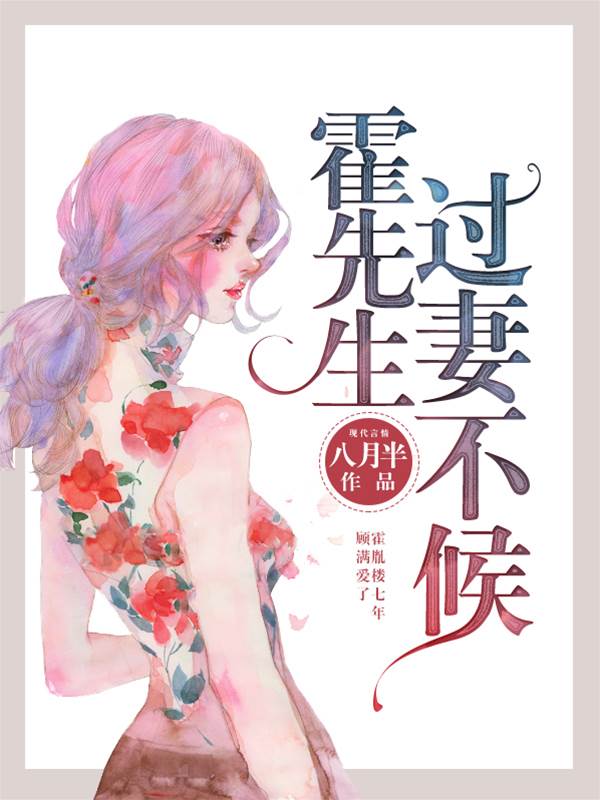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3350 -
完結228 章

月光轟鳴
久別重逢,陸敏跟杭敬承閃了婚。 介紹人聽說兩人中學時期是同學,陸敏還有段給杭敬承寫情書的往事,直言這叫有情人終成眷屬。 實際上,兩人婚後一分居就是數月。 再見面後杭敬承提出第二天送陸敏去上班。 她知道這行為出于禮貌,答應了。 半晌,床墊微響。 “你在……”低沉含糊的聲音在身後響起,她以為他還有什麽重要的事沒說,稍稍回頭。 杭敬承:“你在哪個學校?” 陸敏:...... 杭敬承出身高知家庭,卻一身反骨,做起電影,一路做到總制片位置,事業風生水起。 身邊人都知道他英年閃婚,是因為杭家給的不可抗拒的壓力。 見陸敏又是個不讨喜的主兒,既沒良好出身,也沒解語花的脾性,紛紛斷言這場婚姻不可能維持多久。 陸敏自己也擔心這場婚姻維持不下去,跟杭敬承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他靠在床頭,懶洋洋睇着她,修長手指卷起她耳邊的頭發絲纏繞幾圈,“怎麽着,說我為什麽要跟你離?” “說我,總板着臉。” “哦。那你多笑笑。” “......” “笑一個呗,笑一個給你咬。” 陸敏笑是沒笑出來,耳根子噌地紅了。 這夜夜深人靜,陸敏被身邊人攬在懷裏,睡意朦胧間聽見散漫呓語: “離什麽,不離......” “十七歲的杭敬承告訴我。” “摘到手的月光無可歸還。”
38.3萬字8.18 361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