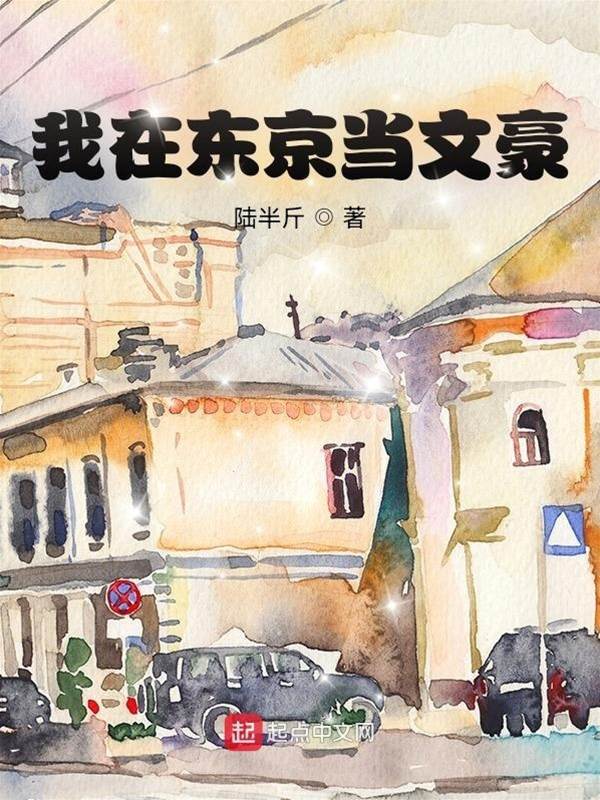《穿成亡國太子妃》 第127章 亡國第一百二十七天(捉蟲)
雨夜的空氣總是得厲害, 這意在室則變得有些黏糊。
秦箏看到楚承稷拿出了兩支嶄新的紅燭在燭臺上點著,室變得更亮了些,愈顯紗窗外雨夜黑沉。
他清俊的臉龐被燭火鍍上一層, 抬起頭時, 眼底映著燭和:“聽說房花燭夜的燭, 得燃一夜才吉利。”
窗外的雨聲噼里啪啦,似鼓點落在人心上。
秦箏原本不在意這些,看他鄭重其事的樣子,覺得好笑之余,心口還有些自己也說不清的別樣緒,開玩笑一般問:“那是不是還得喝合巹酒?”
楚承稷著淺淺牽角, 和他平日里溫和卻讓人覺著有距離的的笑不一樣,這笑似從心底著愉悅。
“合巹酒, 紅手,執子與共誓言久。合巹酒自是不了的。”
音清淺又溫雅, 倒是比合巹酒更醉人些。
杯子是怎麼滾落到床角的秦箏記不太清了, 從前也安過跟前這人, 知道他披著層溫雅和氣的皮囊,在那方面卻有些蠻橫,但不至于不能招架。
等嗚咽得嗓子都啞了,才知道他從前真是隔靴搔憐惜著的。
最后一次被楚承稷從凈房的溫泉里抱出來時,秦箏兩得幾乎站不住。
床上的褥子已經不能看了, 楚承稷盡數扯了下去,扔進臟簍子里, 鋪上新的, 才把抱了回去。
秦箏疲力盡窩在他懷里, 纖長的眼睫被淚水沾后黏在一起, 臉上的坨紅還未散去,像是被人欺負了的小。
楚承稷憐在眼皮上吻了吻,終于良心發現說了句:“睡吧。”
燭臺上的兩支紅燭燃得只剩一小截,底下堆著斑駁的燭淚,院子里都能聽見早起的下人走的輕微聲響了。
Advertisement
秦箏迷迷糊糊看了他一眼,又惱又恨地在他肩膀上用力咬了一口。
楚承稷極致忍地悶哼了一聲,察覺到他的變化,秦箏嚇得瞬間了個鵪鶉,閉上眼一不,就差把“我睡著了”幾個字寫在腦門上。
一只大手輕輕了鬢發,含著笑意的低醇嗓音響起:“不鬧你了,快睡。”
秦箏安心了,側過想把腦袋埋枕頭里,猛然想起他之前把這個枕頭墊到腰后,那顆困得不行的腦袋還是瞬間抬了起來,控訴一般地道:“我不睡這個枕頭。”
秦箏聽見幾聲悶笑,窸窸窣窣一陣響,楚承稷把他的枕頭換了過來,那只鐵鉗一樣攬在腰間的手卻沒松過。
在這類小事上,他對似乎越來越霸道。
……
秦箏醒來時屋外依然下著雨,天有些暗沉,一時間分不清這是清晨還是暮時。
側的被褥是冷的,楚承稷顯然早就起了。
秦箏撐著床榻神微妙地爬起來,只覺自己渾的骨頭都似被人拆了重組過一般。
趿著鞋下床,一雙得跟面條似的,若不住及時扶住了床柱子,可能真站不住。
回想起昨夜的種種,惱怒直接蓋過了所有怯。
還三天?他睡書房去吧三天!
秦箏坐到桌前給自己倒了杯冷茶咕嚕嚕喝下解了,梳妝時見自己頸上沒有半點印記,不會幾天見不得人心底的火氣才消了一點。
更時看到頸下印花一樣的青紫時,臉瞬間又綠了。
敢他這不是學會了收斂,而是專門挑了地方!
秦箏咬著牙,巍巍更完,才推開門讓人送吃食過來。
坐到書案前本想辦公務,但再次提筆于這地方寫東西,心底總有點別扭,正打算搬個團去矮幾上辦公,抬眼就瞧見了書案角落放著的一摞文本,卷首用遒勁方正的字跡寫了“軍規”二字。
Advertisement
秦箏翻開一瞧,發現正是楚承稷按照現有的軍規法令,結合娘子軍的特改良后的軍規。
自己翻閱典籍整理數日也不一定能融會貫通的東西,他不到半日就幫理好了,秦箏不合時宜地想到了“才易”幾個字,整個人都愣了愣。
細致看了一遍,見里面連練兵的規劃都做出來了,角還是往上翹了翹。
白鷺和樓燕送飯過來時,秦箏不意外地得知楚承稷下午就又去和臣子們議事了。
秦箏瞥了一眼一旁的軍規提案,心中腹誹,那人跟一樣天快亮了才睡的,何時起來擬的提案?
秦箏問:“淮王那邊可有什麼作?”
嗓音一反常態地有些嘶啞。
白鷺和樓燕都是娘子軍的人,同府上的普通下人不一樣,對軍知曉得自然也多些。
白鷺回話道:“淮王那邊暫時倒是沒什麼靜,從徐州以東的各大城池,都封鎖了要道,淮王軍中瘟疫肆,不將士都染惡疾,軍心渙散,目前是無力攻城的。”
秦箏點頭表示知曉,又問:“青州和塢城呢?”
白鷺呈上一封信:“這是宋大人寄來的。”
秦箏已經吃得差不多了,用巾帕了角,拆開信封后,里邊是宋鶴卿的折子。
先前秦箏要親自前去鎮清溪縣的暴.,宋鶴卿就極力反對,后來得知淮王軍隊同清溪縣的流民了手,更是擔憂得不得了,猜到若撤軍,肯定撤往閔州,當即把信件往閔州寄了過來。
秦箏一目三行看完,青州災棚和塢城的瘟疫目前是控制住了的,從各地前來的郎中們,雖還沒找到救治疫癥患者的法子,但配出的湯藥,已能阻止患者從紅疹惡化到惡瘡。
Advertisement
哪怕還不能治,能找到暫時抑制病癥惡化的法子也是好的。
青州和塢城無恙,秦箏便寬了心,對二人道:“兩日后你們隨我去郡百姓暫居征兵,閔州多布莊,你們去問問價錢,訂做一批娘子軍的軍服。”
白鷺和樓燕聞言,神都有些激:“婢子遵命。”
秦箏微微頷首:“退下吧。”
樓燕是個耿直的,聽秦箏嗓音有些啞,想到這連日的秋雨,以為著了涼,關心道:“深秋寒涼,太子妃娘娘當珍重貴才是,奴婢聽娘娘音嘶啞,要不要請個大夫看看?”
方才的飯菜油葷有些重,秦箏正喝著茶解膩,猝不及防聽到這麼一句,險些嗆到,勉強維持著臉上的淡然道:“無礙。”
樓燕還想說什麼,白鷺不聲踩了一腳。
樓燕茫然看了看白鷺,白鷺拉著沖秦箏行禮:“娘娘好生休養,奴婢二人這就退下了。”
等白鷺和樓燕退出房門,秦箏看著桌角那摞軍規提案,才又緩緩磨了磨牙。
當晚楚承稷披星戴月回來,推門時就發現房門被人從里邊閂上了。
自己昨晚做了些什麼,他還是有自知之明的。
倒也不是不想憐惜,只是在那種時候哭,反讓他腦子里最后一理智的弦都崩斷了。
不怪會有這麼大氣。
楚承稷抬手輕輕扣了扣門,嗓音平靜又溫和:“阿箏?”
里邊黑漆漆的,沒人應聲。
他又扣了扣,好脾氣地繼續喚:“睡下了?”
白鷺和樓燕在耳房聽見聲響,著頭皮出來回話:“稟殿下,太子妃娘娘說昨夜秋雨寒涼,染了風寒,已經喝藥睡下了。娘娘說為免把病氣過給了殿下,殿下這幾日都去書房歇吧。”
Advertisement
說完空氣里就陷了一陣詭異的沉默。
白鷺和樓燕低頭看著自己腳尖兒,大氣不敢一聲。
屋檐下的燈籠在地面拉出一道斜長的影,許久,白鷺和樓燕才聽見極淺的一聲:“退下吧。”
再無平日里的溫和。
白鷺和樓燕如芒在背,卻也只能行禮后退下。
二人回到耳房后沒敢直接躺下,外邊靜了良久,才響起轉步離開的腳步聲。
白鷺微不可見地松了一口氣,卻又有些擔憂,太子妃娘娘和殿下鬧了脾氣,轉頭真把太子殿下給氣走了可如何是好。
*
房間里,秦箏躺在床上,也是豎著耳朵在聽外邊的靜。
睡了整整一個白日,這會兒沒什麼睡意,楚承稷第一次敲門的時候,就是醒著的。
聽見楚承稷在外邊站了一會兒,腳步聲果然遠了,心中頗有點小解氣。
躺了一會兒,實在是睡不著,爬起來點了室的燈,打算找本書看。
室的燭火剛亮起來,窗欞那邊就似被夜風吹,發出了一聲輕響。
秦箏瞬間繃了神經,拿起燭臺去窗欞看,卻什麼也沒有。
還不死心地推開窗欞往外瞅了瞅,除了花圃里黑漆漆的樹影,什麼都瞧不見。
夜風灌進屋里有些涼,秦箏顧不上攏襟,用手擋住了燭火才避免被風吹熄。
可當空出手去關窗葉時,蠟燭還是被一陣冷風給吹滅了。
四周陡然陷黑暗,秦箏總覺得有雙眼睛似在暗看著自己,渾的皮疙瘩都快起來了。
“咔噠”一聲,強自鎮定關好窗戶,轉看向屋時,壯著膽子道:“楚承稷,我知道是你。”
沒人應。
秦箏在原地僵立了一會兒,豎著耳朵沒聽見屋有什麼聲響,視線也重新適應了黑暗能辨出屋的一個廓,才輕輕呼出一口氣。
猜錯了?
剛邁出一步,一只冰冷的大手就從后攬住了的腰,下輕擱在肩窩,不發一言。
秦箏被他嚇了一跳,低了嗓音咬牙切齒開口:“楚承稷!”
“不是睡了?”
他應,嗓音清淺平靜,似乎又抑著什麼。
秦箏汗直豎,一把揮開他退出幾步遠:“你想都不要想,三天不可能的!”
“回來給你上藥的。”他把人撈起,同樣是手不見五指的黑,他抱著個人都還走得四平八穩,把秦箏放回床榻上了,才轉點了燈。
秦箏坐在床尾,雖然努力維持著一臉淡然,不過那戒備的眼神,怎麼看都像是一只被擼到炸的貓。
楚承稷從懷里取出一個刻著花紋又上了彩釉的橢圓形盒子。
秦箏有種不好的預,警惕道:“上……上什麼藥?”
“不是腫了?”
“……”
“上藥了好得快些。”
“……”
秦箏不愿在他跟前示弱,繃著臉努力維持著一臉淡然道:“我自己來。”
楚承稷原本是想幫忙的,但真幫忙了,會不會變幫倒忙還不好說,便由著自己去凈房了。
等秦箏從凈房回來,見他拿著傍晚看的游記在看,不由道:“你還不走?”
楚承稷看了一會兒,放下書,把炸的貓咪重新抱回懷里,下抵在發頂,緩聲道:“昨晚是我過分了。”
秦箏的怒焰降了一降。
他在鬢角親了親,聲音里著疲憊:“今晨只合眼了半個時辰,阿箏陪我躺會兒。”
秦箏想到他已經理完的娘子軍軍規提案,怒焰又降了降。
這人忙起來,好幾宿不睡都是常有的事,惱歸惱,看他下上冒出來的淡青胡茬兒,秦箏也是真心疼。
在青州時只忙政務都時常腳不沾地,他得理各大州府的軍務和政務,每日要看的折子都比多了一倍,肩上擔子有多重可想而知。
沒應聲,卻窩在他懷里沒再彈,還手環住了他的腰。
楚承稷抱著躺了一會兒,卻又問:“真有那麼難?昨晚你一直哭。”
秦箏:“……”
楚承稷垂下眼,語氣認真:“若真難,往后還是像從前那般好了。”
真到了那一步,他不太能控制得住自己。
從前也那般哭過,昨夜他才沒分清哭究竟是疼還是因為其他的。
不過都腫了,今日又這般生氣,想來是疼的。
思及此,楚承稷眼底有了幾分自厭的緒。
.果然是令人生厭的。
猜你喜歡
-
完結384 章

曹操之女
穿越長到三歲之前,盼盼一直以為自己是沒爹的孩子。 當有一天,一個自稱她爹的男人出現,盼盼下巴都要掉了,鼎鼎大名的奸雄曹操是她爹?!!! 她娘是下堂妻!!!她,她是婚生子呢?還是婚外子?
142.9萬字7.67 25077 -
完結556 章

全家去逃荒,她從懷裏掏出一口泉
特種兵兵王孟青羅解救人質時被壞人一枚炸彈給炸飛上了天。 一睜眼發現自己穿在古代農女孟青蘿身上,還是拖家帶口的逃荒路上。 天道巴巴是想坑死她嗎? 不慌,不慌,空間在身,銀針在手。 養兩個包子,還在話下? 傳說中“短命鬼”燕王世子快馬加鞭追出京城,攔在孟青羅馬車麵前耍賴:阿蘿,要走也要帶上我。 滾! 我會給阿蘿端茶捏背洗腳暖床…… 馬車廂內齊刷刷的伸出兩個小腦袋:幼稚! 以為耍賴他們
102.1萬字8.18 107572 -
連載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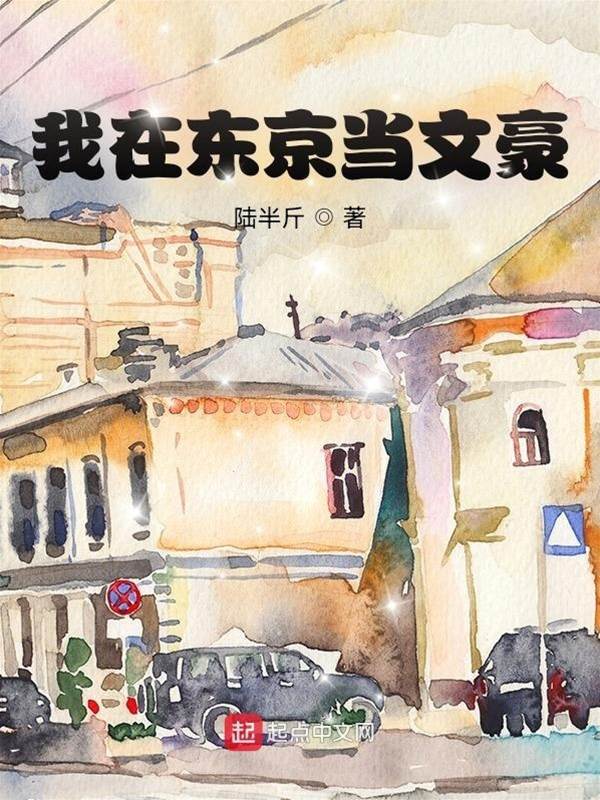
我在東京當文豪
這個霓虹似乎不太一樣,泡沫被戳破之後,一切都呈現出下劃線。 原本那些本該出現的作家沒有出現,反而是一些筆者在無力的批判這個世界…… 這個霓虹需要一個文豪,一個思想標桿…… 穿越到這個世界的陳初成爲了一位居酒屋內的夥計北島駒,看著孑然一身的自己,以及對未來的迷茫;北島駒決定用他所具有的優勢去賺錢,於是一本叫做暮景的鏡小說撬開了新潮的大門,而後這本書被賦予了一個唯美的名字:雪國。 之後,北島駒這個名字成爲了各類文學刊物上的常客。 所有的人都會說:看吧,這個時候,我們有了我們精神的歸屬……
41.5萬字8.18 141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