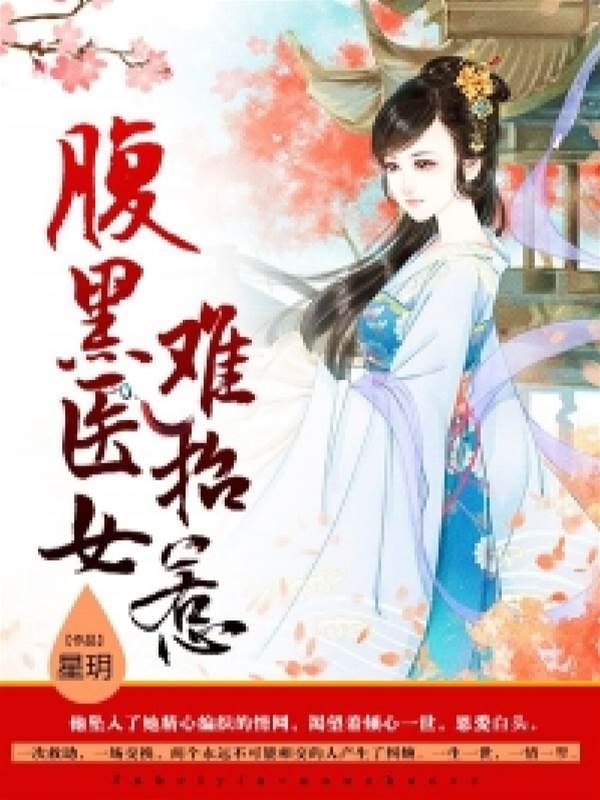《穿成亡國太子妃》 第133章 亡國第一百三十三天
楚承稷出了營帳, 天還沒大亮,巡邏的將士路上見他,都停下一聲:“殿下。”
楚承稷微微點頭致意后, 將士們才繼續巡營。
不遠就是岑道溪的營帳, 他似乎也早就起了,著一廣袖儒袍,端正又風雅, 負手在帳外看著灰蒙蒙的天際出神。
楚承稷路過時道了聲:“先生今日起得頗早。”
岑道溪回過頭,見來者是楚承稷,道:“殿下起得也早。”
同樣是謀士,比起陸則, 他在楚承稷跟前, 了一份拘謹, 多了幾分隨和。
淡薄的天落到二人上,一旁三腳架火盆里的篝火還燃燒著, 明滅的影讓他們影都不甚清晰。
楚承稷問:“同淮王的這場困之斗, 先生以為如何?”
岑道溪語氣清又狂妄:“淮王已不足為懼,余下的勢力很快就能清繳干凈,稍加休養生息,殿下便可揮師北上了。臣所憂的,也是株洲以北、涼州以南的地界,該如何盡收囊中。”
連欽侯要面對北戎外敵,糧草得靠中原腹地補給, 先前連欽侯援助了他們藥材, 楚承稷轉頭也贈了糧草回去, 他們這兩方勢力, 如今可以說是在一條船上。
只是橫在這中間的陳國, 從一開始的李信掌權,變了現在沈彥之和李忠分庭抗禮。
他們若單個擊破,恐怕沈彥之會和李忠聯手一致對外;若拉攏其中一方,幫著蠶食另一方,以沈彥之和楚太子的那些過節,同汴京這邊結盟絕無可能。
李忠那等小人又絕無信義可言,只怕前腳同他們結盟,后腳就能把他們給賣了。
而且他先前被李信授意,已經和北戎人接洽過,一旦到了絕境,再和北戎人穿一條子也是他能做出來的事。
Advertisement
要拿下原本屬于李信的這兩勢力,不太容易。
楚承稷面上卻并無憂,開口時嗓音平靜又斂:“的確還有這最后這兩場仗要打。”
天大綻,火盆里的火也暗淡了下去。
岑道溪偏過頭看這位用了不到一年時間就收復大半失地的儲君,他面容實在是顯得年輕了些,但他事的那份穩重和用兵的老,讓岑道溪都暗自吃驚了好幾次。
這樣的魄力和能力,無怪乎能一眾能臣虎將都信服于他。
將士們都已晨起,軍營里的聲音漸漸多了起來。
楚承稷的親衛去陸則營中尋人不見,一路找過來,“殿下,太子妃娘娘來信了!”
楚承稷斂的眸中這才多了幾分波瀾。
那封信,正是數日前,秦箏寫給楚承稷讓從閔州買一披寒回去的信,除此之外,還提及了株洲那名能治瘟疫的大夫被沈彥之抓走一事。
岑道溪見楚承稷面不愉,問:“莫非是江淮出了什麼變故?”
楚承稷將信遞了過去。
岑道溪看完,神也變得凝重起來,他思忖片刻后道:“殿下,吳郡等地有我和安將軍在此清繳淮王殘余勢力,殿下可回江淮主持大局。”
沈彥之此舉,十有八九又是旨在太子妃,太子妃所有疫癥百姓的命著,可謂進退兩難。
*
陸則昨天夜里沒睡好,等他一個回籠覺睡醒,就得知大清早說自己要去巡視河谷的楚承稷,要押送布匹回江淮了。
他嘖了兩聲,愈發慨,還好家中老爺子當初沒有腦袋發昏,死活要把陸錦欣塞去楚承稷邊,否則他們郢州陸家的好日子真就到頭了。
***
青州。
秦箏未等到沈彥之的那三日之約,就先被從北庭傳回來的一則噩耗驚得慌了神。
Advertisement
北戎人發起了冬后最猛烈的一場進攻,涼州府和羌柳關同時被咬住,連欽侯父子各守一。
但北戎此番領兵的乃北戎大王子,號稱北戎第一勇士,連欽侯同他手時,都險些他斬于馬下。
關鍵時刻,一名小個子將領沖殺出來,替連欽侯接了那一刀,只是仍不敵北戎大王子,被一刀橫劈下馬時,頭盔也跟著掉落,一頭長發和噴灑出的霧齊齊揚在了朔風里,滿是鮮的一張臉,眼神卻兇悍如虎豹。
見同自己手的是名將,北戎大王子足足愣了好幾息,這才讓一名虎背熊腰的護軍趁機將那名將給搶了回去,北戎大王子回過神來繼續追殺那名將,那名護軍替將擋了好幾刀。
沒過多久,就有一支娘子軍扶靈回青州,只是正值沈彥之和李忠斗法,株洲以北的城池全都閉,那支扶靈而歸的娘子軍被困在了回鄉路上,托了不難民和商賈,幾經周折才把消息送到了青州。
秦箏初聞噩耗,整個人都眩暈了一下,勉強維持著鎮定命人去傳宋鶴卿等人前來議事,又鋪紙筆想寫信告知楚承稷北庭遭難,手卻抖得幾乎握不住筆,眼淚大顆大顆往下砸,將書案上的信紙沾了大片。
另一只手捂著,哭得無聲而抑。
是聽旁人描述,秦箏就能猜到那殺出去救連欽侯的將,十有八九是林昭。
那麼被一抬棺木送回青州的又是誰?
秦箏不敢想,也不愿去想。
當初他們被李信和淮王兩面夾擊,連欽侯也被北戎和李信掣肘,楚承稷不得已派出娘子軍去北庭援助連欽侯,謊稱是他們這邊的正規軍,讓李信駐守在北庭的兵馬不敢輕舉妄。
Advertisement
那時楚承稷就明確和連欽侯那邊說過,他們這邊的娘子軍,只是唬住當時李忠的人馬,不到萬不得已不會上戰場。
北庭此番險些守不住,林昭才帶著娘子軍上了戰場的嗎?
秦箏越想,心中越是悲慟。
等宋鶴卿一干臣子匆匆趕來時,哭過一場后已勉強制住了緒,紅著眼眶道:“本宮打算向陳營借道,派人前去迎扶靈而歸的娘子軍,諸位有何疑議?”
株洲以北各城池都封鎖要道,娘子軍要想從北庭回青州,必須得向陳營借道。
當初是和林昭一手創起的娘子軍,不管扶靈歸來的是誰,都要接那些姑娘回家。
宋鶴卿等一干臣子并無異議,齊齊躬對秦箏道:“臣等皆認同娘娘所言。”
秦箏被淚水浸過的一雙眸子不人覺著脆弱,反而堅定又銳利:“勞宋大人擬文書,速速遞往陳營。董將軍留守青州,林將軍和楊將軍點兵兩萬,隨本宮去接娘子軍。”
被點到的臣子們紛紛應是。
***
汴京。
接連下了多日的大雪總算是停了,太甚至還了個臉,不過只是個掛在天上的沒什麼溫度的白影。
地上的積雪人清掃干凈了,墻頭樹梢上,仍是壘著厚厚一層。
沈嬋被婢子扶著下馬車時,正好瞧見沈彥之披著銀鼠皮披風站在路邊,陳欽附耳同他說了些什麼,他臉瞬間變得嚴峻起來。
沈嬋披著斗篷在原地等了一會兒,并未做聲,手卻無意識揪了襟,生怕是自己送走游醫的計劃沈彥之知曉了。
游醫跟在沈嬋后,神也有了些拘謹。
沈彥之往們這邊看了一眼,又同陳欽說了些什麼,陳欽很快抱拳退下。
Advertisement
沈彥之這才往沈嬋這邊走來:“外邊風大,怎不先進府去?”
“我不冷。”沈嬋小心打量著沈彥之的神,見兄長待自己一如往常親近,試探著問了句:“可是朝堂上有事需要阿兄回去理?”
沈彥之搖了搖頭,說:“北庭的戰事,離汴京遠著。”
沈嬋卻是吃了一驚:“北庭打仗了?那我們要出兵幫忙嗎?”
在印象里,從前北庭傳來戰事,榮王得早出晚歸好些天,據說是在金鑾殿上一起商議敵之策。
沈彥之腳步微頓,說了句“不必”,便邁了沈府大門。
沈嬋愣在原地,落后了他好幾步才由婢子攙著自己的胳膊步上了臺階。
這是沈嬋回京后第一次歸家,看到空的庭院,又錯愣了幾許。
自從道跑出京后,李信翻舊賬逮了榮王一項錯,拿了榮王獄,府上值錢的件,也奉命“搜查”的軍收刮走了大半。
除了幾個忠心的老仆還留在府上,其余下人也早被遣散了。
沈嬋一直在宮中,還不知昔日恢弘的沈府已破落了這般,看著沈彥之清瘦單薄的背影,莫名鼻頭一酸。
滿朝文武都說攝政王只手遮天,如今在汴京城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誰又知曉,他日日居住的府宅,破敗了了這般模樣,他都沒修葺過。
沈彥之走在前面,見沈嬋遲遲沒跟上來,一回頭,瞧見紅著眼看著自己,他目在蕭條破敗的庭院里慢慢掃過,帶著一種他自己都說不清的麻木和鈍痛在里邊:“家里變了樣不高興?等年后阿兄讓人照著原來的樣子重修一遍。”
沈嬋搖了搖頭,努力退眼眶的淚意,問:“他呢?”
兄妹二人都不愿稱呼榮王為父親,這麼一問,沈彥之就知道問的是誰,那直的背脊微僵了一瞬,才說:“在牢里。”
李信對付沈家的時候,讓榮王了獄,沈彥之殺回汴京,用慢毒將李信困死在榻上獨攬大權后,仍沒將榮王放出來。
滿朝文武背地里都管他瘋狗,個個懼他如鬼剎。
畢竟都能任其生父在牢里過生不如死的日子,他對旁人狠起來,手段可想而知。
酸意在沈嬋鼻尖聚得越來越重,哽咽道:“阿兄,我不恨他了,都過去了,你也別恨他了,那個人生老病死,于我們無關就是了。”
放不下仇恨,何嘗不是一種折磨。
沈彥之仰頭看著枯枝上的兩只雀鳥,許久才說:“他毀了母親一輩子,也毀了你我一輩子,我如何能不恨?”
這句話讓沈嬋沒繃住,眼眶中滾下了熱淚。
沈彥之說:“哭什麼,報了仇,不該歡喜嗎?”
他似在問沈嬋,又似在問自己。
沈嬋見他似乎已被仇恨折磨得麻痹,心痛如刀割,眼淚掉得更兇,聲問他:“阿兄現在歡喜?”
沈彥之角牽起一抹蒼白的笑:“自是歡喜的。”
沈嬋搖頭,淚如雨下:“你若是當真歡喜,我便不會難過這樣了。”
沈彥之抬手幫拭淚,問:“你難過什麼?阿兄大權在握,不好麼?”
沈嬋哽咽著問:“權勢有什麼好?”
沈彥之目變得很空,自己都沒留意到眼眶慢慢變紅了:“確實不好,奪走了阿箏,又奪走了你。所以我得握它,才沒人再能從我邊奪走什麼,甚至可以把失去的搶回來。這麼看,權勢也算是個好東西,不是嗎?”
沈嬋因為緒過激而大口呼吸,冰冷的空氣吸進肺里,像是刀子在心上豁了個口子,哭著問:“那就可以不折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嗎?我那個風霽月的阿兄去哪兒了?”
沈彥之神一變:“誰給你說了什麼?”
他視線往沈嬋后一掃,臉陡然難看:“木大夫去哪兒了?”
猜你喜歡
-
完結850 章
三國從忽悠劉備開始
漢靈帝西園租官,要不要租? 租!當然租!因為只要恰好租到靈帝駕崩前的最后一個任期,就等于直接租房租成了房東!租官租成了諸侯! 所以,匡扶漢室怎麼能只靠埋頭苦戰呢? 立功與買官并舉、才是最效率的王道。 不過,在做這一切之前,李俗首先得對正直的主公進行一番戰略忽悠才行。
830.7萬字8 13822 -
完結626 章

我,開局輔佐嬴政,成為六國公敵
張赫穿越大秦,獲得最強輔助系統,只要輔助嬴政,便能獲得十連抽。于是張赫踏上了出使六國的道路,咆哮六國朝堂,呵斥韓王,劍指趙王,忽悠楚王,挑撥齊王,設計燕王,陽謀魏王。在張赫的配合下,大秦的鐵騎踏破六國,一統中原。諸子百家痛恨的不是嬴政,六國貴族痛恨的不是嬴政,荊軻刺殺的也不是嬴政。嬴政:“張卿果然是忠誠,一己擔下了所有。”張赫拿出了地球儀:“大王請看……”
122.8萬字8 8438 -
完結1258 章
歡喜記事
穿越到剛剛招安封侯的土匪一家。親爹,威武勇猛愛闖禍。親孃,貌美如花愛愛闖禍。親哥,英俊瀟灑愛愛愛闖禍。……你問她啊?她就比較懂事了,剛剛從街上搶回來一壓宅夫君……
246.1萬字8 14919 -
完結25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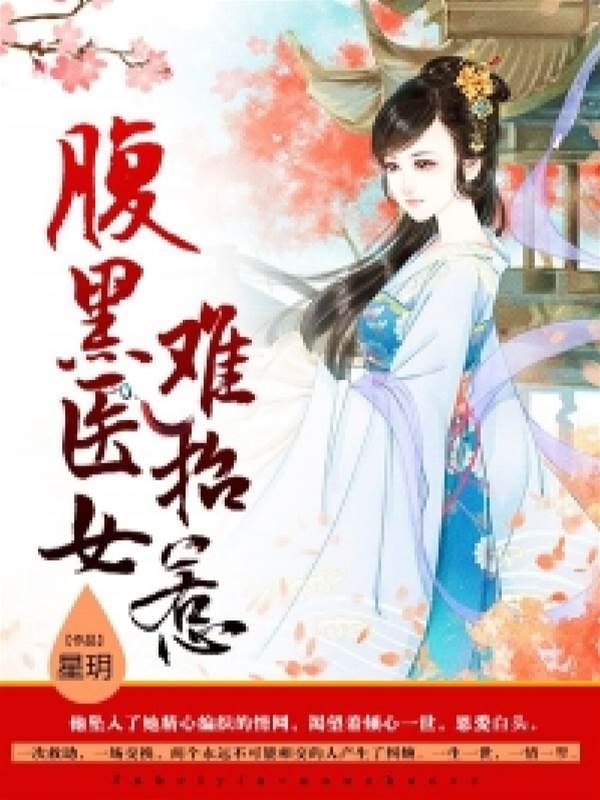
腹黑醫女難招惹
她本是現代世界的醫學天才,一場意外將她帶至異世,變成了位“名醫圣手”。 他是眾人皆羨的天之驕子,一次救助,一場交換,兩個永遠不可能相交的人產生了糾纏。 一生一世,一情一孼。 他墜入了她精心編織的情網,渴望著傾心一世,恩愛白頭。 已變身高手的某女卻一聲冷哼,“先追得上我再說!”
42.7萬字8 116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