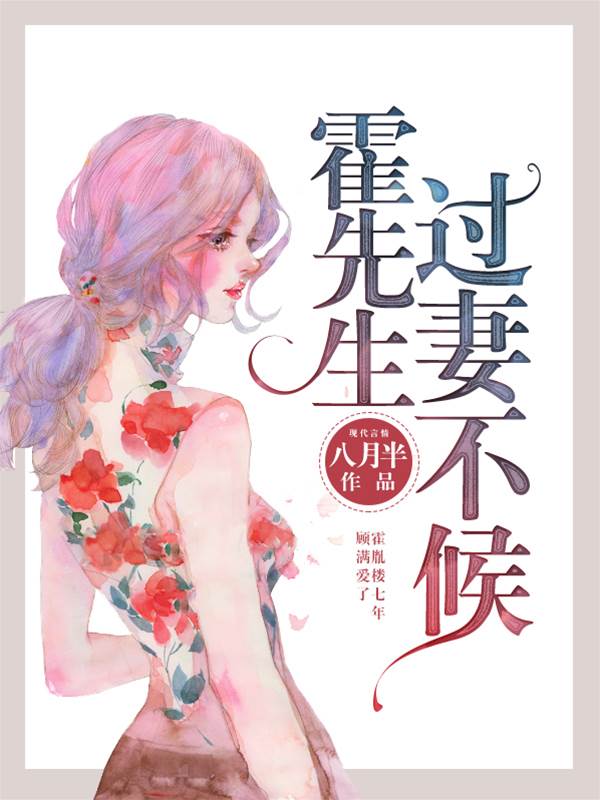《玫瑰撻》 第74章 晉江文學城首發
第七十四章
陳妄對于孟嬰寧這病印象很深。
他剛回來見到那會兒, 第一次見喝醉, 孟嬰寧折騰著演了一晚上娘娘,演累了到家, 小姑娘在角落里憋著嗚嗚咽咽地開始哭。
委屈地看著他說疼。
再后來,只要喝醉, 就都會這樣。
陳妄甚至還問過自己之前的一個心理醫生, 這種況一般可能會是什麼樣的原因造的。
沒見到本人并不好判斷,但是孟嬰寧況很輕,不算是什麼病,大概是以前或者小時候過什麼傷,當時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以至于直到現在這件事對還有些影響。
特別怕疼,倒也有可能,陳妄那會兒還仔仔細細地回想了一遍, 也沒想起來孟嬰寧小時候過什麼特別嚴重的傷。
孟家人一直把保護得好的, 在學校的時候也有人護著,沒怎麼被欺負著過。
再后來那幾次陳妄也試探問過,小姑娘嚴的就跟什麼似的,一句都問不出來了。
陳妄直到現在都不知道到底因為什麼疼。
包廂里熱鬧得很吵,音浪混著燈鼓點似的晃,都不是沒眼力價兒的人, 哄哄地起哄鬧了一會以后大家見好就收, 該蹦的蹦該鬧的鬧。
陸之桓湊到林靜年旁邊跟搶麥,角落里一張圓沙發全給倆人空出來了。
孟嬰寧歪著小腦袋瓜看了他好一會兒, 似乎是在反應他剛剛說了些什麼。
陳妄手過去拉的手,著指尖輕輕了,放緩了語速,又問了一遍:“這兒還疼麼?”
孟嬰寧眨了下眼,搖搖頭:“不了。”
“不疼了?”陳妄說,“那以前為什麼疼?”
孟嬰寧看著他,沒說話。
Advertisement
安靜了幾秒,拱著腦袋小貓似的往他懷里鉆。
小姑娘喝多了以后簡直小粘人附,黏黏糊糊趴趴的,酒蒸得整個人溫偏高,像一團燃燒著的小火爐。
應該也沒醉,就是有點兒多,意識看著至還是清醒的。
陳妄抬手,換了個姿勢側過來坐著,好讓鉆得更舒服點兒:“以前是為什麼,跟我說說?”
孟嬰寧扁著搖了搖頭,含糊地嘟噥:“不能說。”
“怎麼不能說?”
“這是我的小,”孟嬰寧從他懷里挪開,蹭遠了點兒,堅持地說,“誰都不能告訴。”
“我不告訴別人,”陳妄湊近了一點兒,“你只跟我說,行不行?”
孟嬰寧眉眼無打采地耷拉下來,有些沮喪地說:“你會笑話我的。”
陳妄看著的表,沒忍住笑了一聲。
“不會的,不笑話你,你看我的你不是也都
知道了?”
他聲音低沉溫,哄似的說:“不過你真的不想說,我也可以不知道。”
孟嬰寧面難,很糾結地看著他,有些猶豫。
“好吧。”
小姑娘勉為其難地說。
說完,就又不說話了。
陳妄也沒催。
他不是一個特別有耐心的人,但跟孟嬰寧在一塊兒,總是能讓他拿出自己全部的耐,好脾氣地哄著。
好半天,孟嬰寧終于開口,說了:“我那時候以為你是喜歡那種的,就,大波浪,很漂亮的那種,我就……”
孟嬰寧覺得有些難以啟齒:“我就也想變那樣。”
陳妄怔了怔。
孟嬰寧低垂著眼,似乎覺得丟人,完全不看他,委屈地說:“可是我不會用,我弄不好,還把卷發棒給摔壞了,被罵了,還燙了手,好久好久才好。”
Advertisement
陳妄看著,沒說話。
好半天,他才勉強找回自己的聲音,嗓子有些啞:“疼不疼?”
孟嬰寧吸了吸鼻子,抬手了一下眼睛:“特別特別疼,一直疼。”
“陳妄,我就是我,就算你不喜歡,我也只能是我,我試過了,但我……變不,我不能為了讓你喜歡,就拋棄自己了,那樣不對,”孟嬰寧紅著眼睛抬起頭來,看著他,“我變不你喜歡的樣子,我當時就是覺得,我要是不能變那樣,你是不是就永遠都不會喜歡我……”
沒說完。
陳妄手,拽著手臂扯進懷里。
男人的膛邦邦的,像塊鐵板,孟嬰寧鼻子撞上去,有點兒酸。
想抬手,發現本不了。
男人手臂收得很地抱著,勒得孟嬰寧覺得自己骨頭都有點兒疼。
“誰告訴你我喜歡那樣的?”陳妄的聲音沉沉地在頭頂上方響。
“我看到的,”孟嬰寧說,“那時候你總跟那個學姐在一塊兒,我看到好幾次了,你還給買了杯子。”
小姑娘腦袋在他口蹭了蹭,聲音悶悶的:“們都說是你朋友。”
頓了頓,又補充:“不喜歡游戲機,覺得稚,你就把咪咪給我了。”
聲音很哀怨。
陳妄手臂終于松了松,垂眸瞅:“是不是傻?那個就是給你的,老子跑了六七家店。”
“我現在知道了呀,”孟嬰寧仰起腦袋,“那時候又不知道的。”
“知道了也沒了。”陳妄說。
“有的。”
陳妄沒聽清,垂頭:“嗯?”
“我撿回來了……”孟嬰寧小聲說。
陳妄看著。
孟嬰寧別開眼,有些不好意思地說:“你走了以
后,我給撿回來了。”
Advertisement
孟嬰寧坐在沙發上晃悠著兒,聲音特別輕:“就,有點兒舍不得丟……”
陳妄沒說話,忽然站起,接著把也拽起來。
孟嬰寧腳上高跟鞋剛剛是掛著的,剛踩上,就被他扯著往前走。
喝得有點兒多,腦袋昏昏漲漲的,突然一站起來有些站不穩,孟嬰寧趔趄了兩步,另一只手拽著他服堪堪穩住沒摔了,跟著他走。
男人拉著走到門口,在一片起哄聲中推開了包廂門,出去。
“哎,”孟嬰寧在后面跟得很艱難,步子也有些飄,“干什麼去呀?”
陳妄沒說話,拐進里面更深的走廊,基本沒什麼人,一排排的包廂空著。
他隨手推開一間,人扯進來,甩上門,嘭的一聲。
孟嬰寧迷迷瞪瞪地被按在磨砂玻璃門上,被迫抬起頭,封住。
齒纏,有輕微又很清晰的聲音,不知道是不是酒把所有的神經和都無限放大,總覺得好像比哪次都激烈。
發麻的舌尖有些招架不住地往回,孟嬰寧無意識咽了下口水,剛躲開一點點距離,瞬間就被撈著后頸重新按上去。
陳妄低下頭,吻著耳,低沙喑啞:“不想等領證了。”
孟嬰寧本來被他親得迷迷糊糊的,瞬間嚇得整個人都清醒了,抖著手直推他:“現在不行……”
陳妄以為在這兒不好意思,含住嘟嘟的耳珠咬了咬,扣著纖細腰肢的手向下,翻起擺:“回家。”
孟嬰寧人一哆嗦,著子聲:“回家也不行……”
男人指腹帶著薄繭,有些糙的帶起一陣栗,氣息燙著耳廓:“怎麼不行。”
孟嬰寧站都站不穩了,靠在他上,快哭了:“就……”
Advertisement
沒說下去。
陳妄一頓。
厚的。
……厚的?
-
陳妄沒談過,但男人麼,片子不可能沒看過,甚至在氣方剛的年時期,男生只要湊到一堆不是聊游戲就是聊這些有的沒的,還觀欣賞過不。
就怎麼,也不應該是厚……的?
陳妄垂頭。
孟嬰寧看起來恥得下一秒就會哭出來,抬手捂住臉,嗚了一聲,在外面的耳朵在昏暗的燈下是紅的,連著脖頸都紅。
“我今天……不太方便。”小姑娘用蚊子似的音量說。
甚至聽起來還有些失和懊惱?
陳妄沉默幾秒,剛剛那點兒心思全沒了,聲音重新恢復到一片冷漠的低沉:“你不方便還喝酒?”
孟嬰寧:“……”
孟嬰寧茫然地抬起頭來,顯然沒反應過來他重點為什麼能
跑偏的這麼快。
男人的臉不是特別好,角耷拉著。他臉一板,氣場就上來了,無形的威擴散。
陳妄后退了半步,眼一瞇看著,訓人似的:“還敢加冰,孟嬰寧,你命不想要了?”
“……”
好嚇人噢。
孟嬰寧了脖子,氣勢被他得半點兒都沒剩下:“那我不是不怎麼疼。”
陳妄冷笑了一聲:“你就作吧。”
孟嬰寧自知理虧,其實本來也沒想著真的要喝多,但畢竟是陸之桓給開的慶祝會,想著就一點兒意思意思,結果一玩起來就上頭,這些也就忘了。
抬手去拽他的手指,又想到剛剛這手指過哪里,沒忍住又臉紅了:“那我們回去?”
陳妄耷拉著眼睨:“回去接著喝?”
“我喝個果吧,還有椰,”孟嬰寧想了想說,“大家因為我才聚的,我們提前走了不太好。”
孟嬰寧是喜歡熱鬧的格,也確實很久沒跟他們出來玩,陳妄沒說什麼,領著回去。
點歌機放著一首舒緩的英文歌,包廂里正在熱火朝天地討論,發小一幫人撅著屁背對著門,腦袋湊到一起,聊得很專注,誰都沒有注意到包廂門被推開了。
孟嬰寧和陳妄一進來,剛好聽到陸之桓說話:“我覺得不能,就看陳妄哥那格,一個小時?你們瞧不起誰?”
陸之桓是陳妄腦殘,堅定地搖了搖頭:“不能夠,起碼兩個吧,五千。”
“兩個兒兩個,”二胖說,“陳妄一個對象都他媽沒過。一個都沒有,天天跟五指姑娘一起玩的你指他頭回上戰場就倆點兒?換你你能嗎?你想想你當年,有兩分鐘沒有?”
二胖言之鑿鑿。
陸之州在旁邊悠悠然說:“但陳妄力確實好,一個小時吧,一萬。”
陸之桓回過頭來,看著他:“哥,我以為你是個正經人。”
說完又回頭,兜里皮夾子掏出來往桌上一拍,高聲道:“我跟我哥!兩萬!”
“你倆行不行啊,力好沒用,這玩意兒不是靠力的,”二胖著下想了想,說,“二十分鐘吧,兩萬五。”
陸之桓沒說話。
二胖嘆了口氣:“不能再多了,不是我不給妄哥面子,二十分鐘我覺都是往高了估的。”
他說完一抬頭,看見了剛好一首放完屏幕暗下來的點歌機上倒出來的兩道人影。
二胖回過頭來。
孟嬰寧還沒太反應過來,一臉懵地站在門口。
陳妄懶洋洋地靠著玻璃門框子,面無表地看著他們。
二胖的表凝固了。
所有人都跟著回過頭來。
“哇,”咔噠一聲,林靜年點了一下手機計時,抱著臂靠進沙發里。
“有十分鐘呢。”林靜年愉悅地說。
猜你喜歡
-
完結171 章

拒嫁豪門,少奶奶又逃了
參加男朋友家族聚會,不過他哥哥好像…… 蘇小小獨自穿過走廊拐角的時候,突然被男人拉進漆黑的房間里強吻了。 男主:「這就是你說的重逢?」 女主:「別在他面前求你了」
49.2萬字8.33 18026 -
完結1020 章

我閃婚了個億萬富翁
被催婚催到連家都不敢回的慕晴,為了能過上清靜的日子,租了大哥的同學夜君博假扮自己的丈夫,滿以為對方是個普通一族,誰知道人家是第一豪門的當家人。……慕晴協議作廢夜君博老婆,別鬧,乖,跟老公回家。
176.1萬字8.18 310249 -
完結3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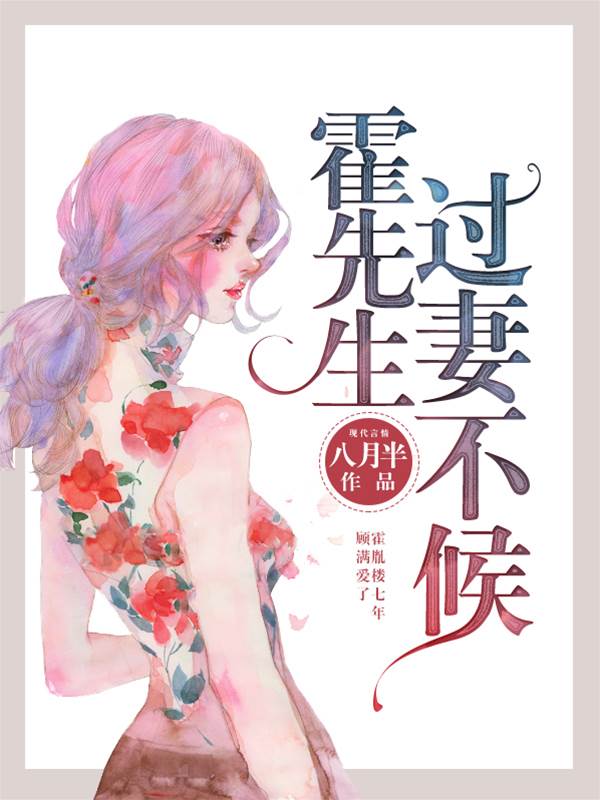
霍先生,過妻不候
顧滿愛了霍胤樓七年。 看著他從一無所有,成為霍氏總裁,又看著他,成為別的女人的未婚夫。 最後,換來了一把大火,將他們曾經的愛恨,燒的幹幹淨淨。 再見時,字字清晰的,是她說出的話,“那麽,霍總是不是應該叫我一聲,嫂子?”
29.6萬字8 83350 -
完結228 章

月光轟鳴
久別重逢,陸敏跟杭敬承閃了婚。 介紹人聽說兩人中學時期是同學,陸敏還有段給杭敬承寫情書的往事,直言這叫有情人終成眷屬。 實際上,兩人婚後一分居就是數月。 再見面後杭敬承提出第二天送陸敏去上班。 她知道這行為出于禮貌,答應了。 半晌,床墊微響。 “你在……”低沉含糊的聲音在身後響起,她以為他還有什麽重要的事沒說,稍稍回頭。 杭敬承:“你在哪個學校?” 陸敏:...... 杭敬承出身高知家庭,卻一身反骨,做起電影,一路做到總制片位置,事業風生水起。 身邊人都知道他英年閃婚,是因為杭家給的不可抗拒的壓力。 見陸敏又是個不讨喜的主兒,既沒良好出身,也沒解語花的脾性,紛紛斷言這場婚姻不可能維持多久。 陸敏自己也擔心這場婚姻維持不下去,跟杭敬承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他靠在床頭,懶洋洋睇着她,修長手指卷起她耳邊的頭發絲纏繞幾圈,“怎麽着,說我為什麽要跟你離?” “說我,總板着臉。” “哦。那你多笑笑。” “......” “笑一個呗,笑一個給你咬。” 陸敏笑是沒笑出來,耳根子噌地紅了。 這夜夜深人靜,陸敏被身邊人攬在懷裏,睡意朦胧間聽見散漫呓語: “離什麽,不離......” “十七歲的杭敬承告訴我。” “摘到手的月光無可歸還。”
38.3萬字8.18 361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