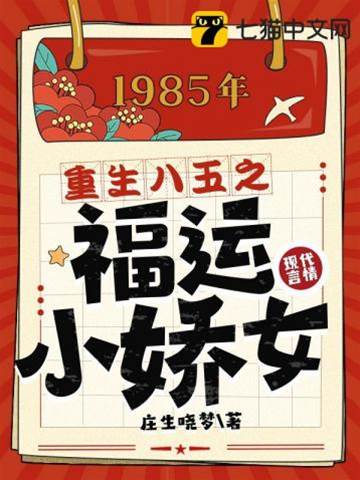《漸漸》 第4章 夏蟬
清晨線和,從窗戶斜斜照進來。樓下種了許多梧桐,已經很有年份,每棵都囂張地茂盛著,從四樓往外都能見蔥蘢的綠葉。
徐未然兩只手還抓著邢況的T恤兩邊。剛才重心不穩,手胡地出去,抓救命稻草一樣去抓他,手指過棉質的料到了男生勁瘦結實的腰。
空氣彷如都停滯下來,四周安靜得能聽到空調出風口微弱的聲響。
明明是白天,教室里依舊亮著燈,財大氣地鋪張著。
線發了瘋般涌進來,讓看到了在他的鼻翼左側,上面有顆小小的、淺淺淡淡的一顆痣。
他鋒利冷逸的一張臉被這顆小小的痣中和出了一分和,兩分妖冶,三分蠱。
男生的話落下以后,徐未然覺自己應該是被嫌棄了。趕松開手,離他遠了些,把椅子往外拉,跟他保持著一個比正常同桌關系要遠的距離。
“對不起。”說話時不敢看他。
邢況滿不在意地收回目,轉回去。
“況哥,”靠墻那邊坐著的李章沖這里說:“怎麼剛來就逗人家小姑娘啊,人小姑娘臉皮薄,經不起你逗。”
旁邊的錢蒙接口:“你怎麼知道臉皮薄,你親過啊?”
李章甩了他個嫌惡的眼風:“說了別逗!”
“李章,我發現你很奇怪啊,”錢蒙上下打量他一遍:“怎麼老是關心未……”
后面一個字被李章狠狠地捂回了里。
進高三后基本沒有什麼知識點要講,每天都被隨堂測驗和錯題講解充斥著。上課鈴響后吳婷從外面進來,把英語卷子發下去。
薄薄的一張試卷,徐未然需要在凹凸不平的課桌上墊本書才能往卷子上寫字。吳婷從講臺上看見,過來說:“同學,是閉卷測試,把書放回去吧。”
Advertisement
“可我墊的是數學書。”
“是書就都不可以的。”吳婷語氣溫和。
徐未然只能把書本拿下去。
桌面被劃得不像樣子,坑坑洼洼。字寫得很吃力,稍不留神試卷就破了。
幾分鐘過去后,一邊的邢況突然丟了筆,靠在椅背上看。
他作不是很大,徐未然的目專心致志掉在卷子上,沒有注意到他。
邢況以前有過幾個同桌,大都堅持不了兩天就走了。這孩也是倒霉,轉學過來的時候班里只剩了唯一一個座位,就算想換也換不了。
孩今天扎了頭發,出一截白細膩的后頸。臉頰兩邊掉著碎發,發。一張臉小巧,白得像雪,側臉溫得不可思議。形瘦弱小,天生有些怕冷,在大夏天里都還套了件淺綠的外套。
都著,像溫室里細心呵護的白茉莉,稍微來一陣風就能把刮倒。
不知道怎麼撐到現在的。
邢況從來不喜歡多管閑事,往日里也不到他多管閑事,沒等他說什麼,那些同桌就自自發地被走了。
只有這一個,明明又又,說話時聲音弱得像蚊子哼哼,好像把聲調多提高一個度對來說都是酷刑一樣,偏偏到現在了還能巋然不地在他旁邊的位置上坐著。
脆弱又堅強。
兩種極致的反差在上異常和諧地共存著。
整個教室里都是筆疾書的刷刷聲。清才中學的學生難管是難管了些,但都對學習很上心,沒有人會拿自己的前途不當回事。
只有邢況。
吳婷站在講臺上,看到邢況已經有十分鐘沒有筆,眼神還一直堂而皇之地落在他那個新同桌上。吳婷拿教敲了敲講臺,提醒底下的學生:“都好好考試,這次績我是要發給你們父母看的。”
Advertisement
邢況非但沒有意識到這句話是沖他說的,反而還旁若無人地把徐未然的筆和試卷全都拿了過來,放在他平整的桌面上。
他拎著自己的書包和卷子起,從后面繞過去,拎著孩領,像拎一只小一樣把提到了他的座位上。
他在的椅子里坐下來,坦然地、懶散地說:“換個位置。”
徐未然不明所以地看他。
邢況的聲音不是很大,可因為教室里安靜得過分,他的聲音多顯得突兀,有不學生都扭頭朝他們這里看過來,眼神里滿是驚詫。
吳婷雖然生氣邢況不把這個老師放在眼里,可也早聽說過邢況的那些榮事跡,并不敢惹這個男生,把不滿全都憋在了嗓子眼里。
邢況仿佛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樣,拿筆在試卷上胡填著ABCD,字寫得十分潦草。
隨堂測驗結束后,徐未然鼓足了勇氣問旁邊的人:“位置、換過來吧。”
聲音還是很小,又磕磕的,好像跟他說話是件很需要膽子的事。
邢況側頭看,目依舊冷淡,手過去把自己那兩本充數一樣的書拿了過來,擱在斑駁不平的桌上,又把的書和書包都給。
一個字都沒有說,淡漠移回了視線。
是很明顯的,不打算跟把位置換回來的舉。
徐未然不能確定他的這一舉是不是出于好心想幫。可自己畢竟了益,不好什麼都不表示。
“謝謝。”說。
男生仍沒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巋然不地把他整個人罩著,讓覺得雖然離他很近,卻永遠也沒辦法朝他靠近一步。
教室里有很多生都朝他們這邊看過來,眼神絕對算不上善意。尤其是包梓琪和張絨,目里明顯裹了層火。
Advertisement
徐未然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被這些生當了公敵。
在旁邊的男生,材高大清瘦,五俊逸人,氣質冷冽,是那種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他在這個學校有著什麼地位的男生。外形條件太過優越,一舉一都引人注目,像是在普通的蕓蕓眾生里唯一發的星星,沒有生會不被他吸引。
是們青春時里遙不可及又拼命追逐的夢想。
徐未然從被安排跟他坐同桌開始,會有人對產生敵意,躲在暗放冷箭,八都是因為邢況。
雖然這個男生明明連一個好臉都沒有給過,會幫可能只是出于基本的禮貌。
但那些生是不會想到這一層的。們只會變本加厲地拿當假想敵。
到了中午,徐未然仍舊趴在桌上做題,沒有要出去吃飯的意思。
早飯和晚飯可以在家里解決,只是中午不吃而已,可以過去。
何況這幾天胃口本來就不好。
因為邢況跟徐未然換了位置,李章得以離生更近了點兒,問:“小妹妹,一起去吃飯唄。”
徐未然搖頭:“我不。”
李章看看瘦小的板,及膝擺下兩條細細的,勸:“你再不吃飯瘦得只剩骨頭怎麼辦?”
“不會,”沒聽出他話里的玩笑,認真回答:“我早上吃了很多,晚上也會吃多點兒。”
李章被這副正兒八經解釋的樣子逗笑了:“早上都吃了什麼啊?”
徐未然回憶了一遍:“一個包子,一個蛋,一杯牛。”
李章不停笑:“吃這麼多啊,是我飯量的三分之一欸。”
徐未然后知后覺地發現這人在逗,沒再說什麼了。
李章去拉胳膊:“別寫了,去吃飯唄。”
Advertisement
徐未然躲開他的手:“真的不想吃。”
李章還想勸,被錢蒙懟了一拳:“你是不是有病啊,人家不想吃你非干什麼。”又問邢況:“況哥,去食堂唄。”
邢況拿著手機回了個消息,口氣清淡:“你們先去。”
李章只好和錢蒙先走了。
教室里的溫度保持在一個適宜的范疇,窗外刺眼的徒勞無功地熱烈。
徐未然知道這個學校的學生要不就是自己本優秀,要不就是家庭條件優秀,兩者總要選其一。后者對來說顯然沒什麼機會了,只能拼命做到前者。
月底就要進行模擬考,不想讓自己的績太難看。中午不需要出去吃飯,可以多出兩個小時的時間做一套數學卷子。
在最后一道選擇題上猶豫了很久,最后還是沒找到解題思路。習慣咬著筆頭,決定看哪個答案比較順眼就選哪個好了。
一邊的男生突然開口:“你多高?”
聲音又低又沉,像摻了磁,聽得人心里發,讓靠近他的那邊耳朵不控制地紅了。
可他說話的容卻絕對算不上好聽。徐未然看了眼空的教室,確定除了他們外沒有其他人了,他又沒有在跟人通話或者是視頻,這才奇怪看他:“什麼?”
邢況仍舊看著手機,聽見問,淡淡地又重復一遍:“你多高。”
徐未然覺得這人莫名其妙。
為什麼會突然問多高?
難道是在嘲笑矮?
的個子在同齡人中算不上出挑,到現在了只有一米五八而已。相倪經常發愁,總是說如今的孩個子要長到一米六五才算合格,營養品箱箱地給買,可吃了以后并沒有什麼顯著的效果。
握手里的筆,有些惱:“怎麼了?”
即使不太高興,可說話聲音依然的,一點兒威懾力都沒有。
邢況放下手機,朝這邊側了點兒頭。
“不好好吃飯的話,”邢況的語氣不是那麼冷了,還莫名給人一種他此刻是在逗小孩的錯覺:“會長不高的。”
徐未然:“……”
更加惱了:“那跟你又有什麼關系?”
“沒關系,”他沒再看,目仍舊放在手機上,側臉線條鋒利又迷人:“就是想提醒你,小孩要好好吃飯。”
徐未然更是滿腦子莫名其妙。
他看上去也才十八九歲而已,憑什麼,能這樣理直氣壯地說是小孩!
雖然是不怎麼高,可也沒有很矮吧。
不想再說話了,趴在桌子上生悶氣。想往下繼續做卷子,可想了半天都想不起那個很簡單的公式到底是怎麼背的!
“不想寫就別寫。”
男生再次開口,明明是冰山一樣多說一個字都費勁的人,現在卻打定了主意要跟過不去一樣:“出去吃飯。”
語聲頤指氣使的,讓人高興不起來。
徐未然仍舊不彈,把他的話當耳旁風。
邢況難得耐著子解釋一句:“我在這,們不敢過來。”
窗戶和門都無所謂地開著,冷氣吐得均勻,與外面吹來的熱風和諧地纏綿出一室恰到好的溫涼。
前面半句是:我在這。
后面跟出的結果是:們不敢過來。
所以要傳達給的信息是,不用再自似的守在位置上,暗不會再有朝施放的冷箭,是可以離開這個教室的。
與跟換位置一樣,再次從指中施放了善意。
徐未然看了他一會兒。男生松松垮垮地往后靠著,上穿了件黑T恤,下穿了件并不算薄的黑工裝,修飾出男生無安放的兩條長。服略寬松,可仍能看出男生優越的高比例,清瘦又不會單薄的材。
只要看一眼,心上就會有被擊中的覺,從心臟開始,呈漣漪狀往全擴散。
又又麻。
是徐未然形容不出的,清爽好的年。
猜你喜歡
-
完結1161 章
他養的小可愛太甜了
他是商界數一數二的大人物,眾人皆怕他,隻有少數人知道,沈大佬他……怕老婆! 沈大佬二十八歲以前,對女人嗤之以鼻,認為她們不過是無能,麻煩又虛偽的低等生物。 哪想一朝失策,他被低等生物鑽了空子,心被拐走了。 後來的一次晚宴上,助理遞來不小心摁下擴音的電話,裡麵傳來小女人奶兇的聲音,「壞蛋,你再不早點回家陪我,我就不要你了!」 沈大佬變了臉色,立即起身往外走,並且憤怒的威脅:「林南薰,再敢說不要我試試,真以為我捨不得收拾你?」 一個小時之後,家中臥室,小女人嘟囔著將另外一隻腳也塞進他的懷裡。 「這隻腳也酸。」 沈大佬麵不改色的接過她的腳丫子,一邊伸手揉著,一邊冷哼的問她。 「還敢說不要我?」 她笑了笑,然後乖乖的應了一聲:「敢。」 沈大佬:「……」 多年後,終於有人大著膽子問沈大佬,沈太太如此嬌軟,到底怕她什麼? 「怕她流淚,怕她受傷,更……怕她真不要我了。」正在給孩子換尿布的沈大佬語重心長的
105.2萬字8 127617 -
完結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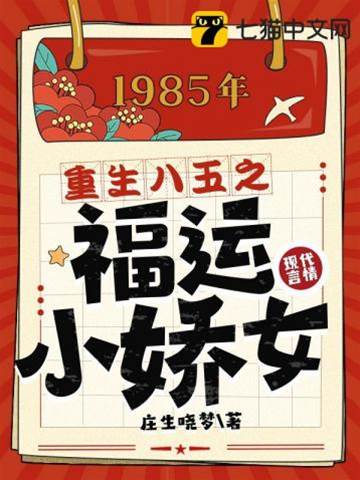
重生八五之福運小嬌女
前世,喬金靈臨死前才知道爸爸死在閨蜜王曉嬌之手! 玉石俱焚,她一朝重生在85年,那年她6歲,還來得及救爸爸...... 這一次,她不再輕信,該打的打,該懟的懟。 福星錦鯉體質,接觸她的人都幸運起來。 而且一個不留神,她就幫著全家走向人生巔峰,當富二代不香嘛? 只是小時候認識的小男孩,長大后老是纏著她。 清泠儒雅的外交官宋益善,指著額頭的疤,輕聲對她說道:“你小時候打的,毀容了,你得負責。 ”
70.5萬字8 21891 -
連載552 章

妻女死祭,渣總在陪白月光孩子慶生
【重生+雙潔+偽禁忌+追妻火葬場】和名義上的小叔宮沉一夜荒唐后,林知意承受了八年的折磨。當她抱著女兒的骨灰自殺時,宮沉卻在為白月光的兒子舉辦盛大的生日宴會。再次睜眼,重活一世的她,決心讓宮沉付出代價!前世,她鄭重解釋,宮沉說她下藥爬床居心叵測,這一世,她就當眾和他劃清界限!前世,白月光剽竊她作品,宮沉說她嫉妒成性,這一世,她就腳踩白月光站上領獎臺!前世,她被誣陷針對,宮沉偏心袒護白月光,這一世,她就狂扇白月光的臉!宮沉總以為林知意會一如既往的深愛他。可當林知意頭也不回離開時,他卻徹底慌了。不可一世的宮沉紅著眼拉住她:“知意,別不要我,帶我一起走好嗎?”
101萬字8.33 184598 -
完結179 章

灼灼浪漫
大雨滂沱的夜晚,奚漫無助地蹲在奚家門口。 一把雨傘遮在她頭頂,沈溫清雋斯文,極盡溫柔地衝她伸出手:“漫漫不哭,三哥來接你回家。” 從此她被沈溫養在身邊,寵若珍寶。所有人都覺得,他們倆感情穩定,遲早結婚。 有次奚漫陪沈溫參加好友的婚禮,宴席上,朋友調侃:“沈溫,你和奚漫打算什麼時候結婚?” 沈溫喝着酒,漫不經心:“別胡說,我把漫漫當妹妹。” 奚漫扯出一抹得體的笑:“大家別誤會,我和三哥是兄妹情。” 她知道,沈溫的前女友要從國外回來了,他們很快會結婚。 宴席沒結束,奚漫中途離開。她默默收拾行李,搬離沈家。 晚上沈溫回家,看着空空蕩蕩的屋子裏再無半點奚漫的痕跡,他的心突然跟着空了。 —— 奚漫搬進了沈溫的死對頭簡灼白家。 簡家門口,她看向眼前桀驁冷痞的男人:“你說過,只要我搬進來,你就幫他做成那筆生意。” 簡灼白舌尖抵了下後槽牙,臉上情緒不明:“就這麼在意他,什麼都願意爲他做?” 奚漫不說話。 沈溫養她七年,這是她爲他做的最後一件事,從此恩怨兩清,互不相欠。 那時的奚漫根本想不到,她會因爲和簡灼白的這場約定,把自己的心完完全全丟在這裏。 —— 兄弟們連着好幾天沒見過簡灼白了,一起去他家裏找他。 客廳沙發上,簡灼白罕見地抵着位美人,他被嫉妒染紅了眼:“沈溫這樣抱過你沒有?” 奚漫輕輕搖頭。 “親過你沒有?” “沒有。”奚漫黏人地勾住他的脖子,“怎麼親,你教教我?” 衆兄弟:“!!!” 這不是沈溫家裏丟了的那隻小白兔嗎?外面沈溫找她都找瘋了,怎麼被灼哥藏在這兒??? ——後來奚漫才知道,她被沈溫從奚家門口接走的那個晚上,簡灼白也去了。 說起那晚,男人自嘲地笑,漆黑瞳底浸滿失意。 他凝神看着窗外的雨,聲音輕得幾乎要聽不見:“可惜,晚了一步。”
30.6萬字8.18 2007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