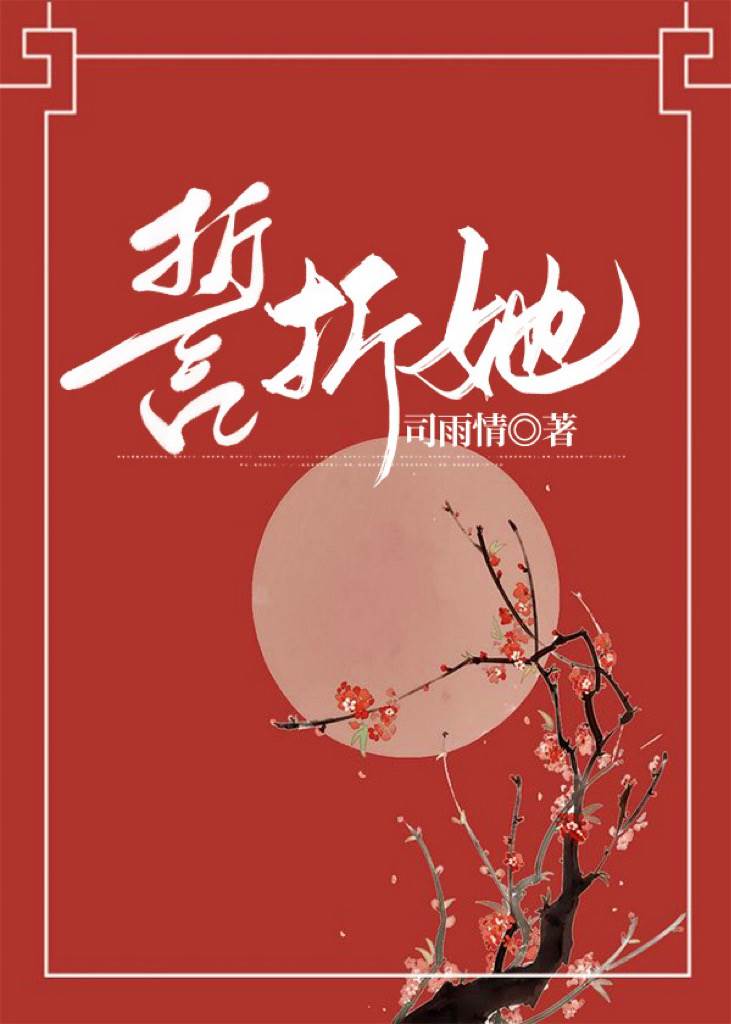《被庶妹替嫁后》 第62章 第六十二章
平城至京都, 府役開道,將迎親的花轎引到城外,杳杳道蔓延無際, 這才踏上送親的路途。
途中轎子停下,拾已與翹楚鉆轎攆。
郁桃瞧見人影晃, 問:“你們怎麼上來了?”
翹楚穩穩當當端著銀盆, 一手掀開紅蓋頭, 笑嘻嘻道:“咱們姑爺說,路途還長, 姑娘且把妝面洗凈,卸掉頭冠, 吃些東西再好好睡一覺。”
郁桃看著面前的小案幾, 拾已從匣子里一樣一樣端出各的點心。
“哪里來的這麼多點心。”
翹楚揚起笑, 頗有幾分驕傲:“姑爺帶的, 比咱們夫人還要心吶。”
郁桃悶頭沒說話,只是一口一個點心, 一面兒撇過臉任由翹楚凈面。
案幾差不多空時,喝了一口茶, 吃飽喝足隨之而來的便是混沌睡意。
晨起過早,親迎路上的忐忑不安, 被這睡意一擾, 反而變淡。
郁桃斜靠在榻上, 隨著花轎悠悠晃晃,打起瞌睡。
隊伍不休不止的行進,偶有驛站停歇, 郁桃也是被人一雙手牽進屋中。
不等說話, 韓祎留下一句:“好好休息。”從未做多停留便離去。
郁桃心里犯嘀咕。
那唐媽媽笑說:“姑爺牽姑娘進來, 那是以示珍重;不做停留,那是未親拜堂,不做越矩之事,尊您敬您。依我看,姑娘遇到了有心人。”
任他們夸出花來,郁桃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心里還在介懷什麼,時常泛起莫名的心虛。
路上耽擱的久,郁嵚齡與郁哲宏在送親的隊伍中,有些擔心誤了時辰。
不過蘇柯遷悠哉道:“還不是心疼弟妹在路上累著,晚上多歇息會兒。”
約莫第五日晨,親迎的隊伍在一驛站停下。
Advertisement
郁桃從睡夢中驚醒,迷糊中看見翹楚和拾已鉆進馬車,將扶起。
“快要京城了,姑娘神些,奴婢喊了嬤嬤來給你上妝。”
郁桃沾著涼帕子醒神,那收好的嫁上,翹楚伺候一一穿上,
許是這幾天在馬車上呆的太多,吃的又太好,郁桃總覺得腰間前的有些。
吸了吸氣,看著桌上的糕點,暫且停了一頓,眼饞著,沒有再手去拿。
不知是過了多久,聽見此人聲鼎沸,鞭炮遠遠地如雷鳴炸響,能聞見的火藥味兒。
郁桃頭上已經遮上蓋頭,聽見翹楚在耳邊說‘姑娘,落轎了’,接著被扶起,攙下花轎。
周邊似是比平城還要熱鬧,此起彼伏的雜談聲里,還有孩嬉笑打鬧。
閆韓侯府的儀制自然繁瑣,郁桃被那雙手帶著,上石階,過火盆,走百子百福廊,最后登高堂。
贊者高嘹亮的嗓子哦,‘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
跟著拜過高堂,拜過天地。最后一道,轉相對時,低頭看見面前那雙男子的鞋履,方才覺得有些真實。
這就算拜過天地了啊......
道賀聲里,被圍擁著往另一去。路不算近,廊廡轉過許多道,還有好幾院門,像是從一府邸到了另一府邸,只是牽著的手,始終沒有松開。
溫暖,干燥,指節有層薄繭。
被安置在大紅的喜床上,聽見一道爽朗的嗓音戲道:“咱們新郎可要坐在新娘子的對面”。
熱鬧聲里,多是婦人的笑聲,喜婆說著吉利討喜的撒帳歌,“一進新房,雙朝,恭賀新郎,滿門熱鬧,蘭桂騰芳,燕爾新婚,喜報吉祥,諸位親長,聽撒房:一撒榮華富貴,二撒金玉滿池塘,三撒三元及第早,四撒龍配呈祥,五撒五子拜宰相,六撒六合同春長,七撒夫妻同偕老,八撒八馬轉回鄉,九撒九九多長壽,十撒十全大吉祥......1”
Advertisement
從前郁桃聽張錦菱說過,這鬧新婚,喜婆最唱一些沒沒臊的詞,如今坐在床上,左耳聽‘房’,右耳又是‘夫妻偕老’,怪讓人害臊。
棗子花生谷子紛紛揚揚落下,墜在大紅的間,被頂著頭冠蓋頭,并不知道幾顆落在頭頂的谷子花生,被人手輕輕撿走,只聽到外頭的哄笑兀的高漲。
喜婆唱完撒帳,又唱‘秤桿上頭如油,一路星子頂到頭。’
詞兒當真是俗的讓人臉紅,但逢喜事,越是富貴的人家越嗆俗的詞兒。
郁桃了汗的手心,看著一道影走近,片刻蓋頭落。
通亮的燭火燃進帳中,映出一張瑩白的臉來,上紅,發間的烏黑,鋪在臉頰上嫵的霞彩,無一不染就一副秾艷的壁畫,鮮活的火在眸中跳躍。
韓祎持秤桿的手微微一頓。
喜婆自是妙詞從出,眾人催促著新人飲下合巹酒。
方才坐著,還不覺著冠子太重,此時需站起,腳下有些發麻,勉強行兩步倒也瞧不出什麼。
只是飲合巹酒,頭卻難以抬起半分。
郁桃悄悄漲紅了臉,不往前行半步,那樣離得實在太近了些。
韓祎瞧著,不聲的略略低頭,一飲而盡。
閆韓侯府的房鬧到此時,變好便收,不肖人多說,合巹酒飲下,便陸續離去,屋中一時安靜,只剩幾人。
郁桃頗有些尷尬的立在原地,不知此時應是站著還是坐著合宜。
燭火搖曳間,韓祎隨意的取過手中的瓷杯,放漆盤中,淡聲道:“你且休息,外頭還有客人,我晚些過來。”
“好......”郁桃未假思索,差些咬到自己的舌尖。
韓祎看著沒說話。
Advertisement
他眼中映出的模樣,俯,抬手向腦后。
郁桃微微啟,僵立在原地,心快要躍出腔,不知如何間,唰的閉上眼睛。
韓祎頓了下,眸中漾過一不易察覺的笑意。
片刻后,郁桃覺自己頭上忽然一輕,耳邊劃過淡淡的嗓音。
“頭冠這般重,我先替你摘下來。”
爾后便是輕輕的腳步聲,消失在門外。
郁桃:“......”
默默了袖中的拳頭,一臉悲憤的睜開眼,映眼簾的便是那一頂華麗無匹的頭冠。
兩抹紅‘蹭’爬上臉頰,郁桃不忍的捂住雙目。
天啊,將才在想什麼?
滾燙的臉頰在手心里,指尖劃過脂,在指頭上留下一道紅痕。
竟然以為韓祎是要......
.
郁桃從來都是既來之則安之的主兒,一應喚人伺候沐浴梳洗,換過衫,舒舒坦坦的坐在凳子前,吃過上頭的糕點,還不忘喝上兩口甜酒。
還是唐媽媽攔著,“食多了不好,姑娘鮮飲酒,當心吃醉。”
如此才收了手,乖乖上了那張寬敞的喜床。
起初還忐忑著,在床上坐立不安,但等到夜漸漸深了,外頭的喧鬧聲還未停止,掩打了個呵欠,靠在枕上不由自主闔上眼。
郁桃只覺自己睡在一片綿中,綢緞錦被冰涼。
但沒多久,這片獨屬于的舒適,就被人一點一點的拉扯去。
不大高興的翻,隨手朝那打去。
一聲清亮‘啪’響起,郁桃迷糊間,覺著手心有些火辣辣的痛。
委屈的癟癟,抱怨道:“拾已,你都將我弄痛了。”
回應的卻只是按上肩膀的一只手,郁桃不大高興的蹙起眉,手去拂開,“才睡下呢,怎麼這個時辰就要起......”
Advertisement
然而,下一刻,一道沉沉的嗓音傳耳中。
“你睜眼看看,我是誰?”
郁桃耳朵了,霎時驚醒,唰的坐起,看見了靠在床頭的男人,只著一里,正看著。
郁桃巍巍抬起手指,聲音還抖著,問:“你......怎麼在我房中?”
韓祎瞧著,似捉不一般,將從頭打量到腳。
郁桃猛地一,躲在墻角,想起如今的境,原來已是羊虎口。
男人一向淡然的臉上出點耐人尋味的笑。
他手握住的手腕,往回帶了帶,兩人呼吸相間,糲的指尖挲的下。
“郁桃,親也忘了嗎?”
瑩亮的燭火照在臉頰上,郁桃像被掐住頸項的小貓,去拉那只住下的手。
但,它們被反握住。
郁桃看見韓祎靠近,睫像是跳躍的火苗,微微栗,上一抹溫熱相。
他眼睫微閉,這樣清冷孤寂的人,舌卻是意外的火熱,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握住,或輕或重的廝磨。
郁桃逐漸忘了掙扎,眼角愈來愈紅,不上氣。
難的去推他,得了片刻的息,迷蒙間看見男人的雙眼沉沉,落在自己臉上。
修長的手指輕輕勾扯系帶,不由得睜大眼睛,下一刻,口中的聲音被含住,化作的嗚咽。
一一撥,仰起細長的脖頸,眼角沁出淚珠,雙頰紅。
男人溫熱的氣息撲在耳際,帶著輕笑,“這幾天,沒有白喂。”
那樣修長的手,拿過狼毫,挽過彎弓,卻握不住。滿滿一手白脂,像上好的羊脂玉,細膩,桃心殷紅,經不住撥弄。
恍惚間,手去掐他,卻被一把住,帶著往下,手心猛然到滾燙。
驀地清醒三分。
晨起時花上的珠也不過如此晶瑩剔。
韓祎凝視,將看的雙頰泛紅,眼神躲閃的偏過頭,手遮住臉。
帶著鼻音,不安的手搡他:“......看什麼啊?”
他拉開的細腕,在燎燎燭火下,兩人對視。
糲的指尖過的臉頰,男人啞著嗓:“哭什麼,手都被你弄了,阿桃。”
郁桃短暫的呆愣,他俯,不不慢的低頭含住,或重或輕的咬舐,將人輕而易舉的重新帶沉溺。
郁桃睜著水霧霧的眼,眸間燈火恍惚,男人高大的軀罩著,游刃有余。
燭火被夜風吹得‘噗呲’作響,床帳的帷幔上是繡工致的百子百福圖,鴛鴦錦被,黑發如瀑,纏繞白皙的肩膀。
男人的落在臉上,清冷的神里,厚重又凌的呼吸聲纏繞彼此。
他的指尖蹭著的,“阿桃到底是什麼桃?”
郁桃聽得清清楚楚,難耐間,仰起頭,在下一波夜風來襲前,毫不留的咬上男人的肩。
作者有話說:
已經非常非常正常了,拜托拜托放孩子出來吧。
猜你喜歡
-
完結1277 章

爆笑穿越:王妃是朵白蓮花
戰神燕王說,我家王妃身嬌體弱,善良溫柔,你們都不要欺負她!被她坑的有苦難言的眾人,你說這話,良心不會痛?登基之后的燕王又說,我家皇后的端莊賢惠,朕獨寵六宮,眾妃們做個擺設就好!鎩羽而歸的眾妃們,皇后的手段比她們高百倍,爭個屁呀?終于,四海升平,海晏河清,燕王含情脈脈:“皇后,咱們好像還缺個太子呢!”
278.4萬字8 51071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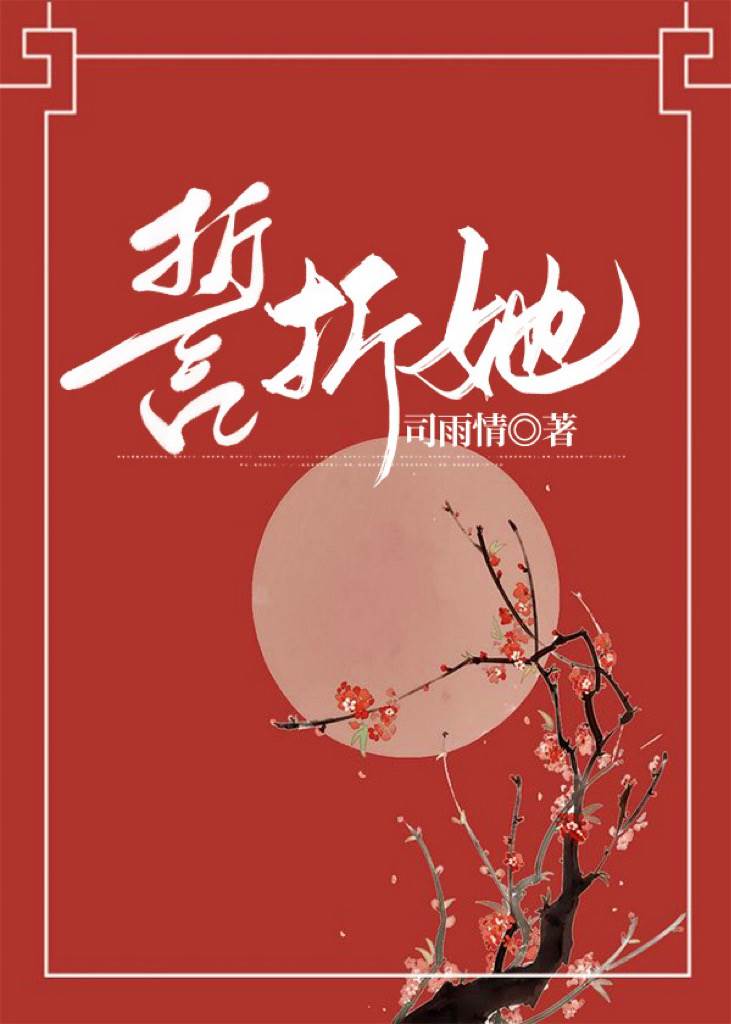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69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