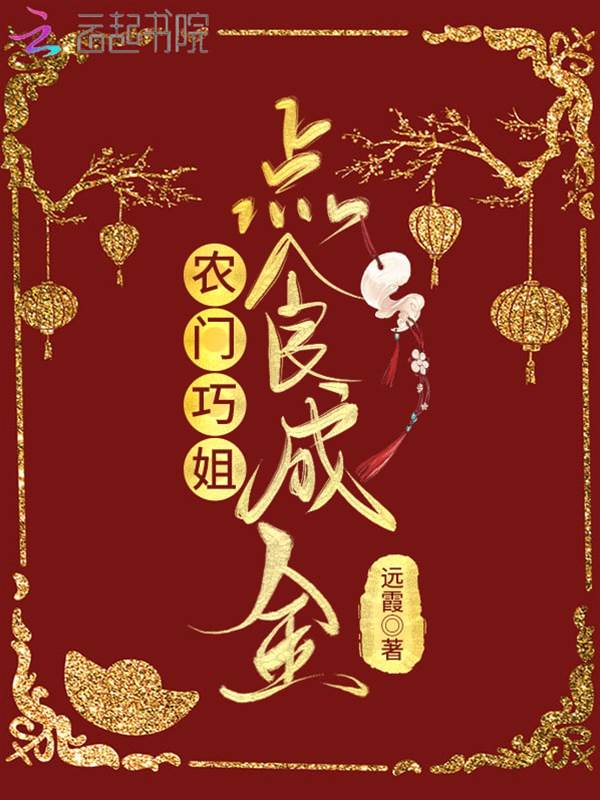《公主真的可以為所欲為》 第28章 27傷口
三皇子一臉令人作嘔的嬉笑, “怎麼,皇妹還不知道?看來,你對那姘頭不過如此。”
三皇子看似輕松, 一雙眼睛卻盯著越長溪, 看一臉漠然, 完全沒有關心的意思,才微微松口氣。
母后就是多心,偏說衛良和公主關系不一般,讓他多加小心。怎麼可能!他就說嘛, 太監算什麼玩意, 哪能讓人快樂。有些事,還得靠他們男人。
滿是污穢的眼睛滴溜溜一轉, 三皇子計上心頭。既然越長溪不喜衛良,聽到那件事,又會是什麼反應呢?
他假裝唏噓道,“倒是可憐衛良, 因皇妹傷, 卻得不到半點垂憐, 唉, 可憐啊。”
什麼!怎麼會……越長溪猛地一驚,衛良調查衛時傷, 為何和有關?
明知道三皇子可能說謊、故意惡心, 卻不控制, 心臟驀地,像被一繩索綁住,勒得不過氣。越長溪拼命按住手掌,掩飾住心中焦躁, 表面不聲,甚至出一分嫌惡,“你在說什麼胡話。”
看見眼底深的厭惡,三皇子咧笑了,哼,他終于抓到小賤.人的弱點,也難怪,聽說一個太監慕自己,哪個人不惡心呢,他都惡心壞了。
越朝暉欣賞夠對方的表,才慢悠悠道,“皇妹還不知道吧,衛良已經擒住許,本不用傷。但許說,死前也能拉公主陪葬、這輩子值了。衛良一時恍神,才中了毒箭。多癡的男人,本王看,皇妹不如從了衛廠公。”
他頓了頓,仿佛突然想起什麼,恍然大悟道,“啊,抱歉,本王忘了,他本不算男人。”
竟是這樣……越長溪怔忪一瞬,下一刻,腔突然升騰出怒火,仿佛一團火焰在心底燃燒。
Advertisement
衛良是傻子麼,如此簡單的謀,任何人都能看穿,他怎麼會沒發現,還任由對方傷到他!他是什麼心狠手辣的殺人機,他分明是個憨憨,還是最傻、最最傻的那種憨憨!真是氣死了!
使勁罵了衛良一頓,越長溪不僅沒舒服,反而更難了,好像有什麼東西堵在口。因為心里始終有個小小的聲音,不停告訴,衛良如此慌,只因為那個人是。
越長溪一直知道,衛良喜歡自己,但他的喜歡過于蔽,像是大霧中的水汽,知道它的存在,卻無法發現。
從沒想過,衛良的喜歡有多深刻,能夠讓他失去理智,讓他不再警惕,那些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因為一點點瓦解。
這就是喜歡麼?僅僅是喜歡……可以達到這種程度麼?
越長溪斂住眼中的復雜,冷漠道,“衛良怎麼想,與本宮何干?”
“本王也是關心皇妹,”三皇子不懷好意地笑,“皇妹在白云寺獨居三年,深山野嶺又都是和尚,想必嘗過不好滋味。如今深宮寂寞,皇妹若是想男人,可以告訴本王,本王不計前嫌,倒是可以幫幫你。”
他下流的眼神掃過越長溪的脯、細腰,最后停在雪白的脖頸。三皇子漫不經心想著,等他登基,也不是不能饒了,當個暖床宮也不錯。
人嘛,在床上收拾幾次,也就老實了。當然,不能讓留下子嗣,還不配。
越長溪差點吐出來。什麼晦氣玩意兒,難怪從前在坤寧宮,偶爾遇見三皇子,他看自己的眼神總是怪怪的,原來打著這樣的主意。
渣渣暉果真牛,每次覺得對方不能更惡劣時,三皇子總能跳出來,再一次刷新的下限。
Advertisement
面對這種人,不,面對畜生,憤怒都是多余的。越長溪緩緩笑道,“若論寂寞,皇后娘娘可比本宮更寂寞,畢竟,父皇已經三年未寵幸過。三皇子若是心有余力,不如幫幫皇后娘娘,沒準能添個弟弟妹妹呢,畢竟都是一家人嘛。”
惡心人,誰不會呢。
三皇子猛地沉下臉,“越長溪,你不要囂張。本王早晚會登基,等到那時,你、還有幫過你的人,什麼鄭元白衛良,一個個都得死!記得當年的貞嬪麼,那就是你們的下場。”
越長溪冷笑,“你登基?還不如讓皇后再生個兒子,三歲娃娃都比你更可能登基。”
“你!”
*
三皇子怒氣沖沖走了,越長溪也面無表走進東華門,兩人錯而過,眼里都是沉沉的怒火。
氣急敗壞的腳步聲逐漸消失,越長溪走進廷,卻沒有回永和宮,沉默等待片刻,覺得時間差不多,三皇子應該離開了,才猛地沖出去,跑向東廠。
該死的慶吉,又騙!衛良究竟怎麼樣了,他……還活著麼?
越長溪飛快跑著,腦中一片空白,只想著快一點,再快一點。
像曠野上的一陣風,急迫地掠過長長的宮道,路上遇見錦衛,他們看見一道的紅影子在黑暗中猛地閃過,都嚇了一跳,第二天甚至傳聞,東廠鬧鬼。
抵達東廠時,慶吉還沒走,他被一群錦衛包圍,正在吩咐什麼。越長溪直接打斷他們,冷著臉把慶吉拽到一邊,“衛良究竟在哪?我知道他傷了,你不要騙我。”
沒發現,張到忘記自稱‘本宮’。
慶吉也沒發現,他苦惱地撓撓頭,臉上一陣心虛,“哎,奴才就說瞞不住您,師父偏不讓,”他示意那些錦衛離開,遲疑問道,“師父還在養傷呢,您要去看看麼?”
Advertisement
越長溪沒回答,實際上,也說不出話。剛才跑得太快,嚨口都不舒服,像是堵著一塊石頭,嗓子涌上一腥甜。沒開口,但堅定的眼睛分明在說,‘帶我去。’
慶吉無奈,左拐右拐,帶著公主來到東廠深,里面有一排小屋子,每個都不大,甚至有些簡陋,只有最里面的房間亮著燈。
慶吉抬起燈,照亮前面的路,指著最深道,“那是師父的房間。”
越長溪皺眉,剛知道,原來衛良住在這里。可他不是東廠督主麼?又喜歡錦華服,怎麼會住在這麼破舊的房間。
越長溪忽然發現,自己似乎不了解衛良,他的人和他的一樣,都藏在霧氣中,不讓別人窺見分毫。
說不出什麼,但著房間里飄忽的燭火,覺自己的心臟也像那盞燭火,忽明忽滅,搖搖墜。
忽然停下腳步。
慶吉自顧自向前走,本沒發現公主沒有跟上,直到他推開房門,剛要說請進,忽然發現后沒人,他一驚,“嗯?”公主呢?人呢!那麼大一個人呢!啊啊啊,他不會遇鬼了吧。
越長溪站在遠,視線一直向狹窄的門口,腳步卻不聽使喚。
該怎麼說,有一種類似近鄉怯的覺,膽怯又恐懼,想要見到衛良,確認他還好;又害怕見到衛良,擔心他不好。
兩種想法在腦海中拉扯,像是沉重的巨石,牽扯無法前進。
終于發現遠的公主,慶吉頓時松口氣,他額頭嚇出來的冷汗,問道,“您不進來麼?”
許久,在慶吉疑的視線里,越長溪終于走進房間。剛邁過門檻,便猝不及防看見衛良。
房間實在太小了,一張桌子和一張床,就是所有裝飾。衛良平躺在床上,眉眼閉,昏暗的燭火在他臉上投出一片影。被子只蓋到小腹,口在外面,布條纏在傷口上,泛著紅。
Advertisement
房間里有一藥味,很濃,像是某種狂風,卷走所有氧氣,令人窒息。越長溪覺陣陣頭暈,甚至不知自己怎麼走進房間,等回過神,已經站在床邊,指尖懸在傷口上,未。
慶吉放下燈,搬來一把椅子,用袖子干凈,“您坐。”
他像是沒看見衛良的傷口,畢竟在東廠,傷是家常便飯,甚至比吃飯還要頻繁,只要命無虞,他們都不太在意。
“不用椅子,本宮坐在床邊就行,”越長溪著床邊坐下,盡力不到對方,俯湊近他的傷口,放輕呼吸,小聲問,“傷的嚴重麼?”
“不嚴重,”慶吉隨口回答,眼睛在房間里搜尋。唉,幸虧公主不怪罪,師父這里空的,本沒辦法招待公主,茶在哪?茶杯又在哪?
衛良從不讓別人進他的房間,慶吉對這里不悉,一邊翻找東西,一邊回道,“太醫已經檢查過,傷口避開關鍵部位,只傷到皮,雖然看著嚇人,但不嚴重,修養半個月就能下床。”
聽到衛良沒事,一直繃的心弦才放松下來,越長溪驟然放松,不張了,失去的理智也慢慢回籠。
捂著額頭無語,啊,真傻,如果真是一箭穿心,衛良怎麼可能活下來,那天怎麼能站在大殿里。三皇子肯定在騙。虧還是穿越來的,高中生都喂狗了。
吐槽幾句,又深吸一口氣,越長溪覺自己清醒很多,輕輕掖被角,“他現在怎麼樣?睡著了?”
慶吉終于翻出茶葉,眼前一亮,回道,“是昏迷。袖箭有毒,太醫雖然開了藥,但余毒未清,師父大部分時間都在昏睡,偶爾才會清醒。不過,昏迷也好,醒的時候才疼呢。”
慶吉看著師父,眼里甚至有些羨慕,怎麼傷的不是他呢,他也想躺著嗚嗚嗚。
“原來如此,”越長溪點頭,目掃過衛良蒼白的臉,眼神一頓,“他臉上怎麼有跡?”不麼?
提到這點,慶吉也很無奈,“奴才沒辦法,”他走到床邊,試探地出手。手掌剛剛靠近衛良,還沒到對方,只見衛良忽然掙扎,他似乎想避開,又因為昏迷無法作,全都在繃,傷口也溢出跡。
慶吉連忙收回手,無奈表示,“每次靠近師父,他都這幅反應。奴才擔心牽傷口,不敢給他。”師父不喜歡接別人的病太嚴重,清醒時還能控制,昏迷時本毫無辦法。
他發誓,他真是個孝順徒弟,并非故意不干活。
想起衛良的強迫癥,越長溪了然,可過了一會,又忍不住想,剛才靠近衛良時……他似乎并不抵。
越長溪糾結地手指,心里激烈斗爭,半晌后嘆口氣,“你去打一盆溫水來。”就當做好人好事,雷鋒叔叔都說,生命是有限的,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
“您要凈手?”慶吉沒多想,應一聲“好”,匆匆跑去打水。
片刻后,慶吉端來熱水和手帕,他端著盆,等待公主凈手。然而,公主沒有洗手,而是認真沾手帕,又在手背上試試溫度,才遲疑地、試探地向衛良。
“欸?!”慶吉剛想阻止,但越長溪作更快,的指尖馬上要到衛良的臉頰,最令慶吉驚訝的是,師父本沒反應,沒有!一點!反應!
慶吉:?還有區別對待?
越長溪也有點張,手指不穩,好在試探過后,衛良的確不抵的靠近。輕輕呼口氣,小心向前手,錦帕上衛良的臉頰,輕輕掉跡。
溫熱的手帕到皮的一瞬,衛良突然繃,他似乎想要作,越長溪不知怎麼想的,命令道,“衛良,不許。”
發誓,只是隨口一說,但沒想,竟然有效果。
慶吉也驚訝地發現,師父真的沒。不僅沒,還仿佛到安,瞬間放松下來。
慶吉:?他已經開始懷疑,師父真的昏迷了麼?不會是裝的吧?
作者有話要說:突然出現的二更
猜你喜歡
-
完結502 章

重生悍婦
前世,她是名門淑女,嫁入侯府十餘載,雖無所出,卻賢良淑德,亦是婦德典範。奈何早逝,原以為會風光大葬,卻落得個草席裹屍,暴屍荒野,屍骨無存的下場。一朝慘死,得知真相,她才明白,這一切,不過是他們的蓄謀已久,而她不過是為他人做嫁衣。重生一世,她誓不做賢良婦,即使背上悍婦之名又如何?小劇場:某日,茶館內。「聽說了嗎?王爺又被攆出府了,而且還鼻青臉腫的。」「聽說又是王妃打的。」「又?」「王妃是出了名的悍婦,偏偏王爺又是個懼內的。」「聽說這次被揍,是因為王爺被個打更的看了一眼。」「……」
203.1萬字8 58521 -
完結4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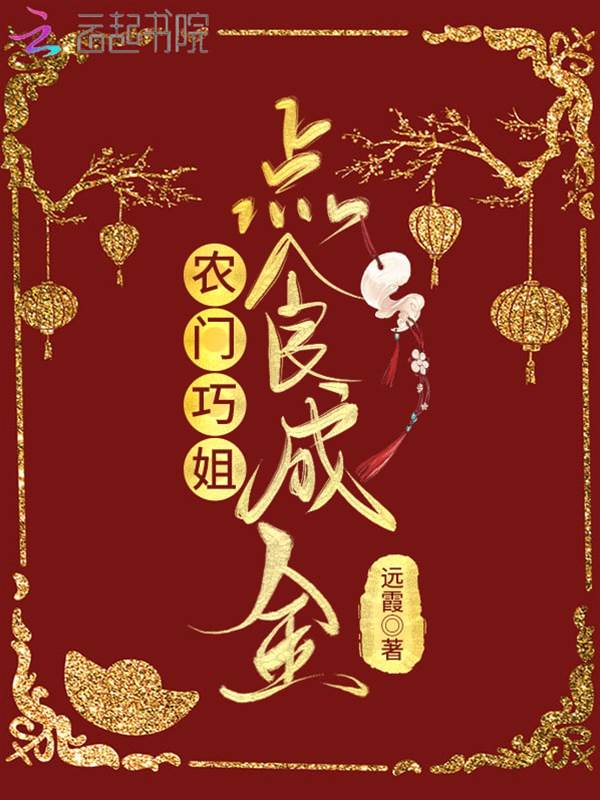
農門巧姐點食成金
高級點心師意外穿成13歲彪悍小農女-包蓉。後奶惡毒,親爺成了後爺。,爹娘軟弱可欺,弟弟幼小,包蓉擼起袖子,極品欺上門,一個字:虐!家裏窮,一個字:幹!爹娘軟弱慢慢調教,終有一天會變肉餡大包,弟弟聰明,那就好好讀書考科舉,以後給姐當靠山,至於經常帶著禮物上門的貴公子,嗯,這條粗大腿當然得抱緊了,她想要把事業做強做大,沒有靠山可不行,沒有銀子,她有做點心的手藝,無論是粗糧、雜糧、還是精糧,隻要經過她的手,那就都是寶。從此,包蓉銀子、鋪子全都有,外加一個自己送上門的親王夫君,氣得後奶一概極品直跳腳,卻拿她無可奈何。
77.6萬字8 37904 -
完結983 章
侯門悍媳
前世顧明秀嫁進靖國公侯府,被庶妹害得夫死子亡含恨而逝,重生回到五年前,懲惡妹,打姨母,救兄長,不屈命運安排,嫁就要嫁自己看中的。 他是長公主之子,英國公世子,生來高貴,卻病體纏身。 人人都說他娶她是拿她當藥引子,他也以為,她就是自己的葯,殊不知,相處相知中,愛意早已浸入骨髓。 「世子,世子妃打了金姨娘,侯爺要將她關進虎籠」 「兩瓶鶴頂紅,夠不夠毒死籠里的所有老虎?」 「世子,世子妃打了愉貴妃的弟媳,愉貴妃要送她去掖庭」 去愉貴妃娘家放火,用火油」 他將她寵得無法無天,她以為,她的感情在前世就耗盡,沒有了再愛能力,很幸運遇上了他,這一世願用生命去愛的男人。
166.5萬字8 627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