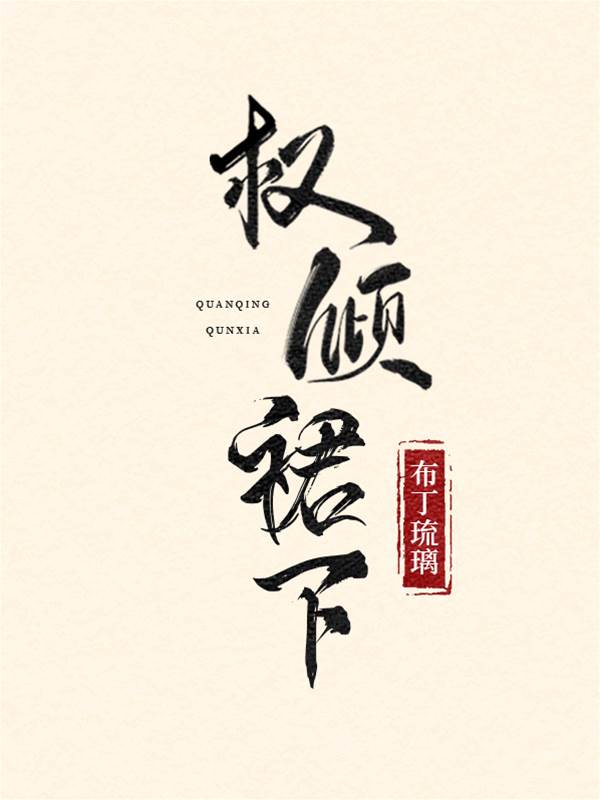《驚!真千金上了變形記[古穿今]》 第75章 第 75 章
孟氏的公關部,發水軍和鈔能力,買了許多營銷號,將臟水全都潑給了謝聚萍。
弄得好像孟同恕和孟嘉憫清清白白白蓮花。
世界上唯一的爛人,就是謝聚萍。
他們這樣做,其實許柚能明白。
畢竟謝聚萍和孟同恕的能量相比起來,明顯來說,獻祭掉謝聚萍,風險和損失是最小的。
區區一個話劇院的的演員,就算在文藝界再有地位,再怎麼被譽為“音樂家”,跟孟家這樣的大資本也是不可相提并論的。
更何況本謝聚萍的名聲就已經很差了,再差一點也沒什麼。
畢竟,臟水一瓢也是潑,兩瓢也是澆,沒有什麼區別。
古人的智慧,還是要多多學習的。
為了保住孟家,犧牲掉謝聚萍的事業、名聲,都不算什麼。
孟同恕和孟嘉憫都是這麼想的。
兩人冷酷無地分析著,都覺得這是最好的路子。
孟同恕甚至說:“只要你媽媽還是孟氏的夫人,就永遠不會被人欺負。可如果我們沒有了孟家,就會一落千丈。”
孟嘉憫贊同點頭。
于是父子二人一拍即合,定下了接下來的營銷方案。
許柚能夠明白他們的想法。
卻不理解,更不認同。
聽完他們說的話之后,只是不屑的冷笑了一聲,拎著自己的書包,,禮貌道:“我上樓睡覺了。”
兩人同時一頓,沒有說話。
許柚心里格外不屑,格外冷漠。
看著孟家這兩個人冷酷無算計自己的母親和妻子的模樣,只想犯惡心。
雖然是世界上最厭惡謝聚萍的人,恨不得謝聚萍就此消失。
但如今看著這個場景,總讓人覺得難。
大約是因為只有算計,沒有任何的吧。
許柚對孟同恕和孟嘉憫的厭惡不一分一毫。
Advertisement
這兩個人現在算計謝聚萍的模樣,總讓想起前世,他們算計時的模樣,是不是也是這麼無?
孟同恕是不是也說了同樣的話。
比如說“許柚是孟家的兒,就不會被人欺負。”
所以就算被全網暴力,就算是死了,也死不足惜。
誰讓不能給孟氏帶來利益,帶來價值。
前世與今生,又有什麼區別呢?只不過是換了個人罷了。
他們就是冷的,是豬狗不如畜生,心里從來沒有任何。
親生的兒可以算計,親生的母親同樣如此。
許柚甚至覺得,假設有一天。孟家沒有食,只剩下他們幾個人。
等到最后,孟同恕和孟嘉憫這樣的人,說不定能夠干出殺了們吃的行為。
他們一直都是這樣自私且冷酷。
許柚很清楚地認識到,這對父子的話,一個字都不能相信。
可謝聚萍卻沒有這樣清晰的認知。
在的想法里,自己是孟家的主人,是孟同恕的妻子,孟嘉憫的母親。
在孟家天然就有著超然的地位,這對父子保護,寵,是應該的。
他們可以對外人冷酷無,可以對孟熙寧、許柚冷酷無,那都是很正常的事。
他們對外做什麼都是可以的。
但如果他們拿出去擋槍,對不好,才是不對的,是不仁不義的。
簡直不可思議,罄竹難書。
畢竟,世界上不該有人辜負自己的妻子,不該有人對母親不孝順。
所以當看到這條熱搜的時候,整個人都呆住了。
愣了半天之后,從房間里跑出來,快速的跑到書房,推開了孟同恕的房門。
張口就是質問:“你為什麼要買這樣的熱搜?”
孟同恕正在看文件,聞言抬頭,為難地嘆口氣,道貌岸然解釋道:“聚萍,我也不想這樣。但這都是為了孟氏,我別無他法。”
Advertisement
謝聚萍然大怒道:“為了孟氏,孟氏是要倒閉了嗎?再為了孟氏你也不能這麼做!大家現在都在罵我,你可以買和許柚和好的熱搜,為什麼還要踩我一腳?”
“你什麼意思,你是不是在外頭有小妖了?嫌棄我了,恨不得弄死我?”
孟同恕便有些不耐煩,反問道,“我沒有踩你。難道這些事不是你自己做的嗎?”
“我能怎麼辦,難道要告訴大家,你沒有趕走許柚嗎?這話你自己信嗎?”
謝聚萍啞了,卻反問道,“這件事先不提,可是留下熙寧是我們共同的決定,為什麼現在了我一個人的錯?”
“他們現在都在罵我,你怎麼能夠做出這樣的事?”
“我們兩個人的行為,卻把我一個人推出去,你還是個男人嗎?”
“我算是看你了。”
的語氣失又難過,像極了一個天真無邪的人,突然遭了風雨的吹打。
于是溫室里的花,再也承不住,只能惱怒的著帶給自己風雨的人。
孟同恕似乎覺得,無理取鬧,皺了皺眉頭,不悅道:“那你覺得我能怎麼辦?”
他抬眼著謝聚萍,心底也非常惱火:“若非你一時沖,趕走了許柚,引起這麼大的輿論危機,我也不用到這個時間還在加班解決問題。”
“你說我不能這樣做,現在你讓我怎麼辦?你給我一個方案?”
“難道說是我的決策,是我趕走許柚,讓消費者對我不滿,從而連累整個孟氏嗎?”
謝聚萍語塞,頓時沒了原先的氣焰。
只顧著來回顛倒地說,“那你也不能拿我出去擋槍,我是你妻子,你應該保護我……”
孟同恕不耐煩道:“那我還能怎麼辦?除了你我,就只有嘉憫有能力做出這樣的事,難道要將嘉憫送出去嗎?”
Advertisement
若說謝聚萍真正的心肝寶貝,那當然還是孟嘉憫。
平日里再怎麼寵孟熙寧,再怎麼為了孟熙寧跟孟嘉憫吵架。
但在心深,還是沒有人能夠比得上孟嘉憫的地位。
哪怕是孟同恕,也不能相提并論。
謝聚萍聞言,當即道:“那當然不行,這件事跟嘉憫毫無關系!”
孟同恕道:“那你還說什麼?沒有辦法的話,就閉上,不要質疑我的決策。”
“我可以告訴你,這就是最好的辦法,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方案能夠將孟氏從風波中救出來。”
謝聚萍總覺得這樣不對,但又不知道正確的做法應該是什麼。
屢次張又閉上,待在那里,不知道該怎麼為自己辯解。
孟同恕見狀,忽然變了臉,略微溫和了些。
他嘆口氣,出苦惱之,道:“你不用擔心網上的輿論,只是一時的事罷了。過了這一段時間,等風波消下去了,不會對你有任何影響。”
謝聚萍半信半疑,總覺得沒有那麼簡單。
如果風波消退,就沒有什麼影響的話,為什麼孟氏不等著風波消退,而要及時轉移視線呢?
然后就在想要質疑的時候,孟同恕又拋出了香甜的餌。
“你不是想要做話劇院的副院長嗎?等到下一任副院長退休,我就讓他們任命你做副院長,好不好?”
“還有半年,你就可以蔣文悅一頭了。”
謝聚萍頓時覺得,如果只是挨幾句罵,就能讓說孟同恕出馬,給自己要個副院長,好像也值得。
猶豫了一下:“那你之前怎麼不……”
孟同恕直接道:“之前是我想著,你的能力可以,才沒有人找人。”
“但是我現在覺得,還是雙保險比較好,你說對不對?”
Advertisement
謝聚萍點了點頭。
孟同恕又道:“但是聚萍你也要知道,只有孟氏好好的,你才有機會做副院長。否則沒了孟氏,就你們劇院那一堆拜高踩低的貨,肯定會欺負你的,對不對?”
這是實打實的話。
謝聚萍對此深有。
別說是孟氏倒閉,徹底沒了。
就算只是上一次,聚萍珠寶破產,手下沒了產業,劇院那些道貌岸然的貨,就已經給了很多臉看。
謝聚萍對此,仍是心有余悸。
再也不想一次。
于是點了點頭,強調道:“你要記住今天的話,給我要一個副院長的職位。”
孟同壽便笑了笑,語氣溫和:“放心吧。好了,我還有一點工作,你先回去休息吧。”
他看了看一旁的鐘表,做出關心的姿態:“很晚了,再不休息,明天臉上該痘了。”
謝聚萍跟著看向時間,連忙點了點頭。
是到睡覺的時間了,若是弄了生鐘,又要不舒服。
只是,往樓上走的時候,心里還是有一疑,總覺得怪怪的。
可是卻始終抓不住關鍵。
只能拋之腦后。
罷了,和孟同恕是夫妻,是嘉憫是母子。
他們總不會害的。
謝聚萍上樓的時候,正好見孟嘉憫從房間里出來。
他穿戴整齊,西裝革履,明擺著是要出門。
看見,孟嘉憫不咸不淡的喊了一聲媽。
謝聚萍腳步一頓,“這麼晚了,你要去哪里?”
孟嘉憫道:“有個朋友讓我出去一趟。”
謝聚萍皺眉,不大樂意,卻沒有說什麼,只是道:“太晚了,注意安全。”
孟嘉憫看了母親一眼,沉默片刻,沒有說話。
他其實有一點想法,突然想問一問,謝聚萍對他們的作為是什麼想法?
會不會因為他們兩個斷送了的事業而有怨言。
是的,斷送。
謝聚萍可能不大明白。
但孟同恕和孟嘉憫看的清清楚楚,對于謝聚萍這樣的文藝工作者而言,一旦名聲盡毀,就等于徹底斬斷了事業。
以后或許能夠因為孟氏的權勢地位,繼續待在劇院里。
但是不會再有觀眾喜歡。
也不會再有人想要看的音樂會。
對于一個依靠觀眾為生的音樂家來說,便再也沒有前途。
孟嘉憫不知道孟同恕是怎麼跟謝聚萍說的,能夠說服謝聚萍,興高采烈從書房中出來。
想要問一問,但是他了一眼孟同恕的房門,想起孟同恕剛才的話,是忍住了。
爸爸說的對,媽媽的事業不值一提,跟孟氏相比,犧牲了也便犧牲了。
大不了,他們給開一個私人的劇院。
隨便找些觀眾,足夠發揮夢想了。
沒有孟氏,又談何夢想。
婦人之仁,要不得。
作為孟氏的掌舵人,生下來之后學的第一件事,就是鐵石心腸。
于是孟嘉憫點了點頭,優雅又平和的走出大門。
看他的神,沒有一一毫的異常。
謝聚萍回頭看了眼,喊住他:“明天早上想吃什麼,我跟管家說。”
孟嘉憫腳步一頓,輕聲道:“不用做我的飯,我不回來了。”
他突然間,加快了腳步。
但網上的輿論卻不像他們設想的,過兩天就消失了,能夠及時控制住。
而是愈演愈烈,如同火上加油,一即發,不可控制。
尤其是在孟氏水軍和競爭對手們的踩踏下,關于謝聚萍的辱罵和黑料,一時之間,真真假假滿天齊飛。
讓人難以分辨。
有人說,謝聚萍在嫁給孟同恕之前,曾經傍過富商,又將那富商甩了,傍上孟同恕。
也有人說,謝聚萍當年為了套住孟同恕這位富家公子,未婚先孕。但懷的是別人的孩子,是賴在謝聚萍頭上,所以在婚后自己流掉了,過了好幾年才生下孟嘉憫
還有人說,謝聚萍當年上大學是沒有考上,頂替了別人的名額。
更有甚者,還有人說謝聚萍在劇院里霸凌別人,一點都不好相與,尤其欺負新來的年輕小孩,將雌競貫徹到了骨子里。
還有人說謝聚萍在劇院里最結各種各樣的小男孩,調戲人家,吃人家的豆腐,反正是一個不太好的人。
那些人,紛紛給自己冠上謝聚萍“同學”“同時”“朋友”“校友”的名頭。
信誓旦旦,好像說的都是真的。
經過這些謠言互聯網,將謝聚萍塑造了一個作風不良,、不齒,人品卑劣低下,違法犯罪,無惡不作的人。
各種各樣的謠言滿天飛,讓謝聚萍措手不及。
謝聚萍沒有生活在真空里。
天天上網,天天觀察輿論走向。
忍不住在家里大發雷霆,“我什麼時候傍富商了,我家里還不夠有錢嗎?我嫁給孟家是門當戶對,為什麼他們要這麼說?”
孟同恕只是敷衍著安:“他們不懂我們之間的事,你別傷心,我了解你就夠了,我不會誤會你。”
孟同恕心想,謝聚萍的家世不差,跟他的時候,還是。
這一點,孟同恕很清楚。
所以倒也不至于聽信那些七八糟的謠言。
謝聚萍卻越來越難過,“你如果還拿我當你妻子,就幫我解決這些謠言,我不了,他們怎麼能這麼說我!”
“我、我沒有未婚先孕,更沒有懷別人的孩子。我不是那樣的人!”
氣到語無倫次,瞪著孟同恕:“你去幫我!發律師函,告他們。”
孟同恕當然知道,不是那樣的人。
但是此時此刻,他也不會主出頭說什麼。
好不容易將戰火從孟氏集團燒到了謝聚萍上,如果替謝聚萍辟謠,用孟氏的名聲給擔保,那戰火重新燒回孟氏上,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就白毀了。
孟同恕不會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
他嘆了口氣,避重就輕道:“我們是夫妻,我肯定會幫你的,我們公司里的幾千水軍現在都在網上幫你刪帖子、回帖子,你放心,很快熱度就會降下去,不會再有人罵你的。”
謝聚萍道:“我要你幫我起訴那些造謠的人。”
孟同恕表示為難:“一旦用孟家的名義起訴他們,那孟氏就會重回戰場,這……”
謝聚萍心底不可抑止地泛起失和怨恨。
茫然無措坐在那里,不知道事為什麼會變這樣。
猜你喜歡
-
完結4011 章

清宮熹妃傳
她為保家人周全狠心拋棄青梅竹馬的戀人入宮選秀,盼能一朝選在君王側,結果卻陰差陽錯成了四阿哥胤禛身邊的一名格格,從此卑微、榮耀、歡喜、絕望都繫於胤禛之身。康熙四十三年至雍正元年,她陪了他整整十九年最終踏上至高無上的寶座,然,換來的卻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殺局。當繁花落盡,他與她還剩下什麼?
718.4萬字8 12498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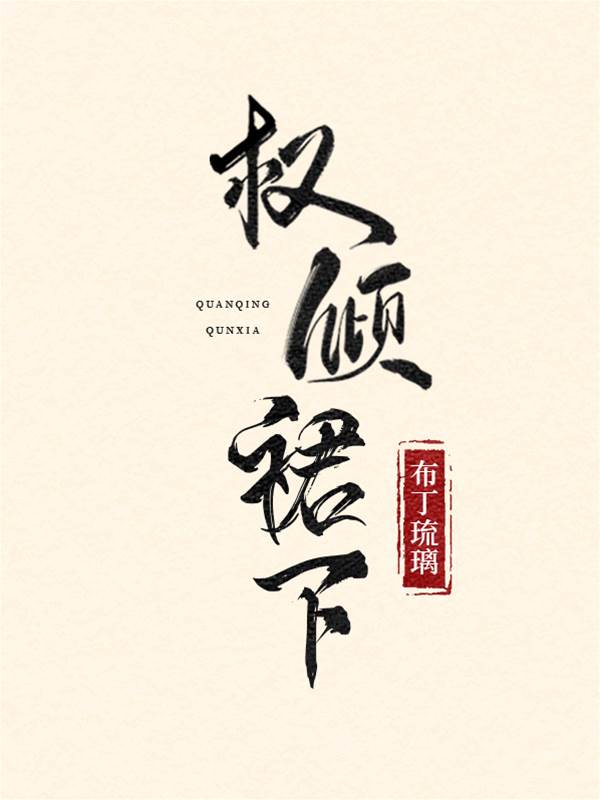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193 -
完結719 章

冒牌皇后醫天下
《冒牌皇后醫天下》有高人觀天象,蘇家應天運出天女,得之可掌控皇權穩固天下,千光國二十一年,蘇女入宮為後,帝后恩愛國之將興。 然而事實上……她是魂穿異世的巧手神醫,別人都是做丫鬟,做千金,做妃子,她倒好,直接做皇后,只是冒牌皇后不好當,各種麻煩接踵而來,所幸銀針在手天下我有,哎哎,狗皇帝你放開我! 他是手握天下的一國之帝,自古皇位不好做,危機四伏屢陷險境他理解,可為什麼自家皇后也上躥下跳的搞麼蛾子,說好的國之將興呢,說好的穩固天下呢?高人:忘了告訴您,蘇家有兩女,二姑娘才是天女! 皇上和皇后相視一笑:早就知道了。
192.5萬字8 8535 -
完結686 章
深宮美人,朕的貴妃膽小又怕事
作為小官庶女,她從小被嫡母苛待和為難,父親對她不管不理,一心只想用她來討好上官,為此來謀取升官的機會。 既然都是要做妾,那她為何不做世界上最尊貴的人的妾? 她步步算計,獲得了進宮參加大選的資格,成為了深宮中一個小小的七品美人。多年以后,她成為了冠寵后宮的貴妃,一眾深宮老人和新人都咬碎了牙,暗戳戳在皇帝面前爭寵。 皇帝只表示道“貴妃膽小又怕事,需要朕的陪伴。”
120.7萬字8.18 19971 -
連載473 章

夫人今天還在裝瞎嗎
強制+追妻火葬場+不原諒+后期瘋批女主卓明月撞見宴清風殺了人,之后每一天都在崩潰。準備就寢時他在,去沐浴他在,去茅廁他也在。可她是個“瞎子”啊!她只能若無其事的寬衣,沐浴,小解。直到宴清風扔了條幾近透明的紗衣給她穿,她實在忍無可忍。……在宴清風眼里,卓明月這樣的女子卑微低賤,空有一副好皮囊,生來便是個食髓知味的玩物。后來,她離開宴清風,成了惑亂圣心的寵妃。他抓肝撓肺,夜不能寐,方知他丟的不是玩物,是肋骨。終于他攔了她的去路,低聲下氣的問她“你喜歡什麼,只要天上地下,這世間有的,我都給你弄來。”卓明月說“想做太后。”她要她的孩子登基,要站到萬人之上的高臺上,要宴清風也成為匍匐在她腳下的臣民之一。
85.2萬字8.18 26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