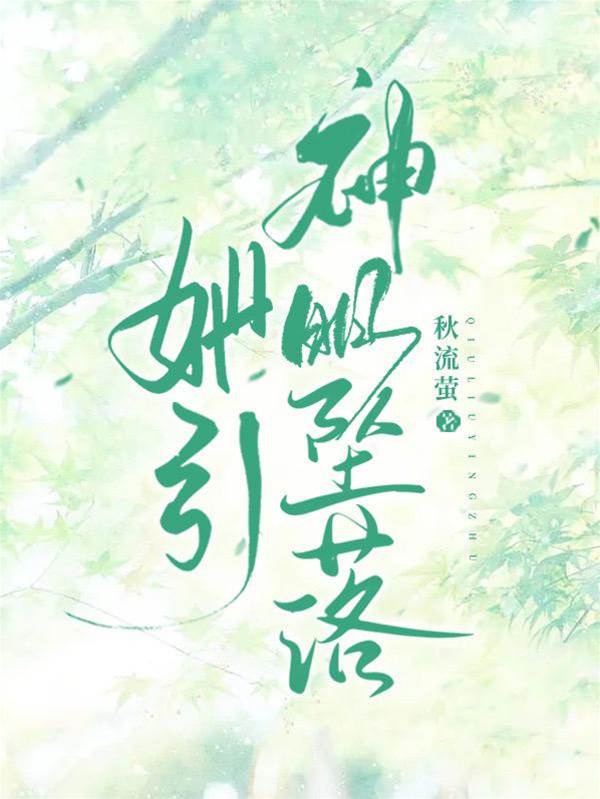《別逼我心動》 第63章 番外一
在國外進修的這兩年,許今今是在各種演出訓練中度過的,在一場場演出中,不但找回了丟失的信心,還實現了自己曾經的理想。
終于,做為主角代表自己國家站在芭蕾舞最頂尖的劇院里表演,臺下是一波接一波如雷鳴般的掌聲。
站在舞臺中央百集,著舞臺下無數觀眾,視線搜尋著一個影。
國臨近新年,陸晏回國去理事務,忙,他也忙。
怕他太辛苦,提前就告訴他,如果時間來不及不用專門過來看的表演。
但真的到了這一刻,心里卻無比期盼著能在臺下看到他。
視線聚焦在前排的位置,只要有的演出,他都會在前排,可當視線從前排座位一一掃過,直到這排的末尾,也沒看到悉的影。
許今今垂垂了眼,面前的幕布漸漸落下。
演出結束后,在后臺和同事們慶祝了一番后先一步離開。
當離開人群,臉上的笑意漸漸去,神有些落寞走出劇院大門。
這里剛剛進深秋,早晚的溫差大,一到室外冷風就撲面而來。
戲院的觀眾已經走的差不多了,劇院外的街上只有零星經過的人,四一片深秋的蕭索之。
許今今眨了眨眼,前眼前,還在期盼著下一秒,想要見的人就能出現。
但著眼前經過陌生影,輕輕嘆了聲氣小聲嘀咕著,“我怎麼會這麼想他呢?男人最煩了。”
裹了裹上的外套準備邁下臺階。
“那究竟是煩我還是想我呢?”
低沉的聲線突然從背后傳來,許今今不敢相信的耳朵,以為自己幻聽了。
秋風將地上的枯葉吹在空中打著旋兒,明明風還是那麼涼,許今今卻不知道為什麼覺口有些熱熱的。
Advertisement
還沒等轉,就突然被人從背后摟進了懷里。
男人帶著寒意的氣息將許今今包圍,然后他輕輕著的發頂。
“對不起,我來晚了,就在后排看著你。”
許今今從他懷里轉,當看到他臉上冒出的青胡茬時,抬手在他臉上了,“你怎麼連胡子都沒刮?”
頓了下慢悠悠道:“是著急來見我嗎?”
陸晏一瞬不瞬地看著,“嗯,是急,急的夜不能寐,寢食難安。”
聞言,許今今眼睛彎月芽,手臂勾住他脖頸剛剛要踮起腳,就覺后腦被人扶了下,兩人間的距離消失。
一個多月的思念都融化在這個吻里。
許今今覺后腦上扣的手越來越重,當呼吸要被奪去時,用手推下陸晏膛。
陸晏手松了松,在角吻了吻才抬起頭。
“還在……劇院呢,你就這樣,就這麼忍不住嗎?”
許今今在周圍看了看,沒發現同事后才瞪他一眼。
帶著息的呼吸聲落陸晏耳中,他低頭抵住額頭,“太想你了,忍不住。”
低沉的聲線里不帶任何掩飾,許今今心里像是被裹進被曬過的棉被里,溫暖。
拉住他的手,“那我們回家。”頓了下湊到他耳邊:“回家讓你親個夠。”
這句話落下,看到男人的目倏然變的幽暗,還沒等反應,突然一陣天旋地轉,被他攔腰抱起來。
“好好的,你抱我做什麼?”
“回家。”
“回家,所以呢?”
“你走的太慢。”
“……”
—
后半夜,許今今用手了發麻的,往側看了一眼,借著室唯一的源,墻上的一盞小壁燈著已經睡的男人。
Advertisement
他睡著的時候,眉眼完全舒展開,弱化了五過于立給人的凌厲,甚至帶了一孩子氣。
視線下移,當看到他抱著的手臂微微蜷著的時,表頓住。
他睡的時候總是這種睡姿,記得以前看過的一本心理學方面的書,這種睡姿是一種自我保護的姿態,這樣的姿勢一般是發生在兒期,如果年后還以這呈這種姿勢,說明心極度缺乏安全。
聯想到他經歷過的一切,許今今心臟位置一陣陣刺痛著,手輕輕在他臉上了。
指尖剛剛到,人就突然朝抱過來。
“今今,別怕我……”
囈語似的聲音說完,陸晏眼睛都沒掀開,可聽到的人卻因這幾個字模糊了視線。
這麼久了,他總是在半夢半醒間說著一樣的話。
許今今垂了垂眼,忍住眼睛的酸,出手臂將人抱在懷里,然后低頭在他額上親了親,“我不怕你……”
短暫地停頓了幾秒后湊在他耳邊輕輕道:“我喜歡你。”
“我不信。”
低沉的嗓音比之間清晰了些,許今今以為他還在說夢話,在他耳上然后用更輕的聲音說,“喜歡的程度太輕了……”
“是我你。”
這句話說完,覺懷里的人突然繃,還沒等反應過來,就被人捧住臉,
“我是不是在做夢?你再說一遍。”
這場景這對話,許今今這兩年不知道經歷過多次,像每一次一樣低頭趴到他肩膀上張開輕輕一咬。
“我你。”
肩膀的輕微刺痛讓陸晏有了真實,他眼底浮著笑將人摟進懷里。
“還想再聽。”
窗外不知道什麼時候起了風,風聲吹打在窗戶上發出“嗚嗚”的聲音,連窗外的梧桐樹都風被吹的搖搖晃晃,聲音里著一寒意,可一窗之隔的室卻是一派溫馨安寧。
Advertisement
許今今臉在他懷里,耳邊是有節奏的心跳聲,手輕輕拍著他的背角彎了彎,“我你。”
“還要再聽。”
“我你。”
“再說一遍。”
“我你。”
“聲音太小了,這次沒聽清。”
“喂,還有沒有完啊。”
許今今在他膛上錘了一下,只是還未來得及收起手,手就被摁住,而急促的吻朝脖頸落下來,像每一次一樣,做出最本能的反應,像電流涌過后栗著。
安靜的室,呼吸聲開始變的重。
當吻從鎖骨下時,許今今著氣用雙手去推他,“都后半夜了,你還讓不讓我上班了?還有完沒完了?”
陸晏聞言做一頓抬起頭,手了緋紅的臉一本正經道:“如果不是因為你要上班,就沒完。”
許今今一言難盡地看著他,“你也十了,節制點吧,小心以后不……”
“行”字還沒說出口,就被人堵上。
沒有一秒停頓,的齒被人無地撬開。
幾分鐘后,連腦仁都開始發麻,幾乎任由著他對自己掠奪。
實在招架不住,幾乎是“嚶嚀”地發出聲音:“你行,我老公最行了,求放過。”
百試百靈的話,下一秒就被人松開,然后頭頂傳來低低的笑聲,“見風使舵的功夫倒是見長了。”
許今今抿了下更加發麻的,撇了撇,“我那是識時務者為俊杰。”
陸晏聽到眼底的笑意更盛,他將被子往上拉了拉給許今今上包的嚴嚴實實又用手臂抱,“睡吧。”
許今今一向怕冷,在這個伴著大風的秋夜,放在平時抱著暖水袋都不一定會暖和,可現在溫熱的溫將包裹住,上哪里還有一丁點的寒意。
Advertisement
在他懷里找了個舒服的姿勢躺好閉上眼睛。
在快睡著的時候,突然想到一件事,就含糊地問了句:“你是什麼時候認出我的?”
陸晏著慢慢垂下的眼睛,他沒回話,只輕輕回了句:“睡吧,以后告訴你。”
他話音落下的瞬間,的眼睛也完全閉上。
陸晏著懷里的人許久,他手指捧著臉,拇指輕輕挲著。
“我被蛇咬的那天,手上很疼,腦子已經開始昏昏沉沉的,我以為自己要死了,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就認出了你,我就就告訴自己,一定要活下來,只是,我沒想到你會那麼怕我。”
他垂了垂眼遮住眼底的晦,聲音低下來,“幸好,你現在不怕我了。”
低沉的嗓音里帶著一意,已經睡著的許今今在睡夢中捕捉到了這個聲音,了囈語著:“不怕你,我你……”
盡管聲音很小很小陸晏還是聽到了,他眼上揚著笑意從里面溢出來,他低頭在角上輕輕吻了吻。
“我也你。”
猜你喜歡
-
完結3328 章

先婚後愛:BOSS輕點寵
她以為離婚成功,收拾包袱瀟灑拜拜,誰知轉眼他就來敲門。第一次,他一臉淡定:“老婆,寶寶餓了!”第二次,他死皮賴臉:“老婆,我也餓了!”第三次,他直接撲倒:“老婆,好冷,來動一動!”前夫的奪情索愛,她無力反抗,步步驚情。“我們已經離婚了!”她終於忍無可忍。他決然的把小包子塞過來:“喏,一個不夠,再添兩個拖油瓶!”
591.3萬字8.46 320926 -
完結3045 章

天價萌妻:厲少的33日戀人
他是歐洲金融市場龍頭厲家三少爺厲爵風,而她隻是一個落魄千金,跑跑新聞的小狗仔顧小艾。他們本不該有交集,所以她包袱款款走得瀟灑。惡魔總裁大怒,“女人,想逃?先把我的心留下!”這是一場征服與反征服的遊戲,誰先動情誰輸,她輸不起,唯一能守住的隻有自己的心。
236.6萬字8 23019 -
連載1815 章

枕上歡:老公請輕點
唐慕橙在結婚前夜迎來了破產、劈腿的大“驚喜”。正走投無路時,男人從天而降,她成了他的契約妻。唐慕橙以為這不過是一場無聊遊戲,卻冇想到,婚後男人每天變著花樣的攻占著她的心,讓她沉淪在他的溫柔中無法自拔……
318.3萬字8 35129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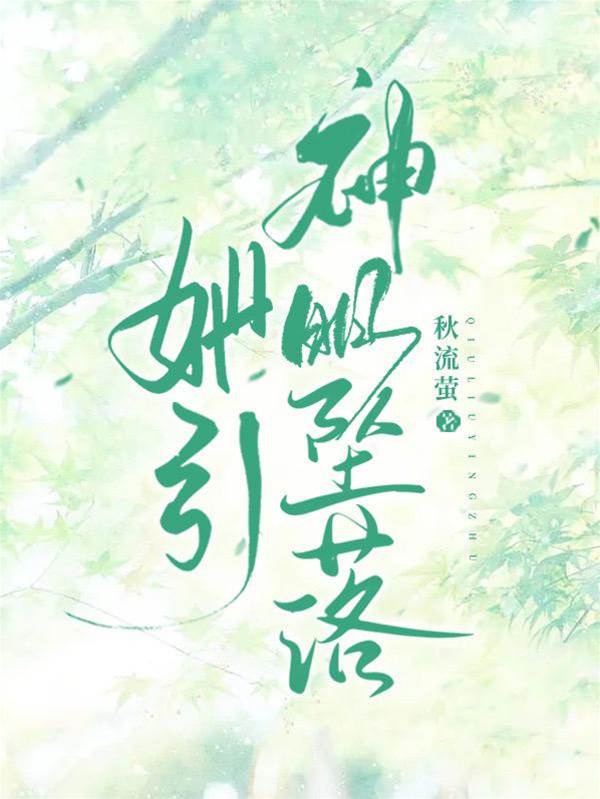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191 章

你有男閨蜜,就不要纏著我了
結婚前夕。女友:“我閨蜜結婚時住的酒店多高檔,吃的婚宴多貴,你再看看你,因為七八萬跟我討價還價,你還是個男人嗎?!”“雖然是你出的錢,但婚房是我們倆的,我爸媽可
33.3萬字8.18 28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