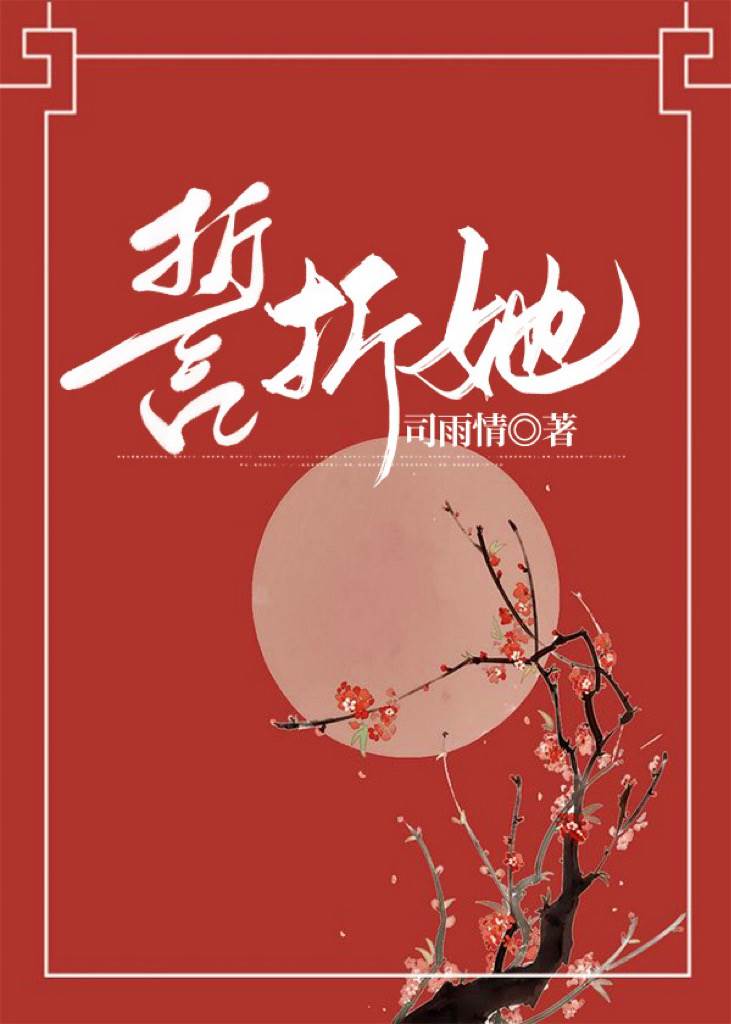《江月窈窕》 第53章 053
第五十三章
江厭辭皺眉, 問:“扶腰做什麼?拾什麼?”
“你竟也不知道……”月皊喃喃著。將臉偏到一旁,眼角著枕巾,眼淚一顆一顆緩緩洇了枕巾。
無聲地哭了一會兒, 聲音輕輕地呢喃:“我要好好想一想……”
江厭辭不清楚要想什麼,卻仍說:“慢慢想。”
他垂眼著月皊, 指腹抹去面頰上的淚痕, 思索著華公主上午帶出去見了什麼。
“冷。”月皊忽然聲說。
江厭辭探,扯過一旁的被子蓋在上。
“好些了?”他問。
月皊搖頭。在被子里蜷起來, 還是覺得很冷。
江厭辭再將疊在床尾備用的一床被子也扯開,再給蓋了一層。他重新在床邊坐下, 給掖著被角, 問:“還冷嗎?”
月皊漉漉的眸子里一片空, 聽了江厭辭的話, 過了一會兒, 才遲鈍地輕輕點頭。
江厭辭回頭,向屋正燃著的炭火。炭火燒得很足,屋子里很暖和。他已試過月皊的額溫,知道沒有發燒。
他沉默地凝著月皊。
良久, 他問:“你是不是想讓我抱你?”
月皊細細的彎眉慢慢攏蹙,空的眼眸緩緩挪過來, 向江厭辭。聚在眼眶里的淚水滾落下去, 模糊的視線逐漸清晰, 眼前的江厭辭五也變得明朗起來。
“是這樣嗎?”茫然地輕聲問。
不是問他,是問自己。
著月皊這個樣子, 江厭辭心里那種陌生的悶再次襲來。
他俯, 推去堆在月皊上的被子, 將纖細的人撈起來, 抱在懷里。
月皊上綿綿,一點力氣也沒有。被錮著江厭辭的懷里,著悉的堅膛。甚至可以聽見他沉穩而有力的心跳聲。
Advertisement
的手垂在側,指尖微弱地了,卻始終不敢抬起來環他的腰。
以前不敢拒絕,如今不敢靠近。
門外,華公主和江月慢轉,悄聲往外走。
華公主眼睛紅紅,心里又痛又酸。待回到方廳,才哽聲道:“我要不了了!”
被疼了這麼多年的無憂小兒,一朝滾落泥里,如今變得這般低微與悲傷。一想到日后江厭辭娶了妻,日日看著廿廿當個低微的婢妾,還不如讓現在一頭撞死算了。
江月慢偏過臉,用帕子去眼角的意,了緒,才頗為慨地開口:“讓廿廿去別人家做兒我也不放心,有時候想著還不如將放在弟弟邊,至放在眼前。”
“這話是從你口中說出來的?你是想讓廿廿一輩子這麼稀里糊涂著,還是想讓你弟弟扶妾為妻?”
“諸以妻為妾,以婢為妾者,徒二年。以妾及客為妻,以婢為妾者,徒一年半。各還正之。 ①”華公主嘆息,“就算不告不管,遠的不說,就說一生治行無缺的杜相,誰人不夸一句賢相,老年將小妾扶為正室,被人所詬病,寫在史書上嗤誚。”
“也有那弄歪腦筋的。鎮恭懿王趙元偓的嫡孫,想把自己的小妾升為繼室,先將人送到府外當友人的兒,洗良家,然后再迎娶進門。可后來事發,還不是被坐奪開府?”
很多路從月皊變奴籍那一刻,就被堵死了。如今給挑的最好的路,只有讓離開江府離開江厭辭,從頭開始。即使是最好的路,華公主也不能著兒走,得將淋淋的真相擺給,讓自己走上去。
江月慢瞧著母親憔悴的模樣,心下不忍。拉著母親的手,心中有悔。
Advertisement
“當初回北時廿廿病著,是我提的餿主意讓不隨行,沒想到……”江月慢哽咽,“不管怎麼樣,我不能看著妹妹困在火坑里。這輩子就算我不嫁了,也要護周全。”
“胡說。你是你,是!不要總覺得自己是長姐,就把什麼都擔在肩上!”
江月慢垂眸,沒接這話。
好半晌,華公主悵然道:“西漢的孔鄉侯傅晏扶妾為妻,落得個奪爵流放的下場。我們不能只想著廿廿,也得為你剛回家的弟弟想一想,為整個江家上上下下幾百口人想一想。圣人自繼位以來,削爵的事做了許多,和咱們江家同期被賜了爵的已經被尋了個由頭奪回了世襲罔替的爵。咱們家要干出這樣的事來,不正好是給圣人遞刀子嗎?”
“月慢,不是母親舍不得這爵位。只是從高落下來,那就是死無全尸。”
“孔鄉侯傅晏被奪爵流放是因為失勢倒臺,隨便挑了個罪名按上去。”江厭辭從門外進來。
華公主一怔,著從外面走進來的江厭辭。
“還有那被坐奪開府的趙宗景,因為是宗親,最后被免了責罰。”
華公主著逐漸走近的兒子,心頭怦怦跳著。
其實,早就知道江厭辭在門外。與江月慢說的那些話,何嘗不是說給江厭辭聽的。
華公主盯著兒子好半晌,長長舒出一口氣,問:“厭辭,你既聽見了。母親倒是要認真問問你的意思。廿廿在我邊當了十七年的閨,如論如何我是舍不得讓做個婢妾的。”
“我沒有意見。”江厭辭回答地毫不遲疑。
華公主皺眉,一時之間不準江厭辭這話什麼意思。
江厭辭默了默,又補一句:“隨。”
Advertisement
江月慢畢竟和江厭辭曾單獨談過一次,約品出弟弟這話的意思。問:“厭辭,你是說都由著廿廿來選嗎?”
“將道理給講清楚,再讓自己想明白不正是母親的用意?”江厭辭反問。
“想留就留,想走就走。”
從始至終,江厭辭對月皊的去留態度從未變過。沒有人能留下,也沒有人能趕走。
只憑自己選。
“厭辭。”華公主站起。皺眉著兒子,鄭重地說:“我不可能讓廿廿做一個小妾。”
江厭辭又一次覺得和長安這些高門里的人流有些障礙。他反思,這興許不是這些貴人們的問題,而是他的問題。長安的這些貴人們在意的東西,他太不在意了。
“隨。”江厭辭再勉力解釋,“想做妾我便不娶妻。想為妻那就當妻。”
華公主略震驚地著面前的兒子,顯然對這答案很是意外。
江厭辭再開口:“我要出府一趟,先走了。”
江厭辭頷首,轉往外走。
華公主怔怔著江厭辭的背影,慢吞吞坐下來。過了一會兒,疑問:“月慢,我沒有聽錯吧?這才多久,有那麼深嗎?他會不會哄人的?”
江月慢遲疑了一會兒,才不確定地接話:“興許江湖人就是這樣不拘小節?無所畏懼?”
江月慢這話倒是提醒了華公主。華公主想起剛剛江厭辭隨口提到趙宗景和孔鄉侯傅晏的事。意識到這個兒子是讀過書的。可是一個從小無父無母的孤兒不僅有一好武藝,還能讀書?
華公主心里突然有了一個猜測——是有人將他收養了,或者仔細栽培過嗎?如果栽培他的人知道他的份呢?
Advertisement
華公主來不及多想,就看見江厭辭回來了。他臂彎里掛著的那件紅的式斗篷很是顯眼。
江厭辭邁步進來,發現華公主的視線落在他臂彎的斗篷上,他解釋一句:“我帶月皊出去一趟。”
華公主點頭。
江厭辭穿過方廳,進了月皊的房間,不多時,和月皊一起出來。月皊低著頭跟在江厭辭后,紅彤彤的斗篷裹在上。
他們兩個出來時,華公主已經不在方廳。府里來了些人過來拜年,和江月慢往前院去了。
來的都是些京中后輩,七八個年輕人。戚平霄也在其列。
華公主看著立在人群里的戚平霄,心里有些唏噓。之前在皇后娘娘面前說本就不同意月皊嫁給太子李淙,這話雖是為了故意□□后,卻也有幾分真。
若月皊執意想嫁,這個做母親的是不會阻止嫁給李淙的。可若讓給月皊挑,戚平霄才是挑中的好郞子。
戚家人口簡單,家風也淳正,是個極好的歸宿。戚平霄也是個端正的好孩子,為人和善有禮又有學識,都說他開了春的科舉能奪得狀元之銜。
可惜……
罷了。華公主輕嘆了一聲,收了收思緒,不再想那些不可能的事了。
因江厭辭出了府,來的這群年輕郎君也沒久待,短暫寒暄后就告退離去。
華公主琢磨了一下,那為江厭辭辦的宴席最近就應該辦了。好讓他盡快地融進京城的圈子里。
·
不是江厭辭要帶著月皊出府,而是他看月皊蔫蔫的,問想不想出去轉轉。月皊想了一會兒,說想去見離娘。
月皊踏上離娘的畫舫時,不見紅兒,瞧見離娘一個人在收拾東西。
“廿廿今日過來了。快來坐。”離娘眉眼含笑地放下手里的事,碎步迎上來,請月皊和江厭辭座,又去給他們兩個人倒茶。
月皊看著收拾好的箱籠,問:“你要搬走了嗎?”
“是啊,哪能做一輩子的賣笑人呢。”離娘聲,“在船上生活了四年,都快忘了踩在實地上的日子了。”
江厭辭不太喜歡畫舫里的香味道,起走出了舫,在舫前的木凳上坐下。
離娘琢磨了一下,拿了一壺酒送到舫外的江厭辭邊,對他笑笑,又折回了舫,和月皊說話。拉著月皊在窗下的凳坐下,聲問:“怎麼了?是不是有什麼事?”
月皊彎起眼睛來,對離娘淺淺地笑著,說:“想出來轉轉。便想到姐姐了。”
離娘了然。垂下眼,聲道:“可你不應該總是來我這里,對你不好的。”
抬抬頭,示意坐在前面的江厭辭,低聲音:“他可能會不喜歡你總到我這種地方來。”
月皊搖頭:“三郎不會。”
離娘笑笑,不再勸。
“你搬走之后會去哪兒呀?”月皊問。
“其實地方還沒有選好,只是先將東西收拾了。”離娘聲音溫溫,“興許會挑一個不算太熱鬧的地方,開一家香鋪子。除了賣笑,我也只會調香了。”
月皊眼前浮現一家開在小巷里的香鋪子,竟也生出了幾分憧憬之。問:“我可以和你一起開香鋪子嗎?我會做花鈿和各種小首飾呢。”
離娘想著月皊不大可能和一起開小鋪子。月皊終究和這種無依無靠的人不一樣。不過還是說:“好啊,如果你想來,我自然歡迎的。”
“對了,一直知道你的閨名是廿廿,卻不知是哪個字。是懷念的念嗎?”離娘問。
月皊將離娘的手拉過來,用手指頭在離娘的手心寫下一個“廿”字,一邊寫著一邊輕聲解釋:“我阿姐生辰是四月初四,阿耶便給取了同音的小名娰娰。我生辰是二十號,便廿廿啦。阿娘說我們的出生是上天賜下的相逢日。”
月皊半垂著眼睛,角掛著一點淺笑。只是這笑容很淺。不是個能藏心事的人,離娘能看得出來月皊緒有些低落。
“那姐姐的名字呢?”月皊略歪著頭向離娘。
離娘笑笑,隨口道:“我自己隨便起的。”
因一生都在離別。
瞧著月皊心不太好,便說:“我給你彈琵琶聽吧?你上次不是說我家鄉的小調很好聽嗎?”
“好。”月皊地應著,又安靜地坐在一旁,聽離娘唱起姚族的離別歌謠。
淺淺的哀思聲聲溢出,漫漫漂浮在水波淋淋的水面。
一曲終了,兩個彷徨的可憐人都紅了眼睛。
月皊收起緒,先扯起角乖乖的笑起來。含笑向離娘,說:“姚族的歌謠真好聽,如果有機會以后去那里瞧瞧。”
離娘很小便離開了那里,卻仍舊對故土有些久遠的印象。點頭,亦悵然道:“若有機會,我也想再回去瞧瞧。”
只是離娘覺得似乎沒有這個機會了。隨著母親的死,和故土便難以再續上關聯。至于父親,那是個不存在的人。
·
月皊跟在江厭辭后,亦步亦趨地沿著河畔往回走。偏過臉,向側的河面,河面上停著一艘艘畫舫,還亮著些河燈,熱鬧又華麗。
忽然想起了宜縣那條安靜的小河。垂柳彎腰,柳枝凍在河面里。
“月皊。”江厭辭停下來,轉過著。
月皊也跟著停下腳步,抬起頭,斗篷的兜帽寬大卻遮了的視線。抬起手來,將兜帽茸茸的邊兒往上抬了抬出一雙眼睛來,著江厭辭:“三郎?”
“過兩天挑個天氣好的日子,去跟你養父母拜年。”江厭辭道。
月皊一下子想到了白家。原來過去這麼久,江厭辭的主意從未變過,只是推遲。
下意識向后退了一步。
江厭辭在開口前,先一步補一句:“沒有趕你走,你也不用住在白家。”
河邊的風忽然有點大,將月皊兜帽上的雪白的茸吹得東搖西晃。風里混了些細沙,將眼睛瞇起來。
江厭辭抬手,將抬高兜帽的手放下來,讓寬大的兜帽徹底落下來,將的頭臉遮住。
他牽的手卻沒松開,牽著往前走。
“只有寄名在別人家,才能改了你的奴籍。”
月皊低頭往前走,悶悶琢磨了一會兒,嗡語:“哦,我明白了。婢妾變良妾再……”
月皊驚覺說錯了話。
猜你喜歡
-
完結326 章
大唐女法醫
一部穿越小說,女主角強大,男主角強大,總之真的很好看啊
97.9萬字8 16887 -
完結125 章
絕寵鬼醫毒妃
她,風,卻因功高蓋主,與兩位好友悲慘身亡,卻意外重生!她,將軍府不得寵的小女兒,上不得父愛,下慘遭兄弟姐妹欺凌,丫的,不發威當她是病貓啊!琴棋書畫,不懂!孫子兵法行不!陰謀詭計,不知!神醫毒術出神入化,好嘛!他,楚雲國最爲得寵的傻王,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可熟不知,得寵的背後,卻是,暗鴆毒血!一場羞辱的賜婚,一場簡單的試探,她嫁給他,相見,一樣的狂傲一樣的不羈,一樣的嗜血,是惺惺相惜,還是生死宿敵!亦或是死生不離!
31.6萬字8.33 30276 -
完結978 章

錦衣玉令
時雍上輩子為了男人肝腦塗地,拼到最後得了個“女魔頭”的惡名慘死詔獄,這才明白穿越必有愛情是個笑話。重生到阿拾身上,她決定做個平平無奇的女差役混吃等死。可從此以後,錦衣衛大都督靠她續命。東廠大太監叫她姑姑。太子爺是她看著長大的。一樁樁詭案奇案逼她出手。這該死的人設,非讓她做殘暴無情的絕代妖姬? 【小劇場】時雍露胳膊露小腳丫,人說:不守婦道!時雍當街扒地痞衣服,人說:不知廉恥!時雍把床搖得嘎吱響,人說:不堪入耳!時雍能文能武能破案,人說:不倫不類!某人想:既然阻止不了她興風作浪,不如留在身邊為己所用。用過之后,某人開始頭痛。“你怎麼越發胡作非為?”“你慣的。”“唉,你就仗著本座喜歡你。”……
239.1萬字8.18 26202 -
完結256 章
大清風華:庶女當家
她,是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認真工作生活,盡情享受美麗人生,過得愜意又多采!豈料,她因一次意外就這麼「穿」了!穿越來到熟悉的清朝。 她過去隻在歷史課本和電視劇上讀過清朝、瞭解清朝,卻沒想到自己已然置身其中!待在陌生的大宅門、身邊都是穿著清裝的人、聽他們說著陌生的話語……這一切的一切對她來說簡直是一場噩夢! 而如果這隻是一場夢,她會欣然接受,好好享受這「大清一日遊」,可這不是一場夢,她是真真實實的成了穿越的女主角,變身清朝潘家七小姐──潘微月。 潘微月是潘家不受寵的庶女,被自己病重的姊姊潘微華作主嫁給她的丈夫方十一當平妻,成為方十一的「候補」妻子。隻因潘微華不久於人世,為了保住自己唯一的兒子在方家的地位,她用盡心機讓妹妹潘微月替補自己,成為方家的少奶奶。 可潘微月不知何故,竟在洞房當晚撞牆自盡,就這麼昏死過去。 而這個潘微月,就是她的新身分。 完全陌生的自己,和未知的一切讓她茫然又心慌,但為了存活下去,她隻能自立自強,尋求生存之道……
76.1萬字8 6339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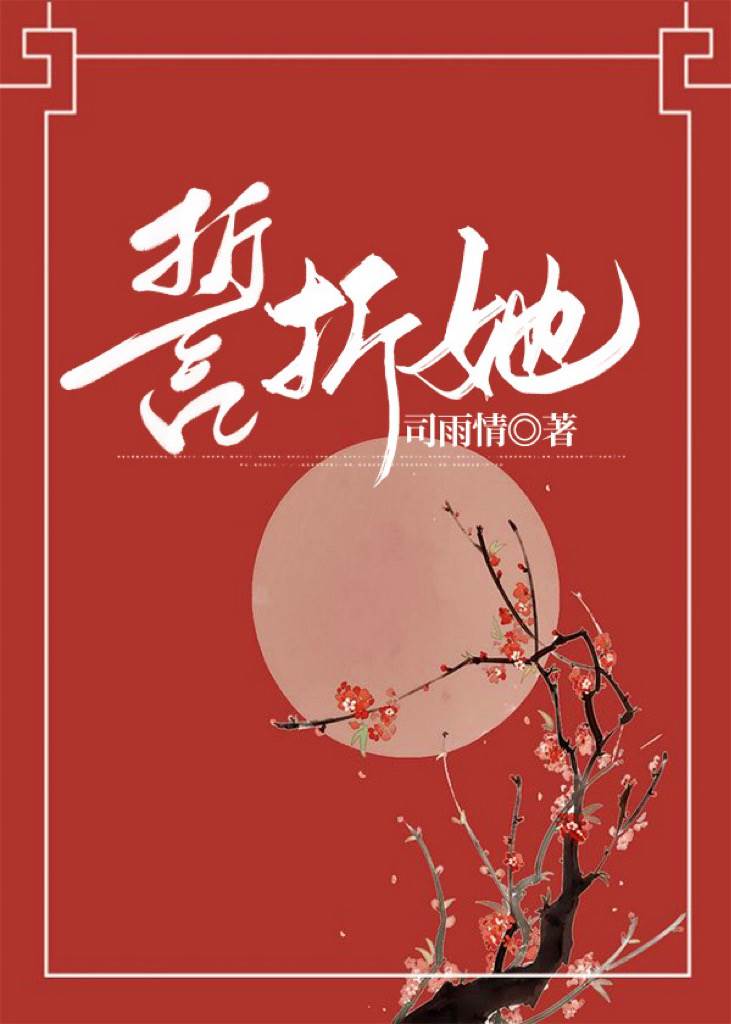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699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