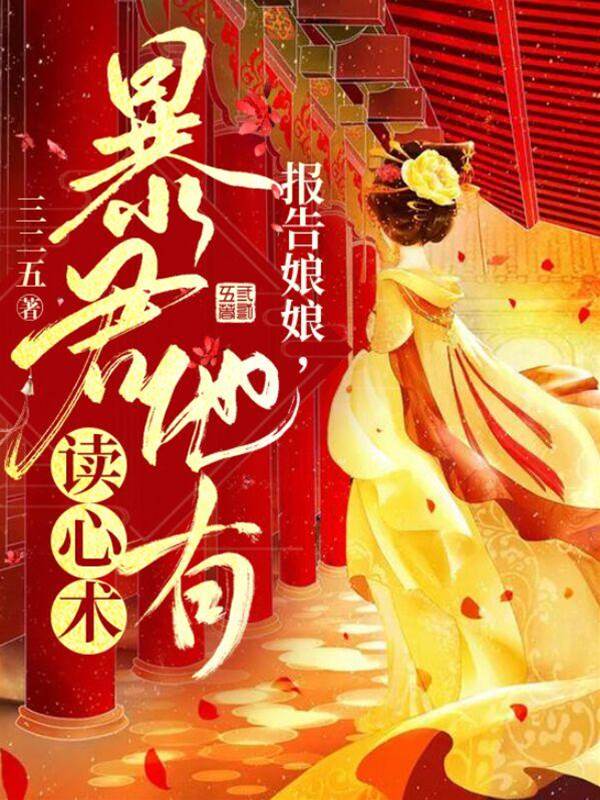《與宿敵成親了》 第88節
我們怎可屈居人後?”
薑一愣,被他這番話逗樂,道:“你小孩兒麽,連親也要爭個先後?”
“不論才學還是武力,我從未輸過他們分毫,婚姻大事自然也不能輸,更重要的是——”說罷,苻離傾俯首,在薑耳畔道,“我想要你。”
薑心間一,|麻之滿上四肢百骸。
這真是一個明朗的天氣,背靠著青石磚牆,看到苻離手,將圈在自己與牆之間,看到他眸中倒映著斑駁的碎影,著不同尋常的炙熱和深沉……如無數次那般,怦然心。
去阮府的時候,已是傍晚時分。
這些時日,阮玉已經能下榻行走,隻是久病初愈,不太朗,走一刻鍾就累得不行。薑帶著在後院裏賞,慫恿飲了一小杯梅子酒,看到日漸的臉上泛出些許健康的紅暈,薑才踏實了許多。
“阿遇見了什麽好事,這般開心?”阮玉有些累了,坐在院中的石凳上問道,邊掛著禮貌而斂的笑,一如曾經。
“懲惡揚善,是特別好的事。”薑笑著了阮玉的臉頰,道,“阿玉你要記得,不管你經曆了什麽,都會有很多人你,非常非常你。”
阮玉隻是懵懂地看著。薑歎道:“終有一日,你會明白的。”
日落月升,應天府又是一個燈火璀璨的夜晚,而被抄沒的平津侯府中,卻是一片漆黑慘淡。
“你來做什麽?”薛晚晴憤怒的聲音打破沉寂,油燈搖晃中,發髻淩,猛然起道,“滾!我不需要你的憐憫!”
程溫站在黑越越的門口,表平靜,眼中既無嘲弄,也無一憐憫。
“守門的校尉隻給了我一刻鍾的時間,有幾句話,我說完便走。”夜涼如水,程溫沒有進門,隻隔著一道門檻緩緩道,“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為何要接近薛家,又要叛離薛家麽?”
Advertisement
“你不要說!我知你是為了阮玉那個賤人!”薛晚晴倏地變得激起來,紅著眼厲聲道,“我就知道你和不清不楚!程溫你知道麽,我寧可希你是貪圖薛家的權勢,也不希你是為了而毀了我!”
“不。此事和阮姑娘有關,卻並非全因而起,實不相瞞,我對薛家的憎恨從六年前便開始了。”不知過了多久,程溫問,“我有個妹妹,你可知道因何而死?”
第86章
程溫家中貧寒,父親隻是個懦弱的窮酸秀才,科舉仕便是他唯一的出路。可生在應天府這樣權貴雲集、人才濟濟的地方,程溫須得比別人更努力才能站穩腳跟,故而每月的朔,他都極回家,潛心留在書院中苦讀。
往往到了換季之時,家中老母會和妹妹一同來給他送吃食和。弘昌十年的秋天,他記得很清楚,那是十月初三,天氣忽然間冷得厲害,母親染了咳疾,出不了門,便讓十四歲的妹妹單獨給他送秋和吃食。
小妹原是和趕集的婦人一同前來的,但婦人們忙著采購,竟忘了等一同回家。小妹隻能提著空空的食盒獨自穿過街市,走過僻靜的荒郊,步行一個多時辰回家……
就在離家三裏地的田間小路上,出事了。
接到母親傳來的消息,他顧不得收拾便匆忙回了家。十四歲的妹妹衫襤褸,出來不青青紫紫的掐痕,清麗娟秀的臉上滿是淚水,隻是絕地搖頭乞求:“娘,你別問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誰!求求你們……求求你們不要再問了!”
傷害妹妹的,是國子監的太學生。
程溫見到了妹妹掙紮時從對方裳上扯下的玉飾,並一塊拇指大的碎布條——布條是上等的煙罩紗,那是太學生才有資格穿的服飾。
Advertisement
接下來的半年猶如地獄般煎熬——父親傷,又因妹妹的遭遇鬱結於心,不久便撒手人寰;小妹不了街坊四鄰的流言蜚語,在一個淒寒的夜投湖自盡,雖被聽到靜趕來的他及時救起,卻陷了永久的昏迷……
程溫變得不那麽說話了,考國子監查出真兇了他支撐他走過那段晦暗歲月的唯一力量。
弘昌十一年春,他功考國子監書學館。查出十月初三外出學生的名單並不難,畢竟十月初三是朔歸學的第一日,若太學生在那日出現在郊外,便隻可能是逃學,而逃學者,監丞必定有記載。
“去年十月初三,學生在東郊小道上拾到玉佩一枚,看樣式應是國子監太學生的佩玉,想來是出遊時失在路上,不知先生可否查看那日出遊的同窗是哪幾人?學生好將玉佩歸還給他。”
“初三是講學日,敢在那時逃課的也隻有那幾個混世魔王了。”監丞翻看考勤薄,角一,厭惡道,“喏,平津侯世子薛睿,大理寺卿之子張顯,刑部尚書之子雷祖德……那日隻有他們三人溜出去秋獵。”
程溫很快見到了那三名紈絝。他不知道自己費了多大的力氣,才勉強住心中翻湧的暗和憎恨。
“玉是我的。我說怎麽找不著了呢,原來是丟在那兒了。”涼亭中,薛睿油頭麵,左右臂膀各攬著名笑得邪氣的狐朋狗友,大手一揮,朝程溫丟了幾兩銀子的碎錢,“這世上竟真有拾金不昧的傻子,小爺賞你了!”
幾顆碎銀子蹦蹦躂躂的落在程溫的腳下,更襯得他的鞋子陳舊無比。他沒有撿銀子,隻是在薛睿等人的哄笑中轉離去,袖中十指幾乎摳爛掌心。
國子監裏,也不全是惡人,終究是好人居多的。譬如苻大公子,薑姑娘,還有他的阮姑娘……
Advertisement
那日淒寒,他撿著被薛晚晴的鬥篷掃落的紙筆,驀地一隻白如水蔥的手替他拾起筆,抬眸間,阮玉地朝他笑著,說:“給。”
就在這一瞬,他見著了他的。
“你問我為何如此憎恨薛家?隻因我最親的人,最的人,皆是毀於薛家之手。我做不到像薑那般高尚,隻要薛睿一人償債,我卻終日想著如何才能整個薛家債償,想來想去,唯有深虎方能找到你們的弱點,一擊致命。”
一檻之隔,薛晚晴在油燈的影裏啜泣,瞪著驚恐的眼神著程溫,如同在看著一個可怕的怪。程溫站在門外的黑暗中,俊秀的臉上沒有痛苦也不再憎恨,隻餘風波後的平靜,淡然道,“你曾罵我懦弱,其實,我隻是比別人更能忍。你爹命我埋葬的每一,我都清楚地記得他們草墳的位置。盡管我並未殺人,但看到那一被你爹下令殺死的麵目扭曲的時,我不怕嗎?不,我很害怕,害怕到夜不能寐,所以我的府上,永遠立著他們的牌位和長明燈,這是我的懺悔,也是我用來擊倒你們的最後證據。”
“你要將那些首的份和位置告訴錦衛?”薛晚晴很快明白了他的手段:一旦那些被查出,薛家便會多上一項‘殘殺異己’的死罪,到時別說是父親,便是自己也要貶為庶人,甚至賣為奴……
“不要!程溫我求求你不要!”薛晚晴哭到幾乎斷氣,再無半分從前的蠻任。普通一聲跪下,匍匐著爬到程溫腳下,攥著他的下裳乞求道,“我替兄長和爹爹給你賠罪!給你妹妹磕頭!如果可以……如果可以,我甚至可以給阮玉磕頭下跪!我懺悔,我真的再也不敢了,求求你放薛家一條活路!不要……不要去告發爹爹!再說了,我爹的事你也參與了,雖不是死罪,但即便你將功折罪,仕途也必定會影響……程溫,你忍心將自己的前途搭上嗎?啊?”
Advertisement
程溫一不,任憑薛晚晴死死攥住自己的裳下擺,道:“縣主放心,至今明兩日,我不會去揭發此事。我會等到後天,太子大婚過後。”
薛晚晴一怔,不明白他此舉的意義。
“按禮,東宮大婚之日必定會大赦天下,即便薛家定了死罪也會被赦免。”程溫垂下眼,有一顆冰冷的淚珠垂落,濺在地磚上。
沒人知道他這顆眼淚為誰而流。程溫說,“所以,我會在太子婚後再呈上證據。”│思│兔│網│文│檔│共││與│在│線│閱│讀│
“程溫!你太惡毒了!”薛晚晴蒼白,幾乎崩潰大吼,“我爹和我哥犯下的錯,和我有什麽關係!你憑什麽要牽連到我!你憑什麽不放過我!”
“無辜……小妹和阮姑娘,又何嚐不是無辜之人?”程溫道,“難道你父兄鑄下的每一項大錯,都沒有你的一磚一瓦?那些浸了鮮和死亡不義之財,你不曾?出現在阮姑娘桌上的那張字條,不是你替你兄長傳遞?”
“好……你說的這些我都認!”薛晚晴滿臉絕,跌坐在冰冷的地磚上,哽聲道,“可替兄長傳字條的人……是李沉啊!”
夜風卷地而來,吹滅了堂中唯一的燈盞,四周陷了一片詭譎的黑暗,冷而森寒。
中秋剛過,這風,便已涼骨髓。
八月十八東宮大婚,苻離要負責組織錦衛儀仗隊的護送任務,而薑則忙著給禮部幫忙準備冊封及大婚典禮的流程,何況朝中才剛出了薛家一案,牽涉員頗多,正是人手缺乏之際,故而比往日更為繁忙。
大婚的餘韻持續了七天七夜,好不容易才歇會兒,程溫又上書太子,出一個驚天。
錦衛在程溫的指引下,先後在東郊和西山等四荒地挖出骸九,據查,皆是在私鹽案之後失蹤的證人,原來竟是被薛長慶暗中滅口了!
九,其中不乏有地方員。太子為之驚怒,薛家的罪行算是徹底打下烙印,隻待最後的判決。念在程溫將功折罪,太子並未太過嚴罰於他,隻是削了他半年俸祿,閉門思過。
薛家滅口案剛過去沒兩日,又趕上魏驚鴻和鄔眠雪親。
這對小夫妻皆是薑和苻離的同窗,又是至好友,故而薑和苻離是一定要赴宴慶祝的。
魏驚鴻和鄔眠雪在應天府完婚,再過幾日,他們便會攜手啟程去滄州定居,聽魏驚鴻的語氣,似乎會從軍,以後跟著鄔家軍戍守邊境。
為此,薑還打趣魏驚鴻,說他和贅也差不了兩樣了。
打趣歸打趣,但心底到底是不舍的。當初風華絕代的國子監年們,走的走,嫁的嫁,留在應天府的人已是越發的伶仃了,再也回不去年結伴踏青、曲水流觴的過去。
或許,這便是長的代價罷。
黃昏酉時,新人已拜了堂,薑送新娘子房,而魏驚鴻則還在廳中敬酒待客。新房布置得很是亮堂喜慶,紅燭紅綢明豔無比,冠霞帔的鄔眠雪更是豔無雙。
薑陪鄔眠雪說了會兒話,見房的時辰快到了,便悄聲關門退出。
魏府到都是紅綢緞、紅燈籠,橙紅的火將府照得亮如白晝。廊下,魏驚鴻喝得微醺,也不知是高興還是醉了,桃花眼下一抹緋紅,著烏紗圓領的公服搖搖晃晃走來,搭
猜你喜歡
-
完結1713 章

秦嶺中醫小娘子
穿越成農家女,溫竹青表示不怕不怕,好在有醫術傍身,我可以發家致富奔小康…… 咦?你怎麼不按套路來?還沒吃苦咋就采了人參娃娃吃穿不愁?還沒有被媒人踏破門檻咋就有了個未婚夫? 明明小村姑咋就成了身世複雜出身大家? 好吧好吧,征服狡黠的未婚夫,拿下商界頭把交椅,也算你是人生贏家!
298.7萬字7.82 301708 -
完結46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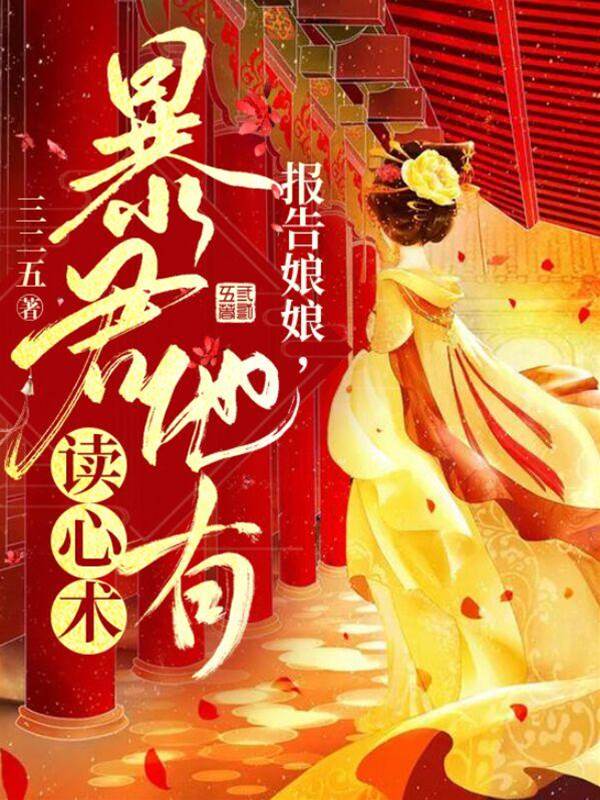
報告娘娘,暴君他有讀心術祝無歡鳳長夜
(雙潔 沙雕 救贖 爆笑互懟)穿越成史上死得最慘的皇後,她天天都想幹掉暴君做女皇,卻不知暴君有讀心術。暴君病重她哭求上蒼,暴君正感動,卻聽她心聲,【求上蒼賜狗暴君速死,本宮要登基!】暴君為她廢除六宮,…
87.7萬字8 2164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