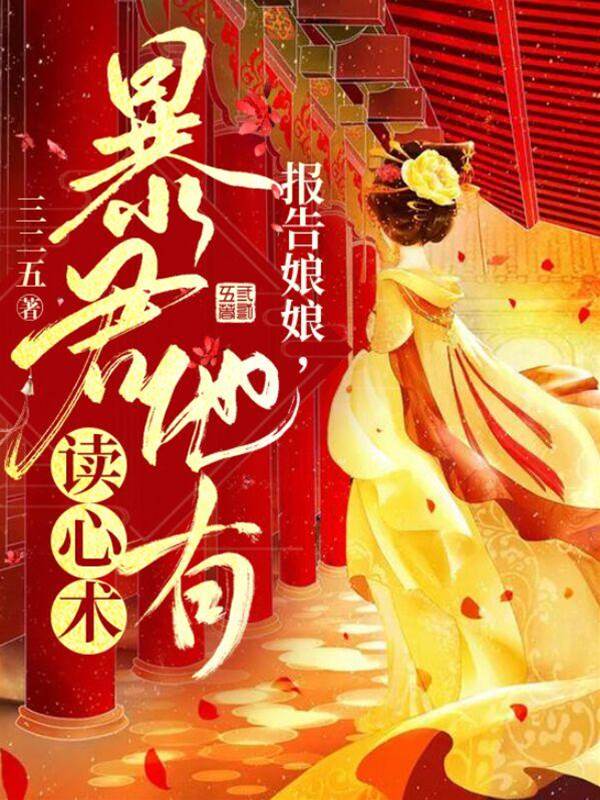《朕甚是心累》 第8章陛下威武
早朝,大元殿。
彈劾沈玉的人,還真是上輩子同一個人,吏部陳尚書陳池。
出頭鳥,往往沒有什麽好下場。
“陛下,沈玉在嗍州私自用刑,沒有經過吏部請示陛下您就斬了嗍州的知府,這明顯是越俎代庖,不把皇上你放在眼裏呀。”
方睿的視線落在彈劾沈玉的吏部尚書陳池的上,心裏冷笑道:如果今天是嗍州知府在嗍州斬了欽差大臣,隻怕又該說是為朕分憂了。
被參本的沈玉表很淡,沒有喜沒有憂,似乎本就不畏別人說什麽。
對呀,怎麽會怕,不僅僅是無愧於心,且就昨日皇上也都說了,斬了個臣,就是為他排憂解難了。
“陳大人,你這話就不對了,何為欽差,欽差就是代天子出巡,難道天子出巡,斬了個貪還得請示吏部嗎?”
方睿聞聲,尋聲看去,說這話的人還是是顧長卿,上一次貌似也是顧長卿替沈玉說話。
金都有四大公子,無論是人品,相貌,還有文采等才能都出類拔萃的,沈玉為其一,其二就是這顧長卿,樣貌氣質與沈玉的清冷不同,整個人給他人覺就是溫潤如玉的公子。
對於顧長卿的話,方睿讚同的點了點頭。
顧長卿這個人如果不是他上一輩子瞎了眼,埋沒了他,估計也能幹出一番大事業。
顧長卿有抱負,卻也不與太後王氏一族同流合汙,這一點是最為難能可貴的。
陳尚書瞪了一眼顧長卿,怒斥道:“你強詞奪理!”
方睿瞥了一眼陳尚書,不疾不徐的喊了一聲:“陳尚書。”
陳尚書聽聞皇上了一聲他,轉回向龍椅之上,彎下腰:“臣在。”
“前幾天你們吏部似乎決了一群臣賊子,是嗎?”
陳尚書不知道皇上突然提起幾天前的時候是為何,慢了半拍才應道:“回稟陛下,確有此……”
Advertisement
“是誰給你的膽子!”
陳尚書還為未說話,方睿便一聲怒斥,嚇得陳尚書一怔,立馬跪了下來:“陛下,這是決臣賊子……”
方睿怒瞪著陳尚書:“你倒給朕說說看是什麽樣的臣賊子!?”
陳尚書不明白這禍水怎麽就引到了他的上來。
陳尚書大抵是因為心虛,額頭之上冒出了冷汗,臉上也有幾分的蒼白,“稟陛下,是、是複興會。”
方睿冷哼,倒是知道尋替罪羔羊。
複興會是前朝建立反對大啟的幫派,前朝皇帝昏庸無道,殘害忠良,他的祖父是方氏皇族,便舉起旗幟,率有誌之士造反,前朝皇帝國破便在大軍圍著大元殿的時候,一頭撞死在了大元殿的柱子之上,
有餘孽逃了出來,前朝皇帝的皇後,念其無辜被封為說太後,隻是這後麵……不僅僅降了皇後,還了他的祖母。
祖母為太後時期懷有孕,生下前朝太子,一生下便夭折了,但是舊朝餘孽卻說太子沒有死,擁立舊朝太子立了複興會,如今已經有五十幾年了,被朝廷剿了那麽多年,早就不氣候了,居然還敢拿出來當替死鬼。
方睿冷眼睨著陳尚書,語氣如冰霜,“可別人告訴朕,哪些隻是些平民老百姓,祖籍三代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何來的臣賊子之說?”
陳尚書咽了咽口水,故作鎮定,“陛下,哪些的確是些臣賊子,若是沒有真憑實據,臣也不敢抓人呀。”
方睿冷冷一笑,“你的證據暫且不看,倒是先看看別人給朕的證據!”隨之看向容泰,“把證據拿上來。”
早兩日他就讓容泰著手調查,收集。
證據二字一出來,整個朝堂上頓時議論紛紛,陳尚書的額頭之上留下冷汗,早已經不淡定。
Advertisement
容泰便朝著大門門口喊道:“把東西都帶上來。”
方睿看這陳尚書,那眼神讓陳尚書通生寒,這眼神讓陳尚書想起了先帝,而別人又說先帝最肖帝,帝可是大啟的開國之帝,最得民心,且手腕也及其的厲害,直接鞏固了大啟的百年基業。
若說最像像帝,不是先帝,先帝就曾說過,最像帝的,應當是曾孫方睿,假以時日魄力比當時的帝還盛。
眾臣的視線全部放在大殿的門口,隻見幾個衙役裝扮的人被押著帶了上來,還有一個侍捧著一疊紙,最後是抬著蓋著白布的架子,總共三抬,架子上麵散發著陣陣的臭味,可想而知這白布蓋著的是什麽東西。
陳尚書看著看被抬進大元殿中的三,眼中出現了恐慌,也不控製的蠕著。
王中元看了一眼表已經破綻百出的陳尚書,袖子下的手細細,暗道此人再也留不得,得找個機會,把此人除了。
架子放下,方睿麵無表道:“把布掀了。”
方睿冷冷一笑,問:“陳尚書,可認識他們?殿外可還有三十二像這樣的!”
“陛、陛下!這些全都是些臣賊子。”陳尚書已經慌了。
“誒?這架子上的人我怎麽瞅著有些眼?”旁人都往後退,倒是見多死人的雷聲大往那已經發黑的上麵湊。
瞇起眼瞧著架子上麵一年紀稍大的,忽然眼睛瞪得比銅鈴還大:“這不是我第八房小妾的父親嗎!?我的老嶽父!陳池,老子殺了你!”雷聲大忽的轉,表兇狠,一拳掃出,雷聲大的力氣大如牛,陳尚書猝不及防被一拳打中腹部,整個人猶如是飛了出去,撞到了柱子上麵,發出“嘭”的一聲響,落到了地上,吐了一大口的。
Advertisement
雷聲大還想繼續,方睿怒喝了一聲:“雷聲大!”
雷聲大磨了磨牙,才罷手,委屈的看向方睿:“陛下,你可得給臣做主,那躺在架子上麵的可是我的嶽父,要是我嶽父能是這臣賊子,那我不也了勾結這賊子的同夥?!”
方睿的角一,瞥了一眼雷聲大,“朕會給你一個代,也會給這些躺在這裏的冤魂一個代!”
看向已經昏迷的陳尚書,冷冷一笑:“當真把朕當瞎子了不?這些人可都是金都南門鬆元街的百姓,有富商出天價收購,想要在此建賭坊院,需要府的文書,也需要百姓的同意,可是這些老一輩的人不願意,就一個個抓了起來,安了個臣賊子的罪名,陳池,可真的是膽大包天!”
而侍捧上來的那些都是簽了字按了指印的地契房契,隻是這是不是自願簽的就不得而知了。
“來人,把罪臣陳池送到大理寺,留他命,審出來,這其中還有誰參與了。”
大殿中被清理之後,方睿掃了一眼大殿中的文武百,冷笑一聲,“先斬後奏,朕允許,但就看誰那麽大的膽子奉違,做出如此這等齷蹉的事,朕定斬不饒!”
這一段話,字字如同帶著千斤石,極威嚴,抑得百大氣不敢一下,對於沈玉的事,誰還敢說半個字。
他們也算看出來了,陛下對於沈玉是非常的信任的,簡直就是心腹,沈玉的聖寵,無人能及,誰若是得罪的了沈玉,那就等同是得罪到了皇帝。
退朝之後,方睿坐在龍椅之上,看著已經空曠的大殿,抬起手放在了桌麵上,歎了一口氣。
容泰見方睿悶悶不樂的的樣子,問道:“陛下,還有什麽煩心的?”
Advertisement
方睿看向容泰,笑了一笑,笑中帶著無奈,“煩心的事太多了。”
他已經重生了半個多月,因為重生的回來的這個時候,對於他來說已經是五年前的事了,五年前的事換作一個普通人都不能記得那麽清楚,且他因為中毒記憶衰退了不,他記得的多是與沈玉有關的,就像是現在陳池的這一件事,他若是能清楚的記得,那些人或許還是可以救下來的。
但事實並非如此。
看來,他現在完全不能掉以輕心。
“容泰,準備便服,朕要出宮一趟。”
容泰聞言一愣,遲疑道:“陛下,這還不到響午……”
這麽早就出去,不怕被識破?
方睿角一:“朕是微服,不是做賊。”
容泰瞬間明白,微服是指臉的,做賊的是不臉的……
陛下這是打算明正大的出宮。
“奴才現在就去準備,可陛下這是要去哪?”
“就先去太保府吧。”他這傷的心,也是需要沈玉藉藉的。
出了宮,坐在在馬車之中的沈玉連連打了幾個噴嚏,皺了皺眉,心中想,大抵是昨夜泡在池子中太久了,有些著涼了。
今天在朝堂的事出乎了沈玉的意料,怎麽也想不到事會反轉到這個地步。
朝堂之上的事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但今晚的事才是真正讓頭疼的。
沒有把這件事告訴老太爺,老太爺不了刺激,而且老太爺為人也狠,若是讓他知道了的份被拆穿了,很難想象得出老太爺會為了太保府而做出些什麽過激的事來。
思索再三,沈玉眼中出了些許的冷意,朝著馬車外的車夫道:“讓人去藥鋪,買些砒霜回來,行事,別出了破綻。”
砒霜在尋常藥店買不到,隻要有門道還是可以拿到手的。
馬車外的車夫沒有半分的好奇,也沒有毫的猶豫,應了一聲,“是”。
猜你喜歡
-
完結1961 章

重生後,我嬌養了反派鎮北王
亡國前,慕容妤是宰相嫡女,錦衣玉食奴仆成群,戴著金湯匙出生,名副其實的天之驕女。亡國後,她成了鎮北王的通房。這位鎮北王恨她,厭她,不喜她,但她也得承受著,因為全家人的安危都掌握在他手上。然而在跟了他的第五年,慕容妤重生了。回到她明媚的十五歲,這時候,威懾四方的鎮北王還隻是她宰相府的犬戎奴。未來的鎮北王掰著手指頭細數:大小姐教他練武,教他讀書,還親手做藥丸給他補足身體的虧損,噓寒問暖,無微不至,把他養得威風凜凜氣宇軒昂,他無以為報,隻能以身相許!隻想借這棵大樹靠一靠的慕容妤:“……”她是不是用力過猛了,現在
208.9萬字8.18 53236 -
完結474 章

小皇叔腹黑又難纏
那一夜,他奄奄一息壓著她,“救我,許你一切。”翌日,她甩出契約,“簽了它,從今以后你是我小弟。”面對家人強行逼婚,她應下了當朝小皇叔的提親,卻在大婚前帶著新收的小弟逃去了外地逍遙快活。后來,謠言飛起,街頭巷尾都在傳,“柳家嫡女不知廉恥,拋下未婚夫與野男人私奔!”再后來,某‘小弟’摟著她,當著所有人宣告,“你們口中的野男人,正是本王!”
137.3萬字8 103194 -
完結46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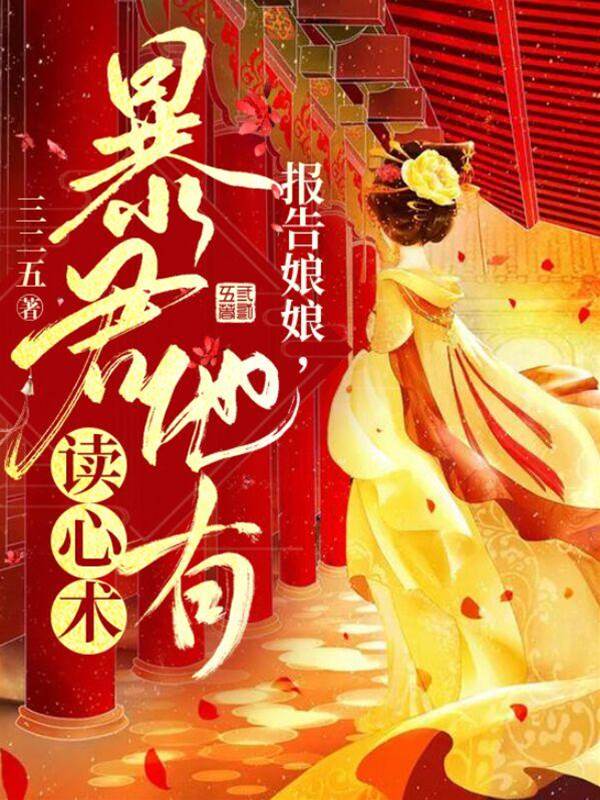
報告娘娘,暴君他有讀心術祝無歡鳳長夜
(雙潔 沙雕 救贖 爆笑互懟)穿越成史上死得最慘的皇後,她天天都想幹掉暴君做女皇,卻不知暴君有讀心術。暴君病重她哭求上蒼,暴君正感動,卻聽她心聲,【求上蒼賜狗暴君速死,本宮要登基!】暴君為她廢除六宮,…
87.7萬字8 22402 -
完結321 章

別人御獸,我召喚老公
許靈昀穿越初就面死局,為了活命,她為自己爭取到參加覺醒大典的機會。別人召喚出來的都是毛茸茸,而她在眾目昭彰中,召喚了只凄艷詭譎,口器森然的蟲族之王。 世人皆知,皇女許靈昀自絕靈之地走出,憑一己之力將燕金鐵騎逼退千里,又將海異人族的殿宇攪得天翻地覆,其兇殘鐵血展露無遺。 但他們不知道的是,當月色拂過樹梢,猙獰可怖的蟲族將少女納入柔軟的腹腔。 再之后,殘暴血腥的蟲族,乖張缺愛的人魚,狂暴兇殘的魔龍,無序的古神混沌之主,都只為她一人——俯首稱臣。
63.6萬字8 29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