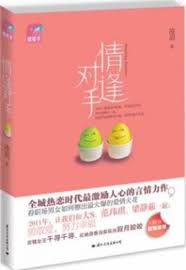《我閉眼了,你親吧》 第61章
兩周后,城人民醫院。
秦野站在病床前和邢驚遲說著話:“隊長,今天搜救隊撤離了。那男人的尸找到了,他們沒找到林丞宴,但都說生存的幾率很小,估計是..”
他沒多說,有些話沒必要說的那麼明白。
余峯坐在椅子上一邊啃蘋果一邊瞅著邢驚遲的臉。明明傷都好的差不多了,他們隊長臉還黑的和什麼似的,心想估計還和嫂子鬧別扭呢。
若換作兩年前,這點傷邢驚遲在醫院里呆一天都嫌多。
秦野的擊水平在他們隊里是數一數二的,完全避開了要害,他一點兒事都沒有。但礙于阮枝蒼白的臉,邢驚遲實在是說不出要出院這種話來。
而且..從那天開始,阮枝就沒怎麼和他說過話。
邢驚遲心里清楚阮枝近來冷淡的態度是為什麼。可對他來說,當時那樣的況,別說是一條,就算那男人要他的命他也得給。
氣他不在乎自己,而他無法辯駁。
這些天兩人就這麼僵著,邢驚遲怎麼哄都沒辦法。
只能老實在醫院里呆著。
這個時間已臨近過年。
因著這件特大盜竊案他們隊里忙了快一個月,好在案子很快就破了。不然市局和他們的力都大,這個年怕是沒法好過。現在就不一樣了,他們非但能好好過年,還能有不獎金,最近他們隊里人人心都不錯。當然這心好的人里面不包括邢驚遲。
秦野說完案子的事后看了眼時間,估著這個點阮枝快來了,就拉著余峯準備走人。臨走了才想來有點事沒說,這件事他實在是猶豫了很久,想來想去還是得說。
“隊長,還有件事。”秦野說觀察著邢驚遲的臉斟酌著措辭,“那條退役的警犬,就我們那天在山里遇見的那條,上山那會兒還給我們帶路來著。它在警隊呆了好些天了,還乖的。你看看是繼續養在隊里還是怎麼著?”
Advertisement
秦野說的是諾索。
它的主人不在了,了一條孤狗。
邢驚遲沉默片刻,應道:“我帶回家,明天出院了就去接它。”
秦野和余峯聽了都是一愣,兩個人對視一眼。
他們說完就走了,走到半路正好遇見來送飯的阮枝。
阮枝看見他們抿笑了一下:“秦野,余峯。明天就是年三十了,你們該放假了吧?”
“嫂子。”
秦野和余峯開口喊。
這段時間阮枝看起來又清瘦了不。
看見他們仍和以前一樣,溫又親近,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已經整整兩周沒對邢驚遲笑了。這是人夫妻之間的事,他們也不好摻和。
余峯笑著應:“對,今兒就放假了。”
本來是早該放的,但案子在這兒沒辦法,好在趕在年前解決了。
秦野輕輕扯了余峯一下,心說你可別打擾嫂子去見隊長了。余峯這會兒也機靈,說了句還有事就和秦野一塊兒溜了,跑得還快。
他們走后阮枝面上的笑意就淡了下來。
微低著頭往邢驚遲的病房里走。
片刻后,邢驚遲房門被敲響。
輕輕的扣門聲,他在這兩周聽了數次。
站在窗前的邢驚遲作極其迅速地躺回了病床,作之快宛如幻影。等阮枝開門進來的時候,邢驚遲已經在床上躺好了。
本來邢驚遲還想裝睡,但一見阮枝就皺起了眉:“怎麼穿這麼?”
天下預報說今天可能會下雪,阮枝卻連條圍巾都沒有戴。邢驚遲看著瘦削的下,心間麻麻的疼痛泛上來。
阮枝抬眸看了邢驚遲一眼。
他的恢復能力實在是好,上周就恢復的和以前一樣了,看起來很神。但不放心,就不提出院的事,每天都來送飯,晚上睡在這里,第二天一早走。
Advertisement
邢驚遲那句話說完后阮枝沒應聲。
一時間病房變得很安靜,除了阮枝拿出碗筷的聲音就沒其他聲響了。
邢驚遲盯著白皙的側臉,有一肚子話想說卻說不出來,只怕說了更惹生氣。就只好這麼傻看著,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枝枝。”
阮枝不理他,只繼續自己手里的作。
等把飯菜都在小桌子上擺好了,才輕聲說了一句:“吃飯。”
說完阮枝就坐到不遠的小沙發上去了,繼續看沒看完的書。放假前賀蘭鈞找,說年后有個和西北合作的項目,問有沒有興趣。阮枝一聽就知道是賀蘭鈞特意來問的,這段時間出了這麼多事,他想著讓換個環境去散散心,可能會恢復好一點。
阮枝想了想就答應了,也想去走走。
這幾天都在看關于項目的書和資料。
邢驚遲沒看面前富的飯菜,一直注視著坐在沙發上的人。
他低聲問:“枝枝,你自己吃了沒有?”
阮枝不應聲,他作勢就要下床。
這會兒才有了靜,掀起眼皮輕飄飄地掃他一眼。
這一眼就讓邢驚遲就不敢了,老實回床上開始吃飯,只是眼睛還黏在上。
阮枝垂著眼瞼,書上的容卻不怎麼看的進去。
那男人吃飯怎麼又那麼快,明明和一起吃的時候改了不。忍了忍還是沒忍住,抬起臉看他:“吃慢點。”
邢驚遲一頓。
黑眸落在繃著的小臉上,心里卻明朗起來。
他笑了一下:“好。”
比昨天吃飯的時候多說一句話。
因著這句吃慢點,邢驚遲恨不得數著米粒吃。
等邢驚遲吃完飯,阮枝合上書起去收拾,順便把明天出院的事兒說了:“明天上午我來辦出院手續,過年哪兒都不去,就在家。”
Advertisement
邢驚遲瞧著阮枝的臉。
這是不去邢家也不去林家的意思。
邢驚遲當然應好,他不得哪兒都不去,只想和阮枝在家里呆著。他看著阮枝收拾完了才說起早上秦野和他說的事。
“枝枝,搜救隊沒找到人,他們今天撤離了。”邢驚遲一邊說一邊注意著阮枝的神變化,“還有,我和秦野說,明天帶諾索回家。”
阮枝斂眸,輕聲應:“知道了。”
邢驚遲向來是擅長察別人的緒的,原本這在阮枝上也是管用的,他能分辨什麼時候開心什麼時候不開心。但現在不一樣,一點兒緒波都沒有。
邢驚遲很擔心。
阮枝現在這樣的狀態并不健康。
下午阮枝有事,兩人說完話之后又去找了邢驚遲的主治醫師,確認邢驚遲沒事可以出院之后就走了。只留下邢驚遲一個人地看著門口。
中午才過完邢驚遲就盼著下午了。
他獨自出了會兒神才拿起電腦開始理剩下的事。
天氣預報說今天要下午,等天漸漸暗下來的時候果然下了雪。
雪下得格外大,洋洋灑灑,像是天被了個窟窿似的著急忙慌地往下落。
邢驚遲起在窗前看了一會兒雪,心里擔心阮枝卻不敢給打電話。這個時間應該在過來的路上,他不想讓在開車的時候分心。
等天完全暗下來的時候,地面上已經覆了一層薄薄的雪。
邢驚遲念著阮枝,沒辦法在病房里等下去,披了件大就下樓去了停車場。沒多久他就看見了阮枝那輛小巧的車開進來。
邢驚遲站在暗里看著。
阮枝下了車,手里還是拎著飯盒。只是卻沒有像他想的那樣立即往口走,仰著頭看了一眼住院樓,是在看他的病房。
Advertisement
就那樣立在雪里,仰頭看了許久。
邢驚遲眼睜睜地看著手抹了抹眼角,他想走過去抱,想哄和說別哭,可這時候他卻一步都彈不得,一句話都說不上來。
直到阮枝了,邢驚遲才生生地邁開步子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阮枝吸了吸鼻子,將淚意都下才垂著頭往里走。風雪從領口灌進去,不由打了個寒。這些天邢驚遲不在,總是忘記戴圍巾。
明明以前都記得。
可是這個冬天,每個早上都是邢驚遲替戴好圍巾和手套,又替系好鞋帶再出門的。可是現在邢驚遲住了院,沒人再為做這些了。
這些天睡在醫院里,晚上邢驚遲以為睡著了,會下床抱著上床睡,等到了早上再把放回去,裝作無事發生的模樣。
阮枝越想越難,握著飯盒的手了。
總覺得這些天著的緒要藏不住,想大哭一場卻又強忍著。
等阮枝平復了緒再上樓已經是十分鐘之后了。
邢驚遲這一次沒再躺在床上裝模作樣,等阮枝敲響了門他就搶先一步把門打開了。暗沉沉的視線落在阮枝微紅的雙眼上。
阮枝怔了一瞬,隨即就垂下了眸,看著自己和邢驚遲的腳尖。
他立在原地一不。
邢驚遲堵在門口不讓進去,他看了一會兒忽然手上的眼角,不問是不是哭了,只低聲道:“吃完飯我想出去散步。”
阮枝心里那點兒悲傷一下子就被火氣下去了。
抬眸瞪了邢驚遲一眼,雖然水汪汪的眸一點兒震懾力都沒有,一把把他推開,直接越過他走進了病房。纖弱的背影生生走出了氣勢洶洶的覺。
阮枝越想越生氣。
這大雪天的說要出去散步,他是想氣死誰。
因著這點氣,阮枝手里的作也大,一時間病房里都是叮鈴哐啷的響聲。碗筷被重重地放在桌上,直到被人從后擁住。
阮枝下意識地掙扎。
可這點兒力氣哪撼得橫在腰間的手,男人的下地在的頸側,溫熱的氣息拂過來,語氣也顯得可憐:“老婆。”
他又低低地喊:“老婆,我錯了。”
阮枝氣悶:“松開我,吃飯。”
邢驚遲抱著不放,直到覺真要生氣了才見好就收。晚飯向來是他們兩個人一起吃的,這一點也是邢驚遲能夠忍耐下去的原因。
窗外下著雪,屋里亮著燈。
兩人坐在小圓桌邊吃飯,邢驚遲一看這湯就知道又燉了一下午。這段時間他每天都能喝到不同的補湯,這待遇都快趕上皇帝了。
阮枝悶著臉吃飯,的碗里還會時不時就多出一點兒東西來。
一塊、一筷子菜等等。
阮枝筷子一停,又瞪邊上的男人一眼。
邢驚遲只好收回手,但眼睛還是和黏在上似的,見吃了半碗就要放下,忍不住開口:“枝枝,就兩口,別剩著。”
這些天他眼看著瘦下去,卻什麼都做不了。
要不是明天能出院,他可能今晚就要把人直接扛回家去。阮枝不理他,他心里也不好,緒一直抑著,但每當對上的眸卻發不出脾氣來。
阮枝手里的作頓了頓,還是拿起筷子把剩下兩口飯吃了。
以前這個時候阮枝總會留在餐桌上陪邢驚遲吃完飯的,但這些天吃完就起出門,也不管他。今天也是一樣,吃完就出去找護士了。
雖然可以出院了,但邢驚遲的傷口還沒長好。
得去仔細問問注意事項,他上的疤痕夠多了,起碼得長好看點。
等阮枝和護士聊完再回病房的時候邢驚遲已經把飯盒都洗干凈了,乖乖地坐在床上等回來。阮枝這些天難得見到他這副模樣,溫順又聽話。
平日里邢驚遲都是強勢霸道的,現在倒像是換了個人似的。
阮枝走到床邊掀開被子,扯起他的腳看了看那猙獰的傷口,借著燈仔細看了許久才側頭問:“想出去散步?”
邢驚遲“嗯”了一聲。
其實這是這些天來邢驚遲頭一次提出要去散步,阮枝也不知道這男人大雪天的怎麼突然要整這一出。心,只好道:“去換服。”
猜你喜歡
-
完結143 章

無法抗拒的他
蘇雲被綠了,怒甩渣男。 將真心收回后再不肯輕易給人。 戀愛麼,何必那麼認真。 何勉偏要蘇雲的心,徐徐圖之。 何勉:「要不要和我談戀愛,不用負責的那種」 蘇云:「……好」 後來。 何勉:「你不對我負責沒關係,我對你負責就行」 蘇云:「為什麼是我?我有過去的」 配不上你。 何勉:「沒事,誰都有瞎的時候,我不怪你」
3.6萬字8 8356 -
完結29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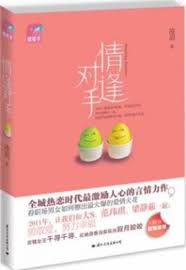
情逢對手
我們兩個,始終沒有愛的一樣深,等等我,讓我努力追上你
55.5萬字8.18 3350 -
完結736 章

退燒
(雙潔,1v1,互撩) 沈宴是江城最有名的浪蕩大少,所有女人都想投入他的懷抱。 可他玩世不恭,什麼都不在乎。 直到 他雙目血紅,箍住女人細腰的手臂上青筋暴起,用卑微的語氣祈求:池歡,不要走…… 原來他心裡那場火,只肯為一個人而燃燒。 池歡和秦駱離婚的當晚,頭腦發熱找上了沈宴。 本以為只是一時纏綿,卻不想,自己早已步步走入沈宴的領地之中。 待她清醒時,才發現這是一場預謀多年的夜宴之邀。 膚白貌美天生媚骨VS八塊腹肌極品尤物
101.1萬字8.18 149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