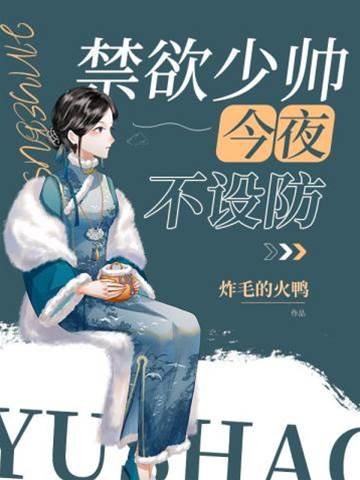《豪門二嫁:只偏愛她》 第94章 一面之詞
全部人坐上桌以后,陳祖安的表總算沒有之前那麼深沉,但是也明顯沒了之前的熱絡,倒是會時不時的給我夾菜或者囑咐我多吃一些。
對于他突如其來的熱絡,我心里也知道他這番作也是起了存心膈應陳若安的心思,所以照單全收,統統都來之不拒,也不管其他人是個什麼表,只是耳觀鼻鼻觀心的吃著自己碗里的飯菜,這段時間一連好幾天都吃著自己做的或者點外賣,確實齁得慌,而吃來吃去,才發現還是容媽做的飯菜比較合我口味。
而在陳祖安不知道是第幾次給我夾菜的時候,陳若安終于坐在一邊看不下去了,或許也是不滿他對沈睿綏的冷漠,忍不住嗔怪的看了眼陳祖安,語氣帶著怨念,“爸,您怎麼就記得陳曦吃蘆筍燜,不記得我其實也吃了,您全程都沒理我一下,給夾就不給我夾嗎?”
陳祖安聞言,眸睨了一眼,卻是輕哼了一聲,“陳曦跟你不同,嫁了人,回娘家就沒有那麼方便,而你一直待在家里,什麼好吃的沒僅你吃,還用得著我對你客氣?”
這句話挑不出任何錯,陳若安一時半會兒找不出反駁的話來回擊,臉更加不好看了。
倒是坐在旁的沈睿綏,一開始一直安靜的,在聽到陳若安的抱怨時,則不不慢的夾了塊不聲的放到了的碗中,語氣低的對說,“吃吧。”
陳若安聽了,眼里幾乎是不敢置信的看向他,與他四目相對一會兒,似乎在確定著什麼,但是很明顯的,臉上的不開心瞬間煙消云散,只聽笑一聲,立即夾起了碗中的放了中。
Advertisement
兩個人無聲的眼神流,看上去倒是分外和諧。
我夾菜的作停了停,隨后將目移向此時正一臉溫的看著陳若安的沈睿綏,此時,他臉上的寵溺很明顯,仿佛陳若安就是他摯一般,至于到底存在幾分真心,恐怕就只有他們當事人清楚了。
我不著痕跡的勾了勾,就在我將要移開目的時候,沈睿綏卻忽然將目轉向了我,猝不及防,我充滿打量的視線被他逮了個正著,我不由一愣,反倒是他依舊從容不迫的,甚至還對我若有若無的笑了笑。
我又是一怔。
等到我再去看他的目時,他卻已經移開了視線,繼續安靜的低頭吃飯,仿佛剛剛的眼神流只是一場錯覺而已。
我暗自皺了下眉。
吃過飯,沈睿綏主告辭,陳祖安顯然樂見其,他總算是出了一笑意,“天也不早,那我就不留你了。”
一旁的陳若安不不愿,但是又礙于陳祖安在場,挽留的話生生的吞了回去。
沈睿綏渾不在意的笑了笑,停頓了一下,隨即把目看向我,微笑得,“大嫂要不要我送一程?”
我看著他,然后指了指停在車子里的賓利,“謝謝,我今天開車來了。”
他隨著我手指的方向看了眼,然后一臉恍然大悟的樣子,“是大哥的車,大哥出差了?”
我沒多想,點了點頭。
然而下一秒他卻頗為意味深長的說了一句,“說起大哥我倒是想起一件事,前幾天聽爸說安氏集團的外部工程出了問題,剛好涉及到之前與沈氏合作的項目,那個地方倒是不遠,就在b城,說起來那里我還有些悉,大哥在那邊讀過幾年書,我小時候也去過,大哥帶我吃過那里的紅豆餅,不知道大嫂知不知道這次大哥是不是去的b城?我想讓他帶點紅豆餅給我。”
Advertisement
我默了默,沈彥遲和我說的是去國外出差,與沈睿綏說的完全不同,但是我也不能輕信他的一面之詞。
于是我道,“他工作上的事我很過問,只知道他是去出差,至于去哪里我并不知道,要不你自己打個電話給他問一問?”
聞言,沈睿綏則搖了搖頭,“大哥忙工作的時候我還是不打擾了。”
我沒有說話。
接著他又接了一句,“我知道安娜姐確實是去了b城代替安伯父解決問題,我可以找幫我帶也是一樣的。”
說完不等我反應,就對陳祖安頷首了一下,然后轉走了。
陳若安見狀,趕追了上去,就連陳祖安低聲阻攔都沒聽見,把他氣得直瞪眼。
我站在那里看著沈睿綏離去的背影,腦海里浮想出他剛剛那些話,有些怔怔出神。
陳祖安剛剛自然也聽得一清二楚,他見我神恍惚,不由冷哼了一聲,“他的話你別太往心里去,明眼人都聽得出來他是在故意挑撥,你要是相信了才是上了他的當。而且沈睿綏這個人給人覺總是沉沉的,無論是氣質什麼,都比他大哥差遠了,我看也就陳若安那個傻丫頭才蠢得喜歡他。”
我聽了,看了他一眼,帶著揶揄的笑,“看來你很不喜歡他?陳若安倒是好像很中意他的樣子,看這形說不準他還真是你未來的婿,可以啊,豪門沈家,別人還求也求不到了,你多好,兩個兒都嫁進去了。”、
陳祖安立即瞪了我一眼,語氣十分不滿,“陳曦,你這是在落井下石嗎?”
我不置可否,只是默然的看著他。
Advertisement
他被我盯得頗為不自在,補充說了句,“沈家,是什麼人都可以進去的?若安那個子,不適合他們家。”
聞言,我輕笑一聲,“那可未必。”
聲音不大,陳祖安沒聽的清,他追問我剛在嘀咕什麼,我對他笑笑,不再發表任何言論。
因為陳若安回來了。
沉著臉,表很不悅,尤其是看到我角那抹笑的時候,臉非常迅速垮了下去。
擺臉,并不是只有我一人看見。
而我還沒說話,陳祖安倒率先說了,他語氣里增了幾分怒氣,“你和那個沈睿綏真的在?到哪一步了?”
陳若安到底還是不敢公然違逆他,沒好氣的說一聲,“人一走你就急著開堂審問嗎?好歹也進屋說去,免得被有心人聽到了好在上頭做文章。”說話間,還似有似無的看了我一眼。
我當然知道里的這個有心人說的是我。
都是單獨的別墅,而且大晚上的,誰有興趣聽墻角。
不過我并不打算與計較,而是轉頭看向陳祖安,“要不我先回去?反正飯也吃過了,人我也見到了,至于對你未來婿的評價我想你也看到了,這個當事人并不是很樂意我參與其中。”
陳若安聽了,微微冷哼一聲。
而陳祖安臉卻變了變,他眼神一沉,“既然你是陳家人,家里所有的事也理所應當的在場,別人敢不歡迎,看來也是不打算把我當父親,既然如此,那就全都不必說了。”
陳若安一聽,神頓時一僵。
想要開口說話,但是當看到陳祖安此時發怒的樣子,到底還是沒敢往下說。
Advertisement
我卻笑了笑,“其實我參與了也不方便講話,畢竟他也是我的小叔子,所以還是你們父倆關上門去聊一聊比較好,這樣吧,你們去書房說,我今晚就不回去了,住家里,明天早上我們一起去城郊那家很有名的早餐店吃早餐,你看行不行?”
聞言,陳祖安的臉總算稍微緩和幾分。
他隨后瞪了一眼陳若安,“還不趕給我滾到書房里來。”說完就轉往里走。
陳若安這回更是老老實實的沒敢說話,安靜的跟著進去了。
猜你喜歡
-
完結558 章

隱婚老公太神秘
傳聞榮家二少天生殘疾,奇醜無比,無人願嫁,所以花重金娶她進門。而結婚兩年她都未成見過自己的丈夫,還遭人陷害與商界奇才宋臨南有了糾葛。她陷入自責中,宋臨南卻對她窮追不捨,還以此威脅她離婚。她逃,他追;她誠惶誠恐,他樂在其中。直到她發現,自己的殘疾丈夫和宋臨南竟是同一人……輿論、欺騙、陰謀讓這段婚姻走到了儘頭。四年後,一個酷似他的小男孩找他談判:“這位大叔,追我媽的人排到國外了,但你要是資金到位的話,我可以幫你插個隊。”他這才知道,什麼叫做“坑爹”。
98.8萬字8 106536 -
完結10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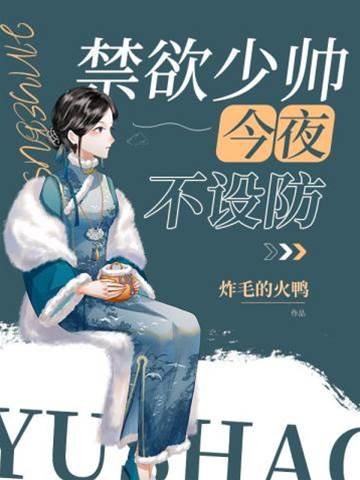
禁欲少帥今夜不設防
一朝身死,她被家人斷開屍骨,抽幹鮮血,還被用符紙鎮壓,無法投胎轉世。她原以為自己會一直作為魂魄遊蕩下去,沒想到她曾經最害怕的男人會將她屍骨挖出,小心珍藏。他散盡家財保她屍身不腐;他與她拜堂成親日日相對;直到有一天,他誤信讒言,剔骨削肉,為她而死。……所幸老天待她不薄,她重活一世,卷土而來,與鬼崽崽結下血契,得到了斬天滅地的力量。她奪家產、鬥惡母、賺大錢,還要保護那個對她至死不渝的愛人。而那個上輩子手段狠戾,殺伐果決的少帥,現在卻夜夜將她摟在懷中,低聲呢喃:“太太救了我,我無以為報,隻能以身相許了。”
193.2萬字8 20524 -
完結141 章

錯嫁瘋批老公後,我直接帶球死遁
夏鳶穿進一本瘋批文,成爲了下場悽慘的惡毒女配,只有抱緊瘋批男主的大腿才能苟活。 系統:“攻略瘋批男主,你就能回家!”夏鳶笑容乖巧:“我會讓瘋批男主成爲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瘋批男主手焊金絲籠。 夏鳶:“金閃閃的好漂亮,你昨天給我買的小鈴鐺可以掛上去嗎?”她鑽進去一秒入睡,愛得不行。 瘋批男主默默拆掉金絲籠,佔有慾十足抱着她哄睡。瘋批男主送給她安裝了追蹤器的手錶。 夏鳶:“你怎麼知道我缺手錶?”她二十四小時戴在手上,瘋批男主偷偷扔掉了手錶,罵它不要碧蓮。 當夏鳶拿下瘋批男主後,系統發出尖銳的爆鳴聲:“宿主,你攻略錯人了!”夏鳶摸了摸鼓起的孕肚:要不……帶球死遁?
26萬字8.18 283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