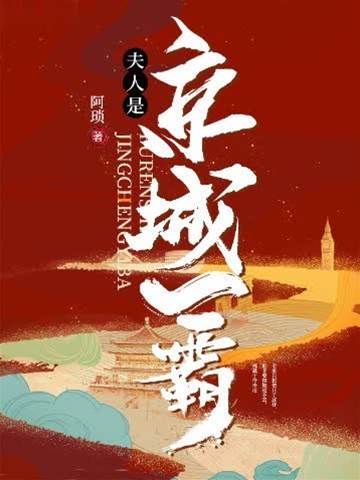《厭春宮》 第一百七十五章 這是有身孕了
“皇上他、他并非故意,”見周旖錦臉蒼白,李祥恍然明白自己犯了大錯,忙輕聲勸道:“周小姐切莫因此介懷……”
話音消散在空曠的殿,周旖錦卻始終抿著,沒有回音。
“我也有些累了,”眼眸中忽而泛起不易察覺的潤,低聲道:“柳綠,回棲宮罷。”
周旖錦走時的背影決絕,毫不容許李祥挽留,不一會兒的功夫,養心殿便恢復了靜謐,連針落地的聲音都清晰可聞。
李祥心中懊悔不已,小心翼翼往寢殿走去,一進門便被濃烈的酒意襲了滿。
“皇上,飲酒傷,您還是早些歇息吧。”李祥自知無功而返,聲音都有些,蹲下將空了的酒壇收起。
邊,魏璇沉郁了許久,悶頭又飲,酒杯重重磕在桌面上,杯底殘留的酒出令人膽戰心驚的漣漪。
“……”
魏璇的聲音有些沙啞,抬起頭來,眸中濃重的緒翻滾。
“周小姐方才來了,聽了奴才的話,候了一會兒又回去了。”李祥心里十分沒底氣,垂首不敢看魏璇。
魏璇沒有說話,微垂的眼尾漸漸浮現出惆悵之,似乎周旖錦的不作為,已經斬釘截鐵地昭示了某種結果。
不知過了多久,他沉沉嘆了口氣:“朕知道了。”
魏璇的腦海中昏昏沉沉,手指攥著,可那種悉的無力一瞬間如颶風般襲來,他清楚地看見自己心里的恐懼。
哪怕他如今已是人人敬仰的九五之尊,可踏了的泥沼,卻毫不占上風,見到那林騫的一刻,他骨子里的占有囂著,幾乎已失了理智,卻又怕自己只是周旖錦寂寞時消遣的玩——
不過是拿來解悶的東西,他若是因此鬧起來,又像從前那般義無反顧地走了,將他拋棄在此,該如何是好?
Advertisement
“皇上……”李祥還想勸他,卻被魏璇打斷。
“明日、明日朕再去尋。”
魏璇的聲音像是自言自語,他全繃,一副敗象。
周旖錦已不知自己多久沒這般頹喪過了,徹夜著窗外煞白的月,一晃神便照出了白晝。
邊空了人,忽然有些不習慣,整夜清醒得厲害,像是在等他,他一夜也沒來。
刺眼的晨曦穿云層徑直打下來,周旖錦撐著子坐起來,低低嘆了口氣。
心里明白,魏璇是值得信任的,可不知為何,每當想起那養心殿里看到的東西,心中就莫名揣著一陣不安。
貿然宮其實算不上理智的決策,沒人比更清楚,哪怕是帝王,口頭上的話語再漂亮,也不過是清晨的一縷霧,水中看花的泡影,不到最后一刻,隨時便能隨風而逝。
可總是覺得魏璇不一樣。
“娘娘今日醒的真早。”聽見房間的響,柳綠手中端著銅盆,前來服侍周旖錦洗漱,一抬頭卻看見周旖錦毫無的臉,向慘然一笑。
“我子有些不適,一會兒再休息。”
周旖錦捂著那因一夜未眠而發悸的心臟,聲音很輕,接過柳綠遞來的清水時,胃中卻忽的一陣痙攣,險些吐了出來。
“小姐!”
柳綠頓時如臨大敵,忙朝外喚道:“來人啊,快傳太醫——”
不過半柱香的時間,太醫便匆匆趕來,隔著帕子替周旖錦診了脈,臉有些愕然,接著又像是為了確認重新把了次脈,才斬釘截鐵地開口。
“微臣恭喜周小姐!”太醫跪在地上叩首,喜悅之請溢于言表:“您、您這是有孕了!”
滿宮里何人不知,眼前這周小姐是皇上親口承認的未來皇后,而腹中的孩子,不論男,份都是極為貴重的,能為第一個報喜的人,太醫不慨自己今日真是走了大運。
Advertisement
仿佛驚雷乍響,周旖錦臉上寫滿了驚訝,愣了半晌,聲線有些抖:“當真……是有孕了?”
“微臣行醫數十年,從未失手,這喜脈千真萬確!”
太醫的斷言被巨大的喜悅裹挾著徑直沖腦海,周旖錦角不由自主地揚了起來,掩不住心底的激,當即吩咐道:“柳綠,賞。”
素來出手大方,那太醫謝了恩,眉飛舞地走出門外,轉彎忽然撞見一個高大的人影,跪下時手中沉甸甸的金子險些沒捧穩。
魏璇看著那太醫,原本沉重的臉陡然浮現出疑來,他大步流星往寢殿走去,一推開門,便看見周旖錦喜悅的神采,隨著看清他影變得有些搖搖墜。
“你子怎麼了?”魏璇憂心那方才見著的太醫,忙問道。
周旖錦心中仍別扭著,只輕描淡寫地一瞥便不做聲,倒是柳綠被這意外之喜沖擊地頭腦發昏,接過話茬道:“稟皇上,方才小姐子不適,沒想到太醫診出了喜脈。”
聽聞此言,魏璇臉上的沉郁霎時一掃而空,他驚愕地向前走了兩步,從這突如其來的驚喜中回過神,又小心翼翼抬起胳膊,屏息給周旖錦診脈。
“錦兒,確是喜脈,”魏璇說話的氣息都有些不穩,他這樣素來冷靜之人,鮮地出了狂熱的稚氣,聲音頓了一下,又緩和下來,勸道:“這些時日你要多歇息。”
魏璇醫湛,輕易便從那薄弱的脈象中得知周旖錦憂心忡忡,多慮眠。
此刻還未梳妝,不施黛的面容白得像紙,細細上去,亦能察覺其下的倦意。
“錦兒……”
魏璇突然有些后悔起昨日之事,自己憋著火不來見。
若是早些將話說開,哪怕周旖錦真的有什麼過失,他便同從前一樣,讓看清自己的好,再回到自己邊便是,哪會如此傷了子——
Advertisement
更何況如今周旖錦懷了孕,每一副藥方都是他親手所寫,他比任何人都知道這個孩子的來之不易。
魏璇惴惴不安地等了片刻,終于聽見周旖錦含著責怪的聲音回在耳邊:“你從前不是答應我,不開選秀嗎?”
周旖錦偏過頭來他,眼中晦的緒織,不等魏璇回答,又道:“就算要選,怎麼不知會我一聲?”
的聲音越來越低,而魏璇也從起初的驚愕中驀然回過神來,忙解釋道:“那折子不過是些不死心的大臣上奏,說什麼皇嗣為重,我早同他們表示過,除了你后宮不會有任何人。”
“錦兒這不是有孕了嗎,往后連回絕的話都不必再提,”魏璇說著,心中不漾起些許暖意,輕輕握住周旖錦的手,忽然開口:“先皇的孝期那樣久,這孩子的名分等不得,左右你份已昭告天下,五日后,我們便婚,可好?”
“五日?”周旖錦不寧的心方因魏璇的一番話平靜下來,倏地卻被這提議驚了一跳。
不有些費解,問道:“為何這樣倉促?”
“欽天監算過了,是個大吉之日,”魏璇的眸忽然沉了沉,視線垂向地面:“邊疆戰事急,不過多時,我便要親征馳援西域。”
他心中懷著歉意,語氣有些急,懇切道:“此去則一月,多則半年,你獨自留在這京城里,各勢力虎視眈眈,不如早些冊封,授了皇后印,那些人便不敢再為難你。”
“可是……”
周旖錦還有些愣怔,魏璇卻已搶先一步說道:“自即位以來,我便著手準備與你的大婚,早已遣告天地宗廟,問名、納吉一樣不落,如今袍也制好了,一切禮儀制度都不會出差池,你放心便是。”
Advertisement
周旖錦睫撲閃著,聲音忽的梗住了。
魏璇既已決心,也沒理由再推辭,于是便點了點頭。
提到那袍,周旖錦猛然想起昨日令他二人蒙生嫌隙的一幕,遲疑片刻,對視上魏璇那雙幽深的眼眸,抵不住暗蘊,小聲道:“子瑜,昨日花園里……”
停頓的間隙,魏璇的心臟被這短短的字句勒住,連呼吸的聲音都下意識放輕。
“這事要從小時說起,倒是差錯……”
周旖錦娓娓道來,似乎有意安他的緒,又輕輕笑了笑:“他聽說你準備立后一事,你那一番為我洗清責任的話,反而他以為我是不愿……”
“子瑜,我對你絕無二心。”
周旖錦微微仰起頭,眸子里盈盈汲著一汪水,坦然而鄭重地著他。
魏璇怔了許久,他了,似乎想說什麼,眼眶卻先紅了。
“錦兒,我以后……不會再隨意猜忌。”
魏璇抿著,忽然傾上前,一把將周旖錦摟在懷中,聲音低沉:“那林騫膽大妄為,貶算是輕饒了他,況且他能進花園里,不了背后籌劃,我必不會放過他們。”
“錦兒,別生氣了,好不好?”
周旖錦還未反應過來,子便已被魏璇厚實的懷抱包裹。
的側臉依著他的膛,周遭仿佛有一瞬間的寂靜,隨即被魏璇劇烈的心跳聲填滿,沉穩而有力,和他的一樣,熱烈綿長。
這短暫的一刻像是被無限拉長,耳邊咚咚作響心跳聲收攏在一,周旖錦已分不清是他的還是自己的。
“我不怪你,你已經足夠好了。”的手臂環在魏璇腰上,壯且堅的,仿佛能將全部委屈安穩納于其中。
“還不夠好……”
魏璇結了,聲音有些含糊,下一刻,炙熱的吻便已襲來,像春日里細的雨,溫潤和煦的風,纏纏綿綿,永無停歇。
周旖錦閉上眼,早已蓄滿的淚順著致的眼尾落,淌過他捧在頰邊的手,又從指的罅隙跌落。
“錦兒,我你。”魏璇的手了,輕輕拭去了那一滴淚。
猜你喜歡
-
完結184 章
穿書之我成了暴君的掌中嬌
玄風淺不過是吐槽了一句作者無良後媽,竟穿越成了狗血重生文裡命不久矣的惡毒女配!為保小命,她隻得收斂鋒芒,做一尾混吃混喝的美豔鹹魚。不成想,重生歸來的腹黑女主恃寵生嬌,頻頻來找茬...某美豔鹹魚掀桌暴怒,仙力狂漲百倍:“今天老子就讓你女主變炮灰,灰飛煙滅的灰!”某暴君霸氣護鹹魚:“寶貝兒,坐好小板凳乖乖吃瓜去。打臉虐渣什麼的,為夫來~”
32.1萬字5 22571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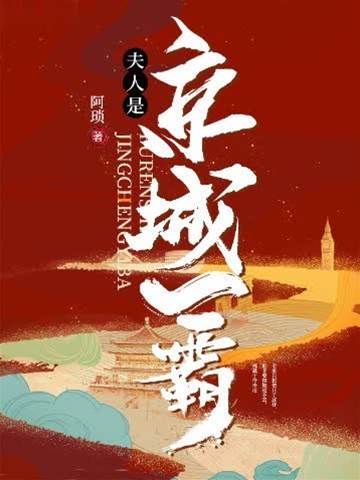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1064 章
全能毒妃:世子降不住
穿越到死人的肚子裏,為了活下去,晞兒只好拚命的從她娘肚子裏爬出來。 狠心至極的爹,看都沒看她一眼,就將她歸為不祥之人。 更是默許二房姨娘將她弄死,搶走她嫡女的位置。 好在上天有眼,她被人救下,十四年後,一朝回府,看她如何替自己討回公道。
186.1萬字8 19787 -
完結791 章

齊歡
她可以陪著他從一介白衣到開國皇帝,雖然因此身死也算大義,足以被後世稱讚。 可如果她不樂意了呢?隻想帶著惹禍的哥哥,小白花娘親,口炮的父親,做一回真正的麻煩精,胡天胡地活一輩子。 等等,那誰誰,你來湊什麼熱鬧。
153.4萬字8 96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