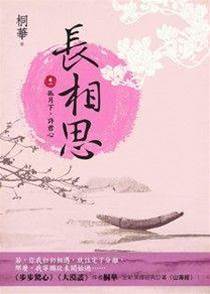《公府貴媳》 第35章 私會
晏長風壞了秦王妃的雅興,自覺把自己發配到了角落坐著。
不知道是不是角落里的不配喝茶,到現在也沒人給送杯茶。百無聊賴地等著十一表哥的丫頭,等得險些睡著。
就在屁快磨出尖的時候,忽然覺有什麼東西砸到了的后背,回頭一看,見花廳側門有個丫頭正朝眨眼睛。
救星可算是來了!
看了眼上座的秦王妃,又環視四周,趁無人關注這邊時離開了座位。
花廳的側門專供客出解決私人問題,其實被看見了也無妨,只是有出無回,還是盡量不惹人注意。
剛出門去腳步倏地一頓,后知后覺反應過來,方才看秦王妃時,好像沒有看見秦惠容。
什麼時候走的?
晏長風一邊琢磨著走出側門,見十一表哥的丫頭遠遠站在恭房附近的花叢中。左右巡視,見周圍無人,便知這丫頭是找準了最好的機會。
快步走向恭房,路過時特意豎著耳朵聽了聽,里面應該沒有人,所以秦惠容中途退出做什麼去了?
今日秦惠容備恩寵,一直被秦王妃拉著說話,要離開也只有以如廁為由,不在恭房就很奇怪。
一面四巡視,一邊不遠不近地跟著小丫頭,一直來到了園子的偏門。
丫頭站在一棵樹下,等到了近前才開口,“表……”
“噓!”
晏長風忽然聽見門外有人說話,立刻示意丫頭噤聲。
丫頭立刻捂住,眼睛轉向了門口。
這個門是專供運送東西用的,只有早上才開,平時無人過來,會是誰?
晏長風躡手躡腳地靠近門口,耳朵著門聽了聽,頓時一樂。
說話的正是裴大世子裴鈺。
“秦姑娘,我自那日見了你之后就念念不忘,今日聽聞你參加芙蓉宴,我特意前來只為見你一面,還請原諒我的冒昧。”
Advertisement
“世子抬,惠容份低微,怎敢高攀……”
晏長風捂住,生怕自己冷笑出聲,想象中的世子與妾,定是干柴烈火不要臉,委實沒想到居然這樣純。
返回樹下,小聲對丫頭道:“快去找人來,說門外有男私會。”
丫頭眼睛登時睜大,吃驚又好奇,但知道眼下不該問,只點點頭,“我知道了表姑娘,可您呢?”
“沒事,我自己會走,有馬麼?”
“有的表姑娘,裴二公子特意吩咐了,給您牽最快的馬,你出去了會有人接應你,有事也不必著急回來還馬,飯可以改日再請。”
晏長風:“……”
這個裴二是蛔蟲托生的吧,什麼都能猜到!
小丫頭得了晏長風的吩咐,快速回到了花廳,心知想要在最快的時間讓這件事發出來,就只有當眾跟秦王妃稟報。
“王妃贖罪,我剛剛看見有位小姐獨自往園子偏門去,一時好奇便跟了過去,卻發現……發現出了偏門,那門外竟是等了個公子!我不敢聲張,只能回來與您代。”
秦王妃大驚,“竟有這等事!”
“千真萬確,不信您可以現在派人去查驗。”
“來人!”秦王妃當即來幾個嬤嬤,命們速去偏門將人帶來,“是小姐也不要顧忌,辦出這樣的事來,想來也不是個安分守己的。”
“是,王妃!”
人派走后,秦王妃的興致也沒了,冷著臉等候抓人的嬤嬤。
盛明宇卻是了不小的驚嚇,方才他看見自家丫頭跑到秦王妃那里,說什麼跟著一個小姐去了偏門,還以為是叛變了來給秦王妃告。直到聽見后面的才恍然大悟,原來是有男私會的好戲瞧!
北都可好久都沒遇上這樣的樂子了,他拳掌地說,“不知道是哪個膽大的小娘子……誒?你大哥那相好呢?”他環顧全場,沒瞧見秦惠容的影子,立刻神了,“不會是吧,私會的不會是你大哥吧?他不是氣跑了麼?”
Advertisement
裴修早就發現秦惠容走了,開始他沒放在心上,后來注意力又放在了晏長風那里,在想有沒有順利出去。
他什麼可能都想了,卻委實沒想到自己溜走,還能順便抓人家的。
“裴鈺不可能白跑一趟。”
盛明宇:“也是,你大哥那人想要什麼就一定要得到。”
在眾人的期盼中,秦惠容很快被幾個嬤嬤帶到了秦王妃跟前。
“怎麼是你!”
秦王妃簡直懷疑嬤嬤抓錯了人。
一個嬤嬤道:“回王妃,我等奉命去往偏門抓人,恰好看見秦姑娘從門外進來,依稀看見門外有個男子的影閃過,好像是,是宋國公府世子。”
方才晏長風在這里一番影,大家心里多有些將信將疑,畢竟秦惠容看著十分知書達理,不像是會勾引別人未婚夫婿的人。
誰知這麼快就被人捉到了證據!
“是我,王妃。”秦惠容倒是十分坦然,“我私自出去未曾與您打招呼,是我失禮了,還請王妃責罵。”
“這豈止是失禮啊!”秦王妃失至極,“你好好的一個孩子,知書達理秀外慧中,我還以為你是個頂好的,怎麼能干出這樣自損的事呢!”
“王妃失了。”秦惠容慚愧地低下頭,“是我糊涂了,我見今日裴世子了氣,擔心他心不好,便,便沒忍住去見了他,一切都是我的錯。”
“是你去見的他?”秦王妃本以為是裴世子招惹了。如果這樣講,興許還能挽回一些面,畢竟一個庶若被世子糾纏,不得不從也有可原。
可如果是去招惹裴世子,那興致就不一樣了,這名聲豈還想要?
秦惠容堅定道:“是我去見了裴世子。”
“好你個秦惠容!”秦淮月從座位上站起來,一路指著秦惠容的鼻子罵到跟前,“我今日帶你出來,本是想帶你長臉的,你竟是干出這等丟臉骯臟之事,你簡直丟盡了我秦家的臉!”
Advertisement
“啪!”
秦淮月一到跟前便給了秦惠容一掌。
秦惠容被打得踉蹌半步,卻只是低頭道歉:“是我錯了,大姑娘要打要罵都行。”
秦淮月說話又是一掌打在秦惠容臉上,“我自然是要打你罵你,與男人私會,勾搭的還是人家的未婚夫婿,便是浸豬籠都不為過!”
眾人又是一驚,這秦惠容一看在家里就是伏低做小慣了,卑微得人唏噓。就算是個庶,也不能當眾說打罵就打罵,豈非連個丫頭還不如?
秦淮月頤指氣使,又一向嫉妒秦惠容有貌有才,甭管家里家外從不給留面子,今日又氣到了頂點,更是理智盡失,打罵都收不住,竟是當著秦王妃的面把人教訓了個夠。
此時在寒風中縱馬狂奔的晏長風并不知道自己惹了多大的熱鬧,只是嘆北都的冬日真不是人的,臉蛋子被寒風刮得生疼。
姚氏在北都有一莊子,位于南郊,距離秦王的莊子不算近,想要趕在天黑前回侯府,就只能快馬加鞭。
幸而十一表哥的快馬強悍,不過半個時辰便到了。
到得山莊別院,先去看了看新的,正在搭建中的鴿谷,此鴿谷并非在山谷,而是在院子里圈了一塊地來改造。因為不能常來,不敢隨意放飛鴿子,只能養在院子里。
又詢問了鴿子幾句,收走了這幾日的來信,這才跑去找柳清儀。
“你可算來了。”柳清儀正在搗鼓的瓶瓶罐罐,見了人立刻放下拉走,“再不來我就要忍不住把那幾個殺手制藥人了。”
“……啥?已經來了?”后癥發作怎麼快嗎?
“是啊,前兩日便來了,后癥發作很快的,不然他們早把我忘了,也無從找我,我怎麼賣解藥?”
Advertisement
晏長風:“……”
這姑娘沒混天下首富簡直天理難容。
“那個小柳,我能問問后癥是什麼嗎?”
柳清儀說:“也沒什麼,就是一吃飯就吐,外加渾發而已。”
晏長風角搐,心說以后打死不能惹了柳四姑娘。
于是很快,便見到了五個抓耳撓腮,蹭墻磨背的殺手。
哦,那個沒有得到啞解藥的殺手居然也在。
“你們是一起來的,還是分頭來的?”晏長風坐在屋里的圈椅上,翹起看他們耍猴。
“二姑娘,求您了,您就饒了我們吧!”有一個絡腮胡的殺手一邊撓一邊將一包東西拿出來,“這些是我們所有的酬勞,都給您吧,我們不賺這遭罪的錢了!”
晏長風瞥了眼那包銀子,“你們?六個人就給這麼點?”
“不是六個,是我們三個!”那絡腮胡指了指另外兩個人,“我們三個,雇我們的人出手極大方,說事再給五,事不也不會要回先頭給的。”
這手筆倒像是章家所為。
晏長風:“藥不是你們下的?”
“什麼藥?我們哥仨雖說在江湖上不是頂尖高手,也不干那等下藥的勾當!”
“哦,那就是你們仨下的藥。”晏長風看向那個還啞著的,“這位兄弟,你還來做什麼呢,你已經失去得解藥的機會了。”
那啞拼命比劃著,像是在說,他還有重要的消息可以代。
猜你喜歡
-
完結97 章

廢後謀
那年,看見他,仿佛就已經中了她的毒,日日思念不得見,最後她嫁給了他的兄弟,他只望她能幸福,哪成想,她的夫君一登基,就將她打入皇陵守孝,既然如此,他不會在放過與她相守的每一個機會了,就算全天下人反對,又如何,他只要她。
17.4萬字8 9475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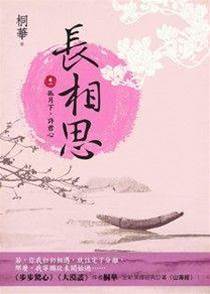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09 -
完結353 章

嫁給白月光的宿敵之后
蘇明嫵本該嫁進東宮,和青梅竹馬的太子舉案齊眉,然而花轎交錯,她被擡進了同日成婚的雍涼王府中。 恨了符欒半輩子,住在王府偏院瓦房,死前才知策劃錯嫁的人是她的心頭硃砂白月光。 一朝重生,蘇明嫵重生在了洞房翌日。好巧不巧,她正以死相逼,要喝避子湯藥... 天子幼弟符欒,十四歲前往涼州封地,十六歲親自出徵北羌,次年得勝被流箭射穿左眼。這樣心狠的大人物,大家心照不宣,蘇明嫵這朵嬌花落入他的手裏,怕是要被磋磨成玩物不止。 尤其是這個美嬌娥,心裏還掛念着她的小情郎,哪有男人能忍得? 雍涼王聞此傳言,似笑非笑點了點頭,好巧,他深以爲然。 婚後滿月歸寧那日,經過樓閣轉角。 “嬌嬌,與母親講,王爺他到底待你如何?可曾欺負你?” 符欒停下腳步,右邊長眸慵懶地掃過去,他的小嬌妻雙頰酡紅,如塊溫香軟玉,正細聲細氣寬慰道:“母親,我是他的人,他幹嘛欺負我呀...” 她是他的人,所以後來,符欒牽着她一起走上至高無上的位置。
53.8萬字8.18 565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