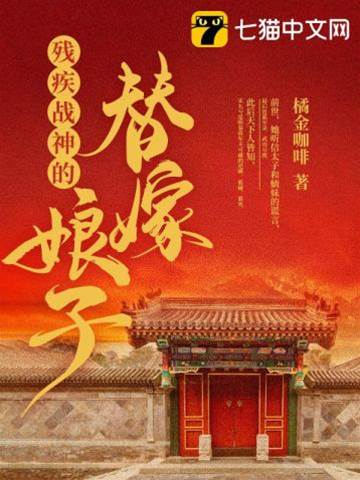《凰權至上》 第60章 衝突
「蔣六曲,孤的命令你也敢不聽,你是想要造反嗎?!」魏津氣極反笑,他的雙目閃過一冰冷之,竟是了殺意。
蔣六曲是在當年的奪門之變中一躍而起的,山海里殺出來的路,實打實的軍功出,哪裡會不到太子殿下雙目中的凜冽。
曾經,蔣六曲就是靠著這近乎野一般的直覺躲過了無數次敵人的襲。
對危險最本能的知讓他瞇了瞇眼。
蔣六曲冷聲說道:「太子殿下言重了,末將只忠於陛下,何來造反一說。」
這位繡花枕頭一般的太子殿下若是把他蔣六曲當一個大老來嚇唬,那就大錯特錯了。
他蔣六曲還沒有這麼蠢!
「看來,你是不把孤這個太子放在眼裡了!」
魏津還是第一次被臣子勾出了這樣劇烈的怒火,他用力掐了一下掌心,語氣冷冰冰地說道:「民間有句俗語: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蔣大人,孤奉勸你一句,做人,還要謹言慎行才是。」
「多謝太子殿下提醒。」
對於魏津話里話外的威脅,蔣六曲小麥的面龐浮上一皮笑不笑的笑容。
陛下正值壯年,龍虎猛,太子殿下想要當家做主,如無不測,二十年後再說吧!
蔣六曲態度里的敷衍幾乎是不加掩飾,毫無對自己的尊重之意。
魏津冷冷牽了下角:自己這個太子當得真是窩囊!
他低頭,手指輕輕拂過袖上暗金線刺繡的祥雲紋路,平聲道:「勞煩蔣大人去向父皇通傳一聲,孤有要事求見,蔣大人這下總該通融了吧。」
魏津話末帶著濃濃的諷刺之意。
蔣六曲像是聽不出來一樣,語氣毫無起伏地道:「太子殿下言重了。殿下您稍等。」
他朝著邊的侍衛招了招手:「張小乙,你這就去通報給馮總管,聽候陛下裁決。」
Advertisement
做張小乙的侍衛領命而去。
蔣六曲隨之在一個宮衛上踹了一腳,對著侍衛暴吼道:「愣著做什麼,還不去給太子殿下搬張椅子來!沒看見太子殿下還站著嗎?」
被踹的侍衛踉蹌了幾步,連忙去找椅子。
蔣六曲瞇了瞇眼,對著剩下的宮衛罵罵咧咧地說道:「一群耳朵都是擺設的東西!太子殿下的吩咐也敢不聽!太子殿下都說了,要我等『謹言慎行』!你們竟敢讓殿下站著!我看你們是想要造反!小心殿下日後要了你們的腦袋!」
被太子先是要挾、再是諷刺,蔣六曲咽不下心中的這口惡氣,忍不住借題發揮,眾目睽睽之下半分不給魏津留面。
偏偏他雖然驕橫、跋扈,卻中有細,話裡面讓人挑不出半個不字,讓魏津這個太子有苦說不出。
「卑職知罪!」宮衛們整齊劃一的請罪聲洪亮至極,像是一記響亮的耳,重重地甩在魏津這個當朝太子的臉上!
都說什麼樣的將領帶出什麼樣的士兵。蔣六曲手下的宮衛同樣是一群驕兵,毫不把魏津這個太子放在眼裡,似乎並不畏懼太子日後會對他們進行打擊、報復。
被一個野蠻的武將當眾奚落,魏津的面十分難看。他強自忍下了腔里的怒意,那雙深海一樣的眼睛像是一頭準備擇人而噬的野,有著濃到化不開的翳。,
蔣六曲暗自覷著太子的臉,不由在心底嗤笑了一聲。
陛下是馬背上奪得的天下,弓馬嫻,有著「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勇,殺的外族片甲不留。
可惜這位太子「子不類父」,被雍王妃拘在宅,徹底寵壞了。
太子不僅拉不開弓,甚至連一匹野馬都馴服不了。
他十三歲時跟著陛下打獵,遇到猛,嚇得兩戰戰、奪命而逃,回去之後竟然連燒三天三夜,如此文弱,一夜之間便為了西北軍中的笑話!
Advertisement
自從太子正位東宮之後,每日里只和文臣來往,言辭之間對於武將多有鄙薄,蔣六曲早就對這位太子不滿已久。
沒想到,今日這個懦弱無能的傢伙抖威風都抖到自己面前來了。蔣六曲哪裡咽的下這口氣。面對魏津殺機重重的目,蔣六曲心中發狠:大不了在太子登基之後,他便解甲歸田!
蔣六曲就不相信了,這個狗太子還能要了自己的命!
張小乙終於在偏殿里找到了一把椅子,他一陣小跑,雙手送至太子面前。
張小乙用袖子在座位上了,語氣恭敬地說道:「太子殿下,您請坐!」
魏津面對這把讓自己難堪至極的椅子,怎麼看都覺得張小乙是在嘲諷自己。
他眉心微擰,低沉的嗓音像是化不開的寒冰:「不必!」
「太子殿下,您這般尊貴的份,怎麼能和末將一樣,就這麼站著!」蔣六曲怪氣地說道,他轉頭繼續對著張小乙罵道:「說你蠢你還真蠢,也不知道給太子殿下在座位上放一張墊,萬一太子殿下了寒氣,你可擔待得起!真以為太子殿下和爾等一樣命賤嗎?」
「蔣大人!」蔣六曲毫不收斂、咄咄人的態度讓魏津忍無可忍,他不由自主地拔高了聲音,低沉、淡漠的嗓音著一居高位的威嚴:「宮衛是父皇的利刃,曾為父皇立下過汗馬功勞,他們每一個人的命,都和孤一樣貴重!」
魏津冰冷、威嚴的目沒有一暖意,他向蔣六曲的視線充滿了迫,淡淡道:「更何況,孤也沒有蔣大人想的那麼貴。」
「太子殿下誤會了,末將這也是以防萬一。若是因為末將的疏忽讓太子殿下有個閃失,末將萬死難贖其罪!」
蔣六曲大義凜然地說道。
Advertisement
魏津被蔣六曲油鹽不進的態度氣了個倒仰,他冷冷一笑,不再贅言。
蔣六曲目中無人,日後再收拾他也不遲,當務之急,是查清楚舅父是生是死。魏津被憤怒沖昏了的大腦有了一清明。若是舅父真的遭逢不測……是誰,膽敢對一國儲君的岳父下手?!
就在魏津暗暗沉之際,馮會獨有的清潤之中帶著一微沙的嗓音從前方傳來:「太子殿下,陛下有請。」
聞言,魏津瞬間收回了思緒,他抬起眼睛,只見父皇的心腹馮會領著兩個小太監迤邐而來。
魏津連忙迎了上去:「馮公公。」
守在東宮門口的宮衛「唰」地一下亮出了利刃。
刀雪亮,耳邊傳來一陣讓人牙酸的破風聲,魏津嚇了一跳,不由後退了一步。
一聲嗤笑,靜靜在空氣里溢散。
魏津如夢初醒,他反應過來自己方才的窘態,忍不住惱怒,厲聲喝道:「放肆!」
蔣六曲皮笑不笑地給魏津賠禮:「太子殿下,底下人不懂事,讓您驚了。」
蔣六曲語氣里著重地咬了一下「驚」二字,生恐魏津聽不出他話語里的嘲諷。
「好了,沒聽到馮公公說了嗎,放行!」蔣六曲對著攔住魏津的兩個宮衛揮了揮手,怒聲道:「你們兩個下去各領二十軍!」
「是!」兩個侍衛齊聲應「是」,朝著魏津拱手一禮,各自退下領罰。
魏津雖然十分清楚蔣六曲這是在故意折辱自己,奈何兩個侍衛已經被罰了二十軍,罰不可謂不重。
有蔣六曲的罰在先,魏津找不到發作的理由,又不能親自去監刑,只能再一次吃下這個悶虧。
不過半個時辰而已,魏津連番辱,蔣六曲在他心中已經是個死人了!
魏津不自地咬住了自己的后槽牙,心中暗暗發誓:總有一天,他會大權在握,生殺予奪盡在己手,讓天下人只能仰他鼻息而活!
Advertisement
「太子殿下,您請吧。」馮會像是沒有看到蔣副統領和太子之間劍拔弩張的氣氛,他朝著魏津微微一笑,很是和善地說道:「太子殿下,不要讓陛下久等。」
「走!」魏津甩了一下袍袖,一張俊的面龐雲布,他大步流星地走到了馮會前面,周像是籠罩著一層無形的冰雪。
著太子筆直、孤傲的背影,馮會暗中搖了搖頭。
蔣六曲原本是陛下的親衛,一路護送陛下回京,為陛下拼殺出了一條至尊之路。
陛下的上百親衛,最後只剩下了十人不到,蔣六曲便是其中一個,可見其忠心和勇武!因此,蔣六曲一直深陛下的信任。
往日里,蔣六曲仗著從龍之功,十分跋扈,等閑人不放在眼裡。可是在陛下面前,他比誰都老實。
可見,蔣六曲的跋扈也是分人的!
馮會都不知道該如何評價魏津這位太子才好了,堂堂儲君,竟被一個臣下轄制住,傳出去簡直丟盡了面。
著太子越走越快的步伐,馮會連忙甩掉腦海里這些不合時宜的想法,一溜小跑,連忙跟上了太子的腳步。
到了養心殿,馮會上前一步,走到魏津前面攔住了他:「太子殿下稍等,奴才這就進去通傳一聲。」
魏津原本是要不管不顧闖進去的!馮會這一攔,瞬間讓魏津的頭腦清醒了不,他剎住形,朝著馮會拱了拱手:「那就有勞馮公公了。」
「太子殿下客氣了。」馮會微微一笑,走進大殿。
猜你喜歡
-
完結406 章

穿越農家之妃惹王爺
《本文一對一,男女主雙潔,種田爽文。》穆清媱這個現代法醫穿越了,變成了村裡的病秧子。為了逃脫祖母的壓迫,帶著受欺負的娘和姐姐脫離他們。動手,動腦,做生意,賺銀子。什麼?祖母那些人後悔了?那關她什麼事!敢來找事,穆清媱肯定動手又動口,收拾的他們說不出話。小日子過的溫馨又愜意間,一堆熱心腸的人給她介紹各種優秀的小夥紙。“沒看到我家沒有兒子嗎?本姑娘隻招婿,不嫁人。”一句話打發一群人。本以為她可以繼續悠閑的過日子。啪嗒!“聽說你家招女婿,本王自帶嫁妝,過來試試。”“呃”
171.7萬字8.18 77183 -
完結4608 章

農家小福女
周家的四哥賭輸了錢,母親病重,賭場的人還想讓滿寶賣身償債。 村裏人都說周家的寶貝疙瘩好日子到頭了,老娘也握著滿寶的小手哭唧唧。 滿寶卻手握系統,帶着兄弟嫂子們開荒,種地,種藥材,開鋪子…… 日子越過越好,嫂子們卻開始憂心滿寶的婚事。 「小姑,庄先生的孫子不錯,又斯文又會讀書,配你正好。」 「小姑,還是錢老爺家的小兒子好,又漂亮,又聽話,一定不會頂嘴。」 滿寶抿嘴一笑:「我早就想好了,就選被我從小揍到大的竹馬白善寶。」
833.4萬字8 146619 -
完結52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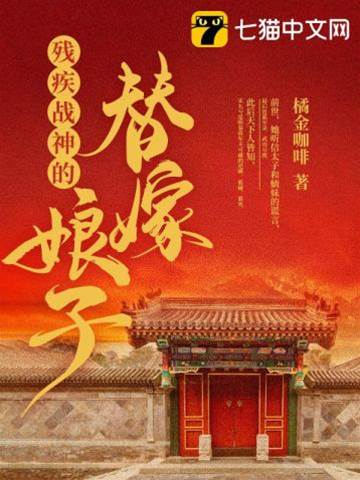
殘疾戰神的替嫁娘子
【重生+男強女強+瘋批+打臉】前世,她聽信太子和嫡妹的謊言,連累至親慘死,最后自己武功盡廢,被一杯毒酒送走。重生后她答應替嫁給命不久矣的戰神,對所謂的侯府沒有絲毫親情。嘲笑她、欺辱她的人,她照打不誤,絕不手軟。傳言戰神將軍殺孽太重,活不過一…
97.6萬字8 305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