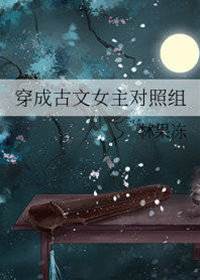《多情應笑我》 第17章
小元寶的代做功課業務越做越大。林芳洲發現,小元寶替人做功課,收錢是很隨意的。金子也收,銀子也收,銅板也收,甚至有一次,他收回來兩個鳥蛋,據說是因為對方暫時沒有錢,先押兩個鳥蛋權當借據,等有錢了再來贖回去。
林芳洲哭笑不得,深深覺得自己做的壞事報應到小元寶的頭上——往常遊手好閑、吃了上頓沒下頓時,就經常賒賬。
小元寶做功課的方式也越來越多樣,一開始隻是幫同窗寫寫字,後來發展代作對子、作打油詩,甚至在課堂上用手勢協助同窗回答先生的提問……反正五花八門的,虧他想得出來。
漸漸的,隻因為代做功課這一項,他竟然賺回不錢。林芳洲把那些錢都匯總,算了一筆賬,然後發現,照這樣的速度下去,小元寶一個月可以賺一年的工錢。
除了小元寶,九萬也經常給這個家庭創收。九萬叼回來的兔子,兔被和小元寶吃了,能省頓飯錢;兔子皮硝好了留著,冬天可以賣錢。
娘的,林芳洲覺得自己在這個家越來越抬不起頭了。
小元寶前前後後賺的錢,金銀銅都算上,有一大捧了,林芳洲高興地對小元寶說,“你真是我的小搖錢樹。”
小元寶也很高興,“夠你去賭場玩多久?”
這句話令林芳洲到意外。問道:“你希我去賭錢?”
“嗯。”
“為什麽?”
“因為你喜歡賭錢。”
“你不怕我把錢都輸了?”
“千金難買一笑,花錢買高興是值得的,”小元寶說著,又連忙補充道,“隻是這次輸錢不要哭了。”
林芳洲有些慨,還有點,“你是第一個勸我去賭錢的人。”
Advertisement
往常有好多人勸不要賭錢,偏不聽,賭癮永遠戒不掉。現在突然有人勸去賭,莫名其妙的,又不想賭了。
林芳洲把那堆錢歸在一,笑嘻嘻道,“要留著給你作聘禮,娶媳婦用。”
一句話,又把小孩逗個臉紅。
第二天,小元寶回到家,問了林芳洲一個很奇怪的問題:“什麽是炒茹茹?”
林芳洲聽到此話,然變,質問道:“這種混話是誰教你的?!”
小元寶深知林芳洲雖偶爾脾氣暴躁,卻很真的發怒,這次這麽大肝火,令他到很意外,他放下飯碗,小心翼翼地看著,不敢說話。
他不說話,更加惱火,“你最近是不是和什麽不三不四的人廝混了?給我老實代!”
“沒有……”
“沒有?沒有,這胡話是誰教給你的?你說出來,我去打斷他的狗!”
“沒有別人教我,我聽說的。”
“聽誰說的?”
“乙班的人,我不認識,沒來往過。”
書院除了蒙學班的小孩外,其他學子按照其自的學問水平分三個班,從高到低依次是甲乙丙,學問夠了可以往上升。這些學子都比小元寶他們大,胡說八道倒是有可能。
林芳洲聽到小元寶這樣說,便鬆了一口氣,瞪他一眼,道,“以後聽到那些髒話就趕躲開,知道了嗎?有人膽敢對你說這個,二話不說朝他老二上踢,記住了嗎?”
“嗯。”小元寶點了點頭,到底還是有些疑,腦中仿佛團了一個疙瘩,忍了忍,終於忍不住了,他又問道,“那,你和縣令是在炒茹茹嗎?”
林芳洲大怒:“我炒你爸爸!”
小元寶輕輕了一下,小聲自語道,“我爸爸你可不敢炒。”
Advertisement
“你說什麽?”
“沒什麽……”
……
林芳洲一連幾天,值班時無打采,幾次言又止,與一同值班的汪鐵釘便有些看不下去,問道:“大郎,我見你這幾日蔫得像霜打了一般,可是賭場又輸個?”
汪鐵釘形容瘦削,人品尚可,隻是說話不中聽,人送綽號“鐵釘”。
林芳洲聽那汪鐵釘如此問,便搖頭道,“我好些天不去賭場了。”
“是不是想去賭場又沒錢,手得慌,所以沒有神?”
“不是。”
“是不是……”他嘿然而笑,“是不是犯了哪家桃花劫……”
林芳洲心裏有事,其實很想找個人傾訴一番,但是又不好意思告訴別人,有人背地裏嚼舌說和縣太爺搞斷袖……太難以啟齒了。
這個嚼舌的人還是兄弟同書院的學子,也算同窗了。
左顧右盼一番,見四下也沒什麽人,便低聲對汪鐵釘說道,“我問你一個問題,你老實回答我。”
“你問。”
“你們,嗯,是不是都覺得……覺得我喜歡男人……”
汪鐵釘聽罷狂笑,又擔心驚了旁人,連忙捂住。
林芳洲:“所以,是的,你們都這麽以為?”
笑過之後,汪鐵釘說道,“何止呢,大家背後都說你是個二刈子。”
“二刈子”是罵人的話,本意是太監,或者和太監類似的男人。
若是正常男人被罵二刈子,怕是有一場架好打,不過林芳洲畢竟是個人,並沒有男人固有的那種自尊,隻是汪鐵釘說話時那幸災樂禍的表,令微有些不痛快。問道,“為什麽說我是二刈子?”
汪鐵釘:“我問你,你平常為何總是係個圍巾,把脖子遮住?即便是三伏天熱得出汗時,圍巾也不摘下來?”
Advertisement
“這個啊?”林芳洲指了指自己的脖子,“我這頸子上有道疤,是時爬樹被樹杈紮傷留下的,因為太難看,所以一直係著圍巾。係習慣了,也並不覺得熱了。”
“真的?”汪鐵釘有些狐疑。
“真的。不然呢,你以為是什麽?”
“我以為是因為你到年紀了不長結,怕被人笑話,所以才用圍巾擋住。”
“這是哪裏話,不信你看,我的疤就在這裏,好多年了。”林芳洲說著,拉開圍巾,把脖上那疤痕展示給汪鐵釘。
汪鐵釘果然看到一道疤痕,嘖嘖搖頭,道,“原來是這樣。”
林芳洲整理好圍巾,問汪鐵釘,“不長結就是二刈子嗎?”
汪鐵釘搖頭道,“也未見得,我有個表弟,結就不很明顯,他親一年後就有了個大胖小子,現在孩子都三個了。”
林芳洲覺得這汪鐵釘腦子不甚清楚,顛三倒四牆頭草一般,搖了搖頭,接過他的話說道:“其實我也差不多,我這結雖沒有旁人那麽大,在床上也是把婆娘幹得哭爹喊娘的。可見從結大小去推斷一個人是不是二刈子,這樣不可靠。”
汪鐵釘來了興趣,“你都沒娶親,把哪個婆娘幹得哭爹喊娘?”
林芳洲神一笑,“良家子,不能跟你說,壞人名譽。”
“嘿呦嘿嘿嘿……”那汪鐵釘笑得很下流。
林芳洲又和汪鐵釘胡謅了一會兒,無非是雙方各自吹噓自己的勇猛,娘們的放浪……其實無聊得很。聊了一會兒天,終於讓汪鐵釘相信,不是二刈子也不是龍好者。
下午散值回家時,林芳洲一邊走一邊想,往後不僅要積極參與討論那些男之事,多吹牛多放屁,平時走在街上還要調戲良家子,如此這般,往後必定要塑造一個“林芳洲很好”的正麵形象,不要讓人以為專門炒茹茹。
Advertisement
否則,若是不巧沾惹上哪個沒沒臊的斷袖,就有的麻煩了。
正胡想著,林芳洲一頭撞見王大刀。王捕頭正帶著幾個人急匆匆往外走,邊還跟著另一個人,看樣子是書院的先生打扮。林芳洲有些好奇,問道:“王捕頭,這麽著急去做什麽?”
“書院出事了,”王捕頭見是衙門裏的人,也不瞞什麽,答道,“打群架,見了,有一個是抬著出去的,生死不明。”
“讀書人也會打架嗎……”林芳洲咋舌,歎道,“還抬著出去呢,真可怕!”
“你兄弟不是也在書院上學嗎,要不要跟我們去看看?”
林芳洲搖頭笑道,“不用,我家小元寶可聽話了,我回家給他做飯。”
“嗯,那我帶幾個弟兄先過去看看。”王捕頭說著,與告辭。他一邊走一邊同旁的先生說話,林芳洲聽到他問先生,“多人?”
“七八個,有大的也有小的。”
“領頭的是誰?”
“林芳思!”
猜你喜歡
-
完結25 章
愛妻帶種逃
那婚前就放話不會把她當妻子看待的夫君,八成犯傻了,不然纔剛摔了交杯酒要她滾出去,怎麼一見她的手腕就變了,還是他真如傳言「生意做到哪,小手摸到哪」那般有戀手癖?要不爲何一眨眼就對她又是愛憐呵護又是纏綿求歡的……寵她之餘,還連所有她在乎的人也都一併照顧了,他說唯有這樣,她纔不會分心去擔心別人,能好好被他獨佔,他說不許她哭,除非是他的愛能寵她到令她流出幸福的眼淚,他說了好多好多,讓她甜上了心頭,也被他填滿心頭,然而也因爲他說了好多,讓她忘了問他爲何對她這麼好,纔會由上門「認親」的公主那兒得知,其實他寵的人不是她,他愛的是前世妻子,而自己手腕上的胎記讓他誤認了……而同時擁有胎記和記憶的公主,似乎纔是他尋尋覓覓的人,她想,他曾給了她那麼多幸福,這次,爲了讓他也得到幸福,即使已懷了孕,即使再痛苦,她都要將他還給他真正愛的人……
8萬字7.82 12634 -
完結2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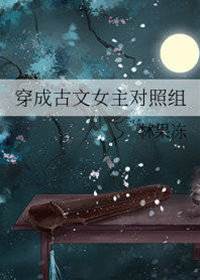
穿成古文女主對照組
楊海燕穿成了古文女主對照組里的那個對照組。 小說劇情里,兩人被賣進同一戶人家當丫頭:原主是大丫鬟、長相好、女紅好、讀書識字,主家落難,奉圣旨嫁給了邊關軍營里的百夫長秦放。 女主是粗使丫環、長相普通、女紅粗糙、沒讀書不認識字,主家落難,也奉聖旨嫁給了邊關軍營裡的百夫長男主韓臻。 自以為優秀的原主一直跟女主比較,結果,女主跟著男主榮陞將軍夫人。而原主作掉了秦放的前程,成了家屬院里女主的對照組。 穿書後: 楊海燕看著身材高大、四肢修長的男人,心裡想,這是她的菜。 秦放看著眼前這個弱不禁風,連桶水都拎不動的女人,心裡想,他一個月1兩銀子、30斤糧食的月例,這些糧食光自己都不夠吃,現在娶了媳婦,他還要把糧食分出去,他好苦。 內心戲很豐富男主VS聰慧隨遇而安女主
81.3萬字8 22007 -
完結590 章

攝政王的末世小農妃
末世女王莊雲黛一朝穿越,成了山村破屋中快要病死的傻女。親爹戰死,親娘遺棄,極品親戚將她跟弟弟妹妹趕到破屋中想把她熬死。莊雲黛當即擼起袖子決定就是乾!原本她只想在古代當個普普通通的女首富,卻沒想到一眼見到在採石場被拘為苦役的他,當場就決定把他認作老公!陸霽青一朝從雲霄之上墜落,成了採石場的苦役,遇到一女子熱情的邀請他當面首。最初,陸霽青:離我遠點!最後,陸霽青:別走!
106.1萬字8.18 243106 -
完結260 章

大師,你桃花開了
【沙雕 甜寵 亡國公主 假和尚 雙潔 毒舌】遇見無塵之前,秦月涼隻想自立自強,一個人幹翻所有覬覦她美貌的人。遇見無塵之後,秦月涼隻想抱緊大腿,讓無塵幹翻所有覬覦她美貌的人。靜安寺外初相見。“大師,人家一個弱女子,你若不管我,我會死的!”“施主,請你看看你腳下的屍體再重新把話說一次……誰是弱女子?”十裏坡外共患難。“聽說出家人不能吃肉,那這隻山雞我就不客氣啦!” “阿彌陀佛,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山雞請分我一半!” 兵臨城下請出山。“大師,出家人不能殺生,天下戰亂與你我何幹?”“施主,忘了告訴你,小僧俗家姓名……燕紅塵。”南景國殺神,燕紅塵。
44.2萬字8 727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