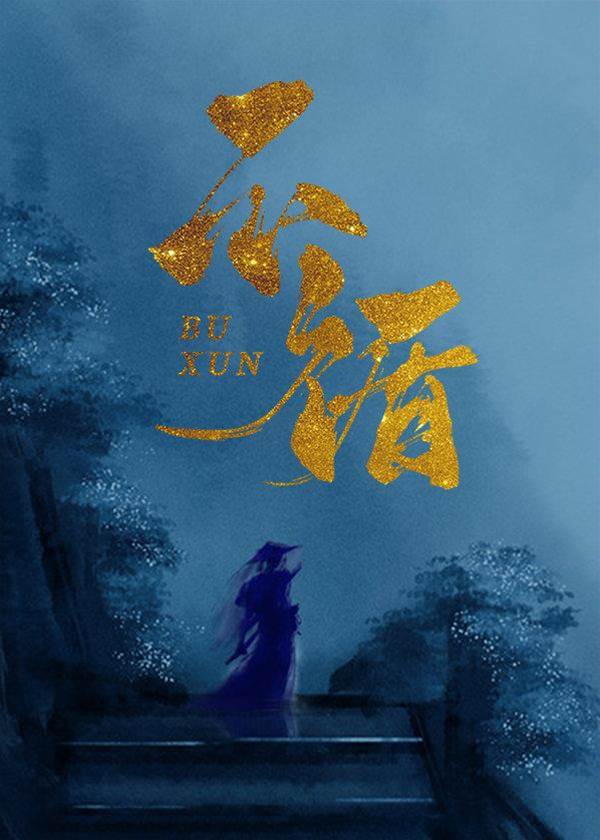《權傾裙下》 第 71 章 兜著 萬事有本王……
殿中人神各異,啞然行禮。
聞人藺袍坐下,理了理一不茍的寬袍,方含笑瞥向趙嫣道:「殿下,該讓他們開講了。」
他不是說「對酸儒舌戰並無興緻」麼?怎麼今日倒來旁聽了?
趙嫣古怪地看了他一眼,回神端坐子,頷首示意臺諫道:「陳臺丞,開始吧。」
「是,是。」主講的史臺中丞陳倫略有張地翻開講義。
不冷不燥的秋風潛殿中,吹書頁嘩嘩作響,陳倫不得不以鎮尺平講義,方清了清嗓開講。
陳倫今日講的乃為《朝綱紀要》,裏面有提到一句:「祖宗舊法不可變也。若人皆恪守,則朝綱整肅,無臣僭越。」
自去年底,依附雍王府的前任史中丞劉忠因出言誹謗東宮、妄議遷都之事被聞人藺死,李左相便提拔陳倫補了史臺中丞的空缺。故而他今日所講,也是左相李恪行那派人的「守舊」之論。
本來這也沒什麼,經筵本就是政論與經史融合的戲臺。
可偏偏今日殿中旁聽的是肅王聞人藺,大玄第一權傾朝野的「僭越之臣」,一時間門不人皆垂下目,神有些微妙。
趙嫣悄悄以眼角餘瞥了聞人藺一眼。他依舊屈指抵著額角倚坐,晏然自若,看不出什麼緒。
直到陳倫翻了一頁,打算繼續往下講時,聞人藺搭在膝上的指節叩了叩,終於開了尊口。
「陳臺丞所言之法,是為誰效勞?」
他的聲音低沉好聽,卻令陳倫無端背脊生寒,當即慎重應答:「自是為君臣百姓。」
聞人藺線一,悠然抬眼道:「夏不冬寒,前人的禮法也未必適應如今之人。既如此,為何法不隨人變?」
此言一出,滿殿嘩然。
雖然經筵之上,旁聽者有權隨時提出疑問,然肅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天子邊最鋒利的一把刀。他開口詢問祖宗禮法的合理,意義大不相同。
Advertisement
這是陛下的意思嗎?畢竟今上求仙問道,所舉亦不在禮法之。
一個月前摘星觀坍塌,老史何頤彈劾妖道世、工部貪墨,就被陛下當庭杖責,全然不顧禮法人……
一時間門講課的陳倫如置熱鍋之上,生怕答錯一句,也落得個杖責罰的下場。
「法最初之目的,為規訓人向善。只要人人恪守禮法,便可一直向善,何須變也?」
「一直向善?去年蜀川之,兵臨城下,你們的祖宗禮法可能救國?」
「這……」陳倫臉漲紅,一時語塞。
聞人藺極輕嗤笑:「經筵之上,別總講些故步自封、執而不化的東西。」
殿中眾人目相接,一時拿不準聞人藺此言深意。
另側的柳白微亦是驚訝,悄悄歪著子同趙嫣耳語道:「他怎的突然和左相的人嗆上了?雖然很解氣……」
話音剛落,就見聞人藺的目掃視過來,淡淡道:「潁川小王孫頭接耳,坐姿失儀,史記上。」
一旁立侍的史立即筆疾書,於冊中記錄「八月十六申時三刻,潁川小王孫於經筵上坐姿失儀」一句。
柳白微敢怒不敢言,憤憤然坐直。
趙嫣哭笑不得,視線與聞人藺幽深的目相,一時心疊涌。
知道聞人藺為何說這些,也知道他是在替誰開口。
今日經筵課畢,眾臣無甚心談評賞,早早就散了。
崇文殿中很快只剩下趙嫣和聞人藺在,如同往常授課那般,安靜平和。
他一直沒走,垂眸倚坐,品著掌中那盞清茶。
趙嫣想了想,起行至他邊坐下,輕輕道了句:「多謝太傅。」
聞人藺執著茶盞,睨過眼不聲道:「謝本王什麼。」
「太傅質問李相的人不懂變通,實則是在為東宮新政撐腰。」
Advertisement
趙嫣挪了挪膝頭,傾道,「那晚在紫雲閣外,我替兄長質疑周挽瀾的『開源策』太過守舊,並非真正的惠民之策,你聽到了對嗎?」
聞人藺頷首:「殿下不算太笨。」
「我本來就不笨。」
趙嫣抿小聲駁了句,又忍不住問,「太傅說這些,不怕朝臣多想嗎?」
「他們想,不妨隨他們瞎琢磨去。」
聞人藺挲著杯沿,徐徐道,「以後殿下想說什麼就對他們說什麼,不必顧忌。」
趙嫣眼眸一亮,笑道:「真的?」
聞人藺端詳著,聲音散漫低沉:「萬事有本王給殿下兜著。」
微涼的秋風潛窗扇,趙嫣耳後垂髮輕舞,黏了一縷在因怔愣而微張的上。
自回宮以來,所有人都在警戒謹言慎行、這不能做那不該做,聞人藺是唯一一個讓想做什麼便做什麼的人。
無暇去辨別此言真假,只知那一瞬,思緒的確如汐涌,溫地漱過心間門。
若說周及是約束,教克己復禮、肩負責任。則聞人藺是放縱,教如何變強、如何保護自己。
不知從何時開始,只有在聞人藺面前才會流出屬於「趙嫣」的一面。
或許,風天生就是不甘約束的。
聞人藺放下杯盞,順手捻下上的那縷耳發,問:「肚子不?」
男人的指腹一即分,沒有半分越界。
趙嫣誠實地點點頭。經筵上一坐就是兩個時辰,除了茶水外什麼吃食都沒有,的確腹中空空。
聞人藺示意殿外立侍的太監,道:「時辰尚早,去後殿吃些東西果腹。」
「吃什麼?」趙嫣問。
聞人藺看了一眼,邊有了笑意:「櫻桃山。」
趙嫣一,惱然抬眸,就見聞人藺得逞似的輕輕搖首道:「不,殿下不吃甜食。還是花生酸酪吧,有位廚的手藝不錯。」
Advertisement
「你這人,說話能不能別總斷在不該斷的地方。」
趙嫣低聲抗議,到底還是沒能拒絕酸酪的。
吸了吸鼻子,握住聞人藺遞來的臂膀,借力起,坦坦同他一起食果腹去了。
……
經過幾場秋雨的沖刷,宮牆上的濃蔭轉眼褪出了淺淡的枯黃,風一吹頗有些瑟瑟的意味。
前些天還穿著夏衫講得滿頭大汗的經筵們,今日已穿上了厚重的秋。
「我想了想,於大玄建造學館耗費巨大,我如今的確承擔不起。不過倒是能將明德館擴建,提高津補,廣納賢才,培養屬於我們自己的一支文脈。」
趙嫣下轎,與柳白微一前一後穿過長慶門,閑聊道:「我讓李浮將東宮的庫房清了清,加上華的金銀細,除了父皇賞的那些不能,其他那些變賣倒是能撐個兩年。至於兩年後如何……再看吧。」
柳白微點頭:「我如今手頭並不寬裕。不過一年足夠我斗贏郡王府的老妖婆,等著吧,將來我出資襄助殿下。」
「老妖婆」是指潁川世子妃,那個試圖去母留子、死柳白微生母的狠角。
潁川郡王年邁衰,後大事也就今年了,柳白微正和潁川世子妃爭奪郡王府掌控權。
趙嫣知他艱難,搖首道:「我不要你的錢。」
柳白微登時有些傷:「堂兄的錢也不要嗎?」
趙嫣噗嗤一笑:「不是,我不能要,這是我自己的事。你若是真想幫我,就替我尋個靠譜的渠道,我要變賣些東西,萬不能惹人起疑。」
「好吧。」
柳白微收斂起失落,應允道,「我手中有信得過的人脈,儘管給我。」
「還有,我想給明德館擢幾位同道的博士夫子,可有推薦?」
「自去年沈驚鳴和程寄行接連意外故,臨江先生悲痛嘔,沒幾個月便大去了。不過他有個門生承他志,仍在著書遊學,頗有賢名。」
Advertisement
柳白微思索道,「那名師兄我見過,和咱們一路的。只是他太過於清高自傲,閑雲野鶴慣了,恐不願拘束,回頭我替殿下去請他出山。」
「好。屆時我親自書信一封,他既重,我便以人……」
正說著,忽聞前殿一陣喧鬧。
「怎麼了?」趙嫣問。
李浮去探了探,不稍片刻回來稟告道:「回殿下,是許編修出事了。聽聞進獻了一篇大逆不道的道詞,犯聖怒,如今還在太極殿外跪著審呢。」
「許茂筠?」
趙嫣和柳白微對視一眼,便知前幾日埋下的線起作用了。
「『風摧五嶽,踏浪斬蛟龍』……這句有何問題?不是向上天請求平息水患之的意思麼?」
「你懂什麼。摘星觀坍塌,印證了『摧五嶽』,而『斬蛟龍』則暗含水患巨浪是妖龍作……」
解釋的那名文適時而止,搖首道,「這個節骨眼上,很難不讓陛下多想啊。」
「嘖,楊大人這麼一說還真……」
先前詢問的那人嘆了聲,「這下許家的仕途算是徹底完了……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見趙嫣進殿,圍攏的眾臣紛紛閉避讓。
趙嫣穿過人群停至垂簾前,就聽一個滴滴的音從東廂房傳來,帶著鋒芒的冷意道:「四公主,你現在隨本位①去陛下面前認罪,還來得及。」
「是許婉儀闖進來了。」
李浮於一旁解釋,「如今懷有龍嗣,誰都不敢攔。」
裴颯今日才解除足,剛到崇文殿便撞見此事,不由握拳向前。
趙嫣攔住了他,不聲道:「你若真想幫,就該讓自己氣起來。」
過了許久,東廂房才傳來一聲細弱但平靜的答覆:「我沒錯。」
「你說什麼?」
許婉儀的聲音陡然尖銳起來,「四公主想清楚了,他是你未來的夫君!」
「我沒錯。」
這回,趙媗的聲音大了些許,帶著一,「我隨手……放在案幾上,是他自作主張走據為己有。憑什麼要算我的錯?我不要再人支配……」
「?他你什麼!」
許婉儀低聲音,「本位要去陛下面前告你忤逆!」
說罷,許婉儀氣急敗壞地掀開紗簾,姣好艷麗的面容上有一難以消弭的猙獰狼狽。
撞見趙嫣等人,許婉儀故作優雅地理了理鬢髮,出個笑行禮,而後頭也不回地走了。
趙嫣這才開垂簾進去,趙媗獃獃坐在案幾后,眼淚打了面前的書卷,洇開一團團油墨的暗痕。
太極門下,聞人藺冷眼看著被軍在階前的許茂筠。
趙媗弱慣了,不可能有這等手段。
想起那日赴經筵,趙嫣從趙媗的東廂房出來的場景,頓時瞭然。
是小殿下的意思啊。
聞人藺淡然一笑,抬手示意,「二十杖,打完了再審。」
他說過,不管想說什麼、做什麼,萬事有他兜著。:,,.
猜你喜歡
-
完結1354 章

神醫嬌媳:寵妻狂魔山里漢
“美男,江湖救急,從了我吧!”情勢所迫,她反推了隔壁村最俊的男人。 ……穿越成小農女,長得有點醜,名聲有點差。她上山下田,種瓜種豆,牽姻緣,渡生死,努力積攢著功德點。卻不想,半路殺出個程咬金,勾走了她的心,勾走了她的身,最後還種出了一堆小包砸!
115.2萬字7.82 116552 -
完結789 章

重生王妃又闖禍了
“王爺!王妃把皇後打了!”男人冷眼微瞇,危險釋放,“都是死人?王妃的手不疼?”家丁傻眼,啥……意思,讓他打?“王爺,王妃把宮牆城門砸了!”某男批閱摺子動作不停,“由她去,保護好王妃。”“王爺,王妃被抓了!”“好大的狗膽!”屋內冷風四起,再睜眼,某王爺已消失在原地。自那之後,某妃心痛反省,看著某男因自己重傷,她淚眼婆娑保證,“夫君我錯了,下次絕對不會這樣。”然——好景不長。“王爺,本宮又闖禍了!”
138.1萬字7 264397 -
連載1606 章

有了讀心術後王爺每天都在攻略醫妃
21世紀醫毒雙絕的秦野穿成又醜又不受寵的辰王妃,畢生所願隻有一個:和離! 側妃獻媚,她各種爭寵,內心:我要噁心死你,快休了我! 辰王生病,她表麵醫人,內心:我一把藥毒的你半身不遂! 辰王被害,她表麵著急,內心:求皇帝下旨,將這男人的狗頭剁下來! 聽到她所有心聲的辰王憤恨抓狂,一推二撲進被窩,咬牙切齒:“愛妃,該歇息了!” 半年後,她看著自己圓滾滾的肚子,無語痛哭:“求上天開眼,讓狗男人精儘人亡!”
146.5萬字8 840800 -
完結16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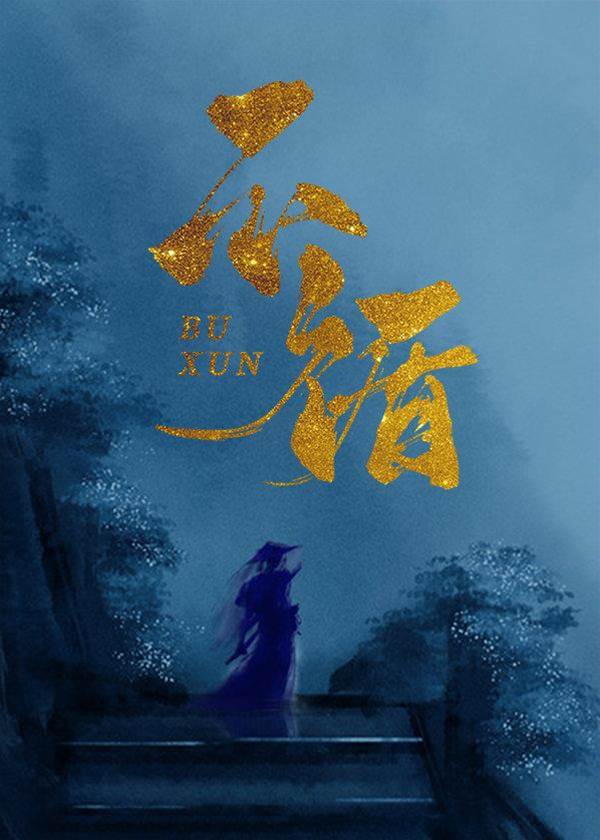
不循(重生)
邵循是英國公府的嫡長女。 父親是一品公侯,母親是世家貴女,宮裡的淑妃娘娘是她姑姑,太子之位的有力競爭者三皇子是她表哥。 人生中唯一的不足就是生母早逝,繼母不親,原本應該榮華富貴不缺,波瀾壯闊沒有的過完一輩子,誰知一場夢境打破了一切—— 邵循夢見自己的堂姑為了給兒子剷除對手,犧牲侄女的名節用以陷害風流成性的大皇子,害得自己清白盡毀,只能在鄙夷中被大皇子納為側妃。 大皇子風流成性,大皇子妃善妒惡毒,邵循醒來後生生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誰知這夢做的太晚,該中的招已經中了,無奈之下決定拼死也不能讓噩夢成真,為了躲開大皇子,慌不擇路的她卻陰差陽錯的撞進了另一個人懷裡…… * 邵循清醒過來之後跪在地上,看著眼前繡五爪金龍的明黃色衣角,真的是欲哭無淚—— 這、這還不如大皇子呢! * 1雷點都在文案裡 2年齡差大 3請原諒男主非c,但之後保證1v1
49.3萬字8.33 45845 -
完結137 章

招魂
-落魄的閨閣小姐X死去的少年將軍-從五陵年少到叛國佞臣,徐鶴雪一生之罪惡罄竹難書。即便他已服罪身死十五年,大齊市井之間也仍有人談論他的舊聞,唾棄他的惡行。倪素從沒想過,徐鶴雪死去的第十五年,她會在茫茫雪野裡遇見他。沒有傳聞中那般凶神惡煞,更不是身長數丈,青面獠牙。他身上穿著她方才燒成灰燼的那件玄黑氅衣,提著一盞孤燈,風不動衣,雪不落肩,赤足走到她的面前:“你是誰?”倪素無數次後悔,如果早知那件衣裳是給徐鶴雪的,她一定不會燃起那盆火。可是後來,兄長失踪,宅田被佔,倪素跌落塵泥,最為狼狽不堪之時,身邊也只有孤魂徐鶴雪相伴。 伴她咬牙從泥濘里站起身,挺直腰,尋兄長,討公道。伴她雨雪,冬與春。倪素心願得償,與徐鶴雪分道揚鑣的那日,她身披嫁衣將要嫁給一位家世,姿儀,氣度都很好的求娶者。然而當夜,孤魂徐鶴雪坐在滿是霜華的樹蔭裡,看見那個一身紅的姑娘抱了滿懷的香燭不畏風雪跑來。“不成親了?”“要的。”徐鶴雪繃緊下頜,側過臉不欲再與她說話。然而樹下的姑娘仰望著他,沾了滿鬢雪水:“徐鶴雪,我有很多香燭,我可以養你很久,也不懼人鬼殊途,我們就如此一生,好不好?”——寒衣招魂,共我一生。 是救贖文,he。
50.1萬字8 2237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