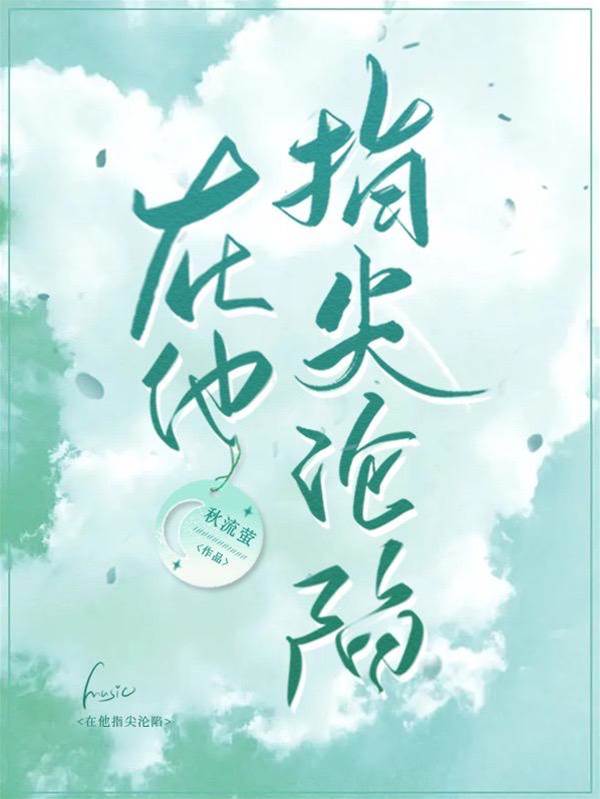《絕對臣服》 第55章 第 55 章
姜濃被請過來的路程也就十來分鐘,進了調暗極的室,先是聞到空氣中太過濃郁的熏香味,有哮,呼吸只能極輕著,很快就看到有個過百高齡的老太太端坐在紅木貴妃榻上。
著了雍容華貴的刺繡旗袍,戴的是祖母綠寶石首飾,耳環沉甸甸地襯著臉旁,和藹的笑容全無,儀態像極了舊時閨中的富家太太。
而林不語就坐在旁邊椅凳上,恰好說起了要去英國留學的事。
老太太聽了,倒是很贊進修:“趁著年輕多出去走走,不像我,老了只能困在這里。”
只是林不語去讀書,和傅錦明三月春結婚的事就得耽擱下來,是來求老太太一句恩準的,眉眼帶,把漂亮的話也說得冠冕堂皇。
兩人這邊聊著,卻故意將姜濃晾在原地,就這般尷尬站著。
直到管家見時機差不多了,趁老太太說話累了,端起茶的功夫就上前:“人來了。”
老太太抿了口茶水,跟現在才看到屏風旁安靜站著一個人影似的,老花眼了卻不開亮的燈,瞇起瞧個半響,慢悠悠說:“這臉長得還標志。”
姜濃和的眉眼沒有喜悅緒浮,知道大費周章請人過來,自然不是為了看一下臉。
室寂靜不到三秒。
老太太將茶杯擱在桌旁,突然就發作了:“你和季如琢是什麼關系?”
這話引得姜濃抬起卷翹的睫,許是眼中過于坦然剔,并沒有半點驚慌失措:“他是我多年的朋友。”
老太太沒說信不信,只是將幾張照片不輕不重地扔在了腳下。
室用的東西極貴,就連手工古董地毯都是金線的,照片散在暗紫的毯上,姜濃垂眼,印視線的都是一些醫院時和季如琢獨被拍的畫面。
Advertisement
拍這個的人角度刁鉆,換誰看了都會心生誤會。
何況是老太太這種出就重規矩的人家,原對姜濃的普通出就諸多挑剔,加上林不語送來這些,瞧了差點沒當場摔碎茶杯,聲是沉著的:“你在電視上搞的那些拋頭面的事,我也懶得手,免得你們這些小輩要在背后罵我食古不化,盼著我早點去見列祖列宗。”
林不語花容失:“老祖宗!”
傅老太太這把年紀了,早就對生死看淡,抬手制止說,那雙細長的眼從始至終盯著姜濃一人:“但是你要跟別的男人不清白,讓傅家沒了面,就算是青淮來了也護不住你。”
姜濃垂在側的手無聲地,氣氛僵持許久,面對老太太犀利的質問,只是冷靜的解釋和季如琢的關系,未了,眼尾的余淺淺掠過一旁的林不語,啟又說:“這幾張照片上,傅青淮都在場,老太太要是不信,可以讓管家去這家私人醫院調監控,我想不會那麼巧,監控也沒了呢。”
林不語臉微僵,低頭喝茶不說話。
姜濃是毫不懼老太太幾分審視的眼神,笑了笑:“訓斥的不該是我。”
放眼去傅家三子,都是以老太太或老祖宗來尊稱,第一次聽到這個陌生稱呼,老太太怔神了下,很快皺起眉頭表示不喜:“我還錯了?”
姜濃音清冷冷的,看著眼前這個連喝茶都要微微上翹著小拇指,完弧度把控的就跟拿尺子測量出來的,極講究規矩的老太太:“您該訓斥的是搬弄是非之人,深宅大院最忌諱的便是這種小人做派,來告狀,卻只想憑這區區幾張照片……”
“姜小姐不愧是做新聞的,這口才我佩服!”
林不語打斷了姜濃的話,聲音幽幽地:“你行為不端正,被拍到和季如琢不清不楚,卻反倒要求老太太去罰揭發你的人,我看這傅家祖宗定下的規矩早晚要改姓姜了。”
Advertisement
老太太被這一句不端正給打回神,差點被姜濃給繞了進去,臉不太好看。
林不語側頭看,聲音輕卻充滿了狠毒:“老祖宗,您就發善心先別為了這事大干戈,我看不如讓姜濃跟那季如琢斷了來往,不就杜絕了后患麼……”
話聲落地。
老太太重新看向后背直了站在原地的姜濃,語氣冷淡生疏:“就這麼定吧,日后你不要跟季如琢見面了。”
姜濃臉頰被烏錦的發襯得有些蒼白,卻倔強地抬起頭:“我做不到。”
老太太漫不經心地轉著手上的翡翠玉珠,纏繞著皺紋的拇指說:“做不到就去外頭跪著,什麼時候跪明白了再來跟我說。”
室所有人,包括一旁穿著黑長袍的老管家都沉默著,無人敢出聲。
傅家上下皆知,老祖宗最不喜忤逆自己的晚輩,若是要倔犟,就把你這一倔骨頭連帶拔的出來,扔出去喂狗。
姜濃膝蓋才初愈不久,這要跪,傷勢加重不說,連主母的面都盡失了。
林不語笑看著,姿態也越發高高在上。
靜了許久,姜濃指尖在側的料上泛起淺淺嫣,面上卻不顯緒,就當要開口時,室外傳來了另一聲,聽著音猶如在青玉盤撒下一把珍珠般清澈,又摻和些溫,輕輕撞在場的人耳朵里:“檀香味也太膩了,快開窗通通風吧。”
“誰來了?”老太太先問。
不等老管家回答,眾人只見屏風那邊,有個握著折扇的孩兒步子很慢走進來,穿著胭脂的紅,像是藏寶閣里古畫走出來的,本就不俗的臉在偏暗的線里像染上一抹艷似的,即便年紀還小,卻依稀能看出將來必定是個驚艷全城的大人兒。
老管家回過神,立刻低語:“是泗城賀家族長的。”
Advertisement
老太太一聽是賀家族長的金枝玉葉,也沒空管姜濃了,立刻朝這個小貴人兒招招手:“瞧著真討人喜歡,快過來,告訴老祖宗你什麼名字?”
“我賀南枝。”
孩兒說著,卻不往老太太邊走,自然地停在了姜濃的邊,對一笑。
姜濃不識這位人兒,卻知道泗城賀家的族長地位尊貴,與妻多年只養育一,是比自稱是家中掌上明珠的林不語還要真正備千萬寵的存在。
也難怪老太太看到,兩眼都亮了。
賀南枝的到來,讓原本僵持住的氣氛瞬間化解,無人再提先前的事。
而也輕輕環住了姜濃微涼卻的手,沒有繼續站著,朝旁邊的沙發大膽坐。
這看的林不語眼底泛起警覺敵意來,卻無法話進去。
因為老太太專注都在了賀南枝上,問起:“你父親來了?”
“爸爸不出門。”賀南枝似嫌室的檀香太濃,用折扇輕輕遮著鼻說:“我是跟謝忱岸來瀝城找小觀音姐姐的,順便來這兒拜訪一下。”
不用找話題聊,老太太點點頭:“賀族長居慣了,上次來傅家給我賀壽,都是十年前的事了……我之前好像聽了一耳,你是學戲曲的?”
賀南枝的母親是娛樂圈著名影后,忙著拍戲,而自是跟著父親旁長大的,孩時,就整天日的在賀宅跟族中一些老輩的聽著戲曲,后來逐漸起了興趣,就被送去請名師教學了。
老太太這一問,林不語總算能上話說:“賀小小姐不如唱一段?”
賀南枝細的手指攥著折扇輕晃,雖有扇子擋著,但是姜濃離得近,還是看到給了個冷眼過去,淡淡嫣的抿著說:“今天沒開嗓,不唱。”
Advertisement
“……”
這是賀家的金枝玉葉,父親年紀極輕時就位列族長之位了,且賀氏家主也就是親伯父只有一名私生子,給撐腰的幾個男人都不好惹,是有囂張資本的。
林不語即便不服氣,也要忍著微笑。
賀南枝才不管林不語怎麼想,子綿綿的朝姜濃的肩頭靠著,一邊回老太太不停地問話,一邊又悄悄地對說:“我是按分鐘計費的。”
姜濃纖長垂落的眼睫茫然輕眨幾許,似乎被暗示到了。
……
待了近乎半個小時,老太太年紀大了有點疲倦,揮揮手讓們都下去。
賀南枝是第一個起的,牽著姜濃的手就往外走。
林不語只能跟在后頭。
等沒了外人,老太太被扶著進里屋,略有點可惜:“賀家那小人兒我瞧著喜歡,就是年紀小了,先前不適合訂下,不然這份配青淮,也是配得起的。”
老管家彎著腰低語:“老祖宗糊涂啊,這金枝玉葉早就被謝家給訂下了。”
“謝家?”
“與謝家未來繼承人謝忱岸是青梅竹馬,自一起長大的,謝家主早就選了做兒媳,聘禮都備了十來年了,就等著長大了進家門呢。”
*
出了院子。
姜濃讓賀南枝到前面等自己,停下,微微側眸看向林不語。
這里沒了旁人,誰都沒有繼續裝下去。
林不語更是眼神恨到了骨髓程度,只是做夢都沒想到,上次兩人在新聞臺初見,份地位還懸殊著,如今倒是姜濃生生一頭。
姜濃站在庭園的尾竹下,眉目被細碎的碧影襯得極為清冷:“林小姐,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雖等得起,卻也不愿意等這一時半刻了。”
林不語冷笑:“你什麼意思。”
“你想借去英國留學來避開與傅錦明三月春結婚的事,又不甘看我在傅家過的稱心如意,便想借老太太的權威來教訓我。”姜濃心思清又聰明,一眼就看破了林不語費盡心思布的局。
旁的可以忍,但是林不語千不該萬不該拿季如琢做文章。
靜幾秒,點破,啟繼續說:“多謝林小姐讓我親會到原來傅家……規矩是能掌控一個人的自由。”
林不語越發聽的不對勁,連帶后背都發涼。
“你想做什麼?”
姜濃微側過臉,被淡淡的碧籠罩著,表淡笑卻沒有溫度:“你這麼管傅家的事,英國留學就不要去了,三月春嫁進來再說吧。”
“姜濃。你以為能做主?”
林不語氣笑,去英國留學只是避婚的借口,是林家和傅錦明想出來的對策,先去進修學業個四五年在回來,到時婚約的時被淡忘,再去求老祖宗解了。
說得通俗易懂點,就是去避風頭的。
姜濃何嘗不知,才會用這個還擊,清的音不變:“你在老太太面前有一句話提醒道我,傅家的規矩改姓姜也未嘗不可,日后這個家,下一任乃至下下一任家主,都是與我脈相連的,規矩沒改之前,我的話也是規矩。”
看著林不語姿態再也高高在上不起來,結束談話之前,輕描淡寫般落下一句:
“婚約如期舉行,今后林家也不會給你提供一分錢的生活來源,林小姐,傅家老宅還是養得起你的,就安心待在里……”
待在這里看姜濃臉度日?
這比活剮了林不語還痛苦,妝容致的臉孔也變了:“我林家才不會聽你的。”
姜濃細細的高跟鞋略停一秒,卻沒回過頭:“林家會聽的。”
林不語即便在家中是掌上明珠,卻有個不爭的事實,提前是能給家族帶來利益。
姜濃往前走,面對一抹胭脂站在走廊上的賀南枝時,眉眼的冷意才褪去,覆上了淡淡清的笑:“方才謝謝你來救場。”
賀南枝要不來的話,堅持不愿跟季如琢劃清界限,必定是要惹怒傅家老祖宗,被罰去外面跪上一跪的。
不過賀南枝沒有邀功,搖晃著手中折扇說:“是青淮哥哥請我來的,他說老祖宗好面子,他要來的話,指不定得火上澆油,我來,最合適不過了。”
自古“婆媳”問題就很難理,哪怕老祖宗不是正兒八經的婆婆。
傅青淮用意很深,也不想姜濃日后在這傅家,徹底得罪狠了老太太,但是賀南枝就沒這方面顧忌,重新去挽起姜濃的手,皺了皺秀氣的鼻:“傅家祖宗規矩真大,我不喜歡。”
猜你喜歡
-
完結324 章

軍閥權寵:大帥,你過來!
民國年,烽火亂相生,軍帥各領占地為王。 蘇城被攻陷那日,喬綰像個貨物,被獻給西北三省的新主人。 傳聞中,季九爺冷血陰狠,克死三房夫人,是天煞孤星。 季世延自垂花門下溜達出來,自墨鏡余光里撩了一眼.... 春光明媚,少女眉目如畫,身段娉婷,像朵飄零無依的菟絲花。 季九爺舌尖頂了頂腮,招寵般抬了抬手,矜貴優雅。 多年后,喬綰站在垂花門下,沖著院子里跪了一個正午的挺拔身影,嬌慵喚道,“大帥,你過來。”
60.2萬字8 26453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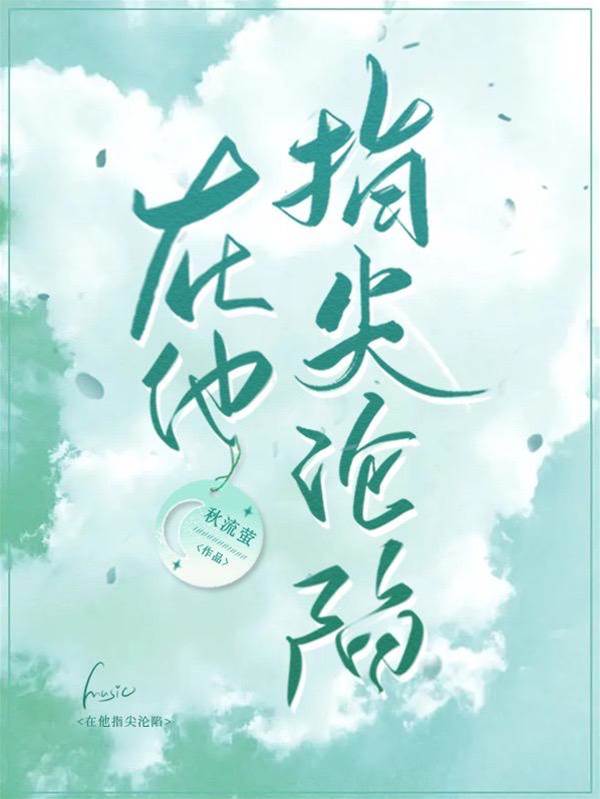
在他指尖淪陷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跡,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 -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隻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麵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子。閱讀指南:久別重逢,身心幹淨,冬日小甜餅。
20.2萬字8 20496 -
完結222 章

許愿
虞粒喜歡程宗遖,從14歲開始。 那天,他在舞臺上彈奏貝斯,張揚肆意。只是驚鴻一瞥,她再也沒能忘卻。 幾年後重逢,他已成爲商場大亨。西裝革履,氣質矜貴凜然。 她終於按耐不住心中愛慕,鼓起勇氣上前搭訕:“程叔叔,你這個年紀的人,應該不用微信吧?” 他饒有趣味看她兩眼,將手機遞給她:“加上看看不就知道了?” 18歲生日那晚,她從家裏跑出來,失魂落魄地撥打他的電話:“程叔叔,我沒有地方可以去了。” 他聞訊而來,揉揉她腦袋,憐惜中透着蠱惑:“跟我走嗎?”
33.7萬字8 3961 -
完結199 章

瀝青
文徵剛住宋家那年,宋南津去美國長居。人爸媽在國外開企業,文徵被他姑母收留,兩人沒什麼交集。 後來宋南津回國,兩人被迫共居一室。 文徵知他不好相處,不敢招惹,處處小心。 可後來才知道,其實宋南津心裏想她想很久了。 男人慢條斯理繫着袖釦,聲音溫柔又淡薄:“文徵討厭我,爲什麼勾引我。” - 在宋南津面前,文徵向來處於一個弱勢地位。 他是她在宋家的哥哥,文徵從不敢隨便僭越。 轉變皆來自那天。 所有人眼裏井水不犯河水的二人依舊安然做自己的事,天際暗淡,文徵無意和宋南津在逼仄過道相遇。 客廳傳來家裏其他人的講話聲。 文徵從他身旁經過,手指卻悄然被他勾住:“這次準備和他談多久?該分了,文徵。” 和男友分手的夜,他們最後攤牌,宋南津說要結婚,文徵冷靜表示自己不太能無縫接軌。 男人指間掐煙,口吻淡然。 “我要你,你覺得自己還有選擇嗎。” - 文徵貧瘠的世界觀裏,隨遇而安是她的生存法則。 而宋南津是衆星拱月的目光焦點,資本子弟。 他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可那些她孤獨又沉默的歲月。 他也想成爲她的全世界,爲她依託。
33.1萬字8.25 612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