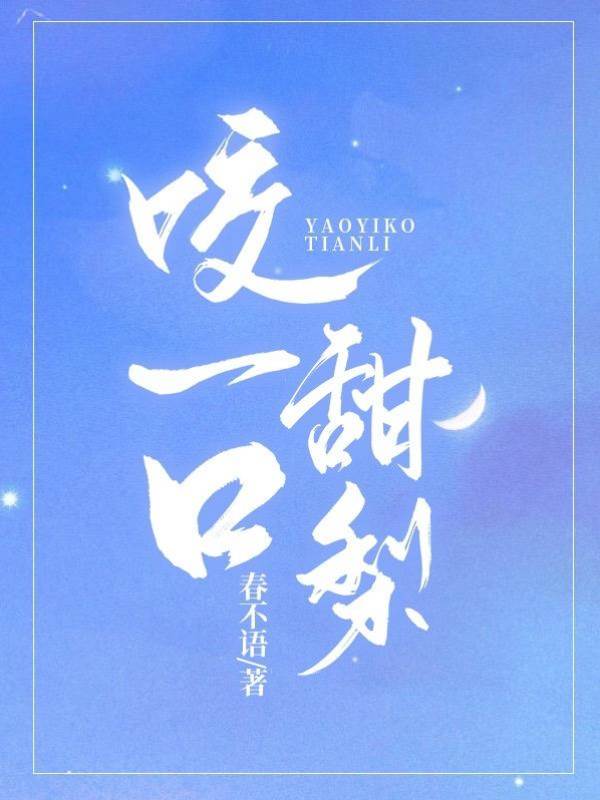《小濃情》 35
上育課大家都沒穿外套,料略顯單薄,那生在他的下微微抖,有點躲開的意思,低語,“我,我知道了老師。”
那老師慢慢鬆開手,又如法炮製地糾正了其他幾個生,連男生都注意到了,一直站在前麵喊口號的育委員見狀索直接跳過了兩個節拍,“4–––4,停!”
連續做了兩個熱運後,那老師越聽越不對勁,駐足抬眼質問育委員,“你是不是喊拍了?”
育委員也是條漢子,沒有,還指向全班,“老師不信你問他們。”
全班當然一致站在他那頭,齊齊高喊,“對!沒有!”
那老師也無可奈何,隻得從生堆裏走回隊伍前,“行吧,那開始測。”
生們這才稍稍鬆了一口氣。
他立在前麵捧著個名單冊宣布,“第一個測試容是坐位前屈,生先來,男生先站一邊等會兒,可以自由活。”
生們麵麵相覷,有不大好的預,一時間無人所,而他已經吹了一聲口哨,“男生,原地解散。生,跟我過來。”
男生們便四下散開,隻剩生心事重重地跟了過去。
Advertisement
王驍歧被周鄴他們幾個圍住,有人問去不去打會兒籃球,王驍歧卻罕見地沒做聲,而是從材室門口隨手拿了一副羽球拍丟給周鄴一隻,並順勢揮了兩下,耳邊瞬間刮起一陣“呼呼”聲。
他,“今打羽球。”
他不去打籃球,其他男生也覺得沒意思了,都留在原地附近開始打起了羽球。
生那邊等測試儀到位,也開始測了,按照學號來,第一個是許意濃。
眾目睽睽之下,走過去了鞋,踩上了墊子坐了下去,兩直撐靠到那儀的平麵上。
那老師,“開始吧。”
於是雙腳平撐在測試板上,兩手筆直地抵在遊標上,上一個前屈,開始一點一點地往前推那遊標,不論是姿勢還是作,從頭到尾都堪稱完。
可剛推到一半,那老師忽然停。
“姿勢錯誤,雙不能彎曲,重做。”
生們都一愣,這樣的都不合格要重做嗎?
許意濃蹙了蹙眉,仰起頭,“老師,我剛剛沒有彎。”
卻是徒勞,他非認定就是彎了,“我一直站這兒仔細看著呢,怎麽沒彎?”
Advertisement
許意濃抿了抿,隻能把遊標拉回重做,這次把雙刻意繃直,重複著先前的作緩緩屈推著油標向前。
原本站在一旁的老師突然蹲下,手按住的雙,仿佛在耳邊話,“你看,剛剛還不承認自己彎。”他邊按手掌還邊在大側了兩下。
許意濃整個人嚇得一僵,一下彈開,險些就要站起來,測試因此再次半途而廢。
可那老師卻不為所,像什麽都沒發生似地抬頭提醒其他人,“你們記住啊,每個人隻有三次機會,可別被自己浪費掉啊。”又看一眼,“你已經浪費兩次了。”
許意濃暗自咬著牙,上下直打哆嗦,想到他剛剛的行為舉止心底酸水直冒,泛起一陣惡心。
萬萬沒料到這種平日新聞裏出現的事有朝一日會發生在邊以及自己上,這樣的人簡直枉為人師。
甚至想直接撕破臉一了百了,可那人竟還恬不知恥地催,“趕的,你後麵還有其他同學要測試,都在等你。”
話音一落,他又俯不知所畏地朝手而來。
許意濃眼看那隻魔爪再次襲向自己,腦中空惘一片,心跳如鼓,屏著呼吸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魚死網破。
Advertisement
那邊周鄴打出了一個高球,男生們都仰著頭聚會神地盯著那隻羽球劃過長空,周鄴對麵的王驍歧忽而側了側,舉著球拍的右手肘已微微折起,幾秒的時間他似已經據高度目測好了距離,他長稍稍往後退了幾步,卡好落球時機整彈跳起,結實的右手臂如甩出鞭子般狂勁有力,抬手就揚起一記大扣殺。
羽球與球拍網擊起強烈的撞,產生了“砰——”地。
周鄴簡直連跑帶跳,可那球跟流星似地從頭頂一閃而過,他本接不住,還摔了個大跟頭。
倏地,許意濃聽到“嗖”地一聲,一個看不清的白點如風般從而降,速度飛快。
“啪——”一下,不偏不倚地砸在了那老師的左側臉頰上,而後掉落在地上,滾了一圈才停下。
在場的生定睛一看,才發現是一隻羽球。
那老師臉上當場留下了一記紅印,猶被人了一掌,一看力道就不。
他惱怒地朝附近打羽球的男生堆裏看去,眼睛雖被墨鏡遮擋,卻也能到他的氣勢洶洶,他朝那邊高喝,在學生群裏探究著“肇事者”,“誰?!是誰打的球?!”
Advertisement
不遠,王驍歧長佇立,男生堆裏異常醒目。
長長的羽球球拍桿在他右手中微,下去了幾節,最終球柄被困在他手心,他坦坦地,“我打的。”
整隻球拍在他手中懸空而掛,隨風輕,把他接下來的話也一並吹來。
“扣殺沒控製住力道,偏了。”他從場的亮徐徐而來,如同向而生,聲音也人畜無害。
“老師,你沒事吧?”
猜你喜歡
-
連載1965 章

左先生寵妻百分百
她是能精確到0.01毫米的神槍手。本是頂級豪門的女兒,卻被綠茶婊冒名頂替身世。他本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專情總裁,卻因錯認救命恩人,與她閃婚閃離。他從冇想過,有一天,她會用冰冷的洞口指向他的心臟。“這一顆,送你去給我的孩子陪葬!”她扣下食指……
164.4萬字8 184413 -
連載2383 章

錯嫁纏婚:首富老公乖乖寵我
為了救父親與公司,她嫁給了權傾商界的首富,首富老公口嫌體正直,前面有多厭惡她,后來就有多離不開她——“老公寵我,我超甜。”“嗯......確實甜。”“老公你又失眠了?”“因為沒抱你。”“老公,有壞女人欺負我。”“帶上保鏢,打回去。”“說是你情人。”“我沒情人。”“老公,我看好國外的一座城......”“買下來,給你做生日禮物。”媒體采訪:“傅先生,你覺得你的妻子哪里好?”傅沉淵微笑,“勤快,忙著幫我花錢。”眾人腹誹:首富先生,鏡頭面前請收斂一下?
219.6萬字8 148192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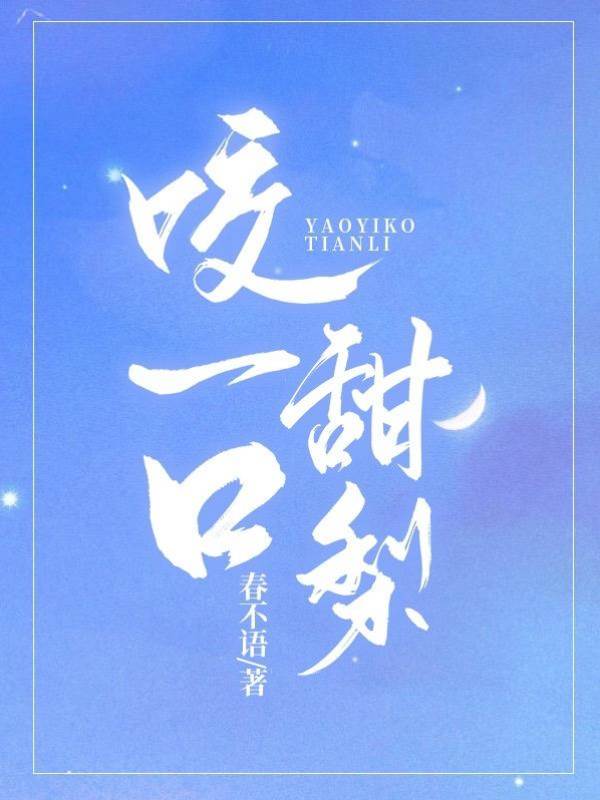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73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