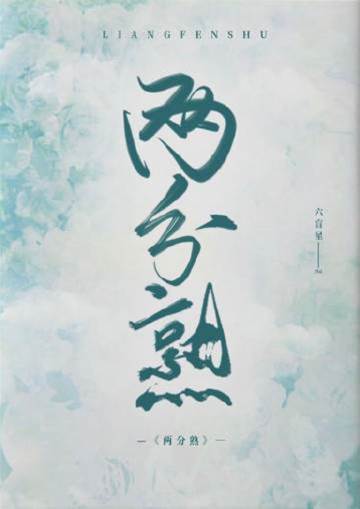《南城》 067
下午兩點,從申城出發的火車歷經數小時的行程之後,終於穩穩停在了杭城車站。
陸鐸穿著一白西裝站在一等車廂前的站臺上,等啊等,幾乎所有乘客都走了,就在陸鐸懷疑自己是不是看眼了的時候,兩個黑壯漢突然跳下車,分別守在一側,接著,一條出現在視野,白的細高跟鞋,潔修長的細膩如瓷,再往上,是件白的裹短。
陸鐸只覺得眼前一亮,在杭城待了半年,他已經很久沒見過這麼大膽的扮相了。
他繼續打量對方。
人戴著白小洋帽,低頭下車,眼睛被帽檐擋住,塗玫瑰的紅艷人,與帽子上的紅玫瑰花相輝映。
確認了份,陸鐸走上前,摘下帽子,十分紳士地招呼道:「是溫小姐嗎?我是東盛紡織廠的副經理,陸鐸,電話里與您流過。」
溫霞抬起頭,出一雙漂亮的丹眼,眼角微微上挑,只是靜靜地看過來,便有種嫵的味道。
饒是見過中外人無數,陸鐸也失神了幾秒。
溫霞微微一笑,大方自信。
陸鐸回神,誠心地讚道:「溫小姐比熒幕上更漂亮。」
「謝謝,陸也比報紙上的照片年輕俊多了。」溫霞調侃著說,同時朝陸鐸手。
人的小手若無骨,紅艷的指甲油襯得勝雪,陸鐸卻沒有再失態,禮貌的一握便鬆開手,做了一個請的姿勢:「我的車就在外面,我先送溫小姐回酒店休息,傍晚再設宴款待,如果溫小姐肯賞的話。」
溫霞笑靨如花:「陸客氣了,能同您與三爺共進晚餐,是我的榮幸。」
聽提及舅舅,陸鐸只是笑笑,並沒有解釋什麼。
上了車,陸鐸與溫霞坐在後座,陸鐸口才極好,尤其擅長接人待,一路民俗風介紹下來,再恭維一番溫霞的貌與表演才能,逗得溫霞笑了一路,不知道的,還以為兩人是久別重逢的故友。
Advertisement
陸鐸一直將溫霞送到酒店門外,然後才告辭。
佈置奢華的酒店房間,溫霞走到窗前,挑開一窗簾,目送陸鐸駕車離開。
作為一個十七歲出道、在影視圈爬滾打三年的明星,溫霞常年遊走於際場,太多的男人覬覦的,使出各種手段對展開追求,男人見多了,溫霞眼睛也毒了,所以經過剛剛的短暫相,溫霞非常確定,的人魅力,沒能征服陸鐸。
不過,陸鐸也不是此行的目標。
想到申城頂層圈子裏無人不知卻鮮有人真正見過其容貌的顧三爺,溫霞興地了下紅。明星,呵,看著鮮,其實背後一堆齷蹉,有背景後臺的天之驕還好說,像這樣出貧寒的,幾乎每一個往上爬的機會,都是在男人床上換來的。
時至今日,溫霞不必再陪小人了,但想徹底穩住自己的地位,還需要一位經濟實力足夠雄厚的金主。這兩年溫霞一直在,有過兩次機會,可惜都沒能抓牢,好不容易等到顧三爺主朝拋出橄欖枝,溫霞咬住,告訴自己一定不能再錯過。
.
顧家別墅,陸鐸一回來便去向舅舅報告他與明星見面的經過。
「我怎麼覺得,今晚很想見你?」坐在書桌對面,陸鐸沒正經地開玩笑,「舅舅,你這樣算不算深巷裏的酒,雖然你不出去,但架不住別人聞著味兒往你這兒趕?」
顧懷修不想浪費時間陪外甥科打諢。
「那你晚上去不去?」陸鐸正問。
顧懷修冷冷看了他一眼。
陸鐸懂了,閉上,識趣地走出書房,並從外面帶上門。
傍晚五點,陸鐸準時去酒店接溫霞。
他一個人來的,溫霞猜測顧三爺應該是在酒樓等著,笑盈盈地上了陸鐸的車。
Advertisement
人人都知道山居客是杭城最好的酒樓,這頓晚餐自然訂的這裏,不過陸鐸有點心虛,下車后一直張地盯著旁邊的麵館,擔心清溪出來撞見他與溫霞。舅舅心大,陸鐸心可細著呢。
幸好有驚無險。
酒樓夥計將兩人引到雅間。
溫霞趁夥計推門的時候,不著痕跡地看向裏面,卻一個人影都沒瞧見。
夥計走了,陸鐸請溫霞落座,主解釋道:「不好意思,我舅舅脾氣古怪,不喜歡應酬,今年杭城舉辦元宵煙花大會,舅舅也拒絕了主辦方的邀請,寧可一個人在家看書下棋……總之怠慢之,還請溫小姐多多包涵。」
溫霞笑容不改,善解人意地道:「三爺深居簡出,我早有耳聞,沒關係的。」
陸鐸再次表示歉意。
溫霞端起茶碗,眼裏掠過一霾,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果連顧三爺的面都見不到,魅力再大也沒用啊!
溫霞很發愁。
陸鐸佯裝不知,風度翩翩地陪吃陪聊,飯後還陪溫霞去南湖邊上逛了一小時。
溫霞只有五天的空閑,來杭第二天,陸鐸便將溫霞請到紡織廠,先簽代理合同。
顧懷修給的代理費非常可觀,溫霞開心地簽了字。
第三天,陸鐸請來杭城日報商業板塊的大牌記者,先拍照片,再做採訪。
採訪結束,今年代理方面暫且就沒有溫霞的事了,陸鐸禮貌地詢問溫霞返申時間,他願意幫忙購買火車票,並送溫霞登車。
溫霞不甘心就這麼回去,故意多逗留了一日,想找機會與顧懷修「偶遇」,沒想到顧懷修要麼不出門,出門就是去汽車廠,路上哪裏都不停,本沒有適合偶遇的機會。
但,溫霞畢竟是混明星圈的,知道有時候緋聞也夠用了。
夜幕降臨,溫霞打電話給自己的經紀人,悄悄地提點了一番。
Advertisement
.
清溪這幾天過得很焦躁。
一是食節的評比結果還沒有通知下來,二是顧懷修給畫了一個大餅,卻理不清切合實際的步驟。食節的事只能等結果,關於徐慶堂的發展,清溪去找祖母商量。徐老太太得知孫竟然還妄想將徐慶堂發展杭城第一酒樓,當場就笑了,勸孫別好高騖遠……
在祖母這裏得不到建議,清溪發愁兩日,又去找師父楊老商量。
不做面了,休養半年的楊老明顯胖了一圈,看起來也年輕了幾歲。
聽完徒弟的抱負與煩惱,楊老一邊修剪盆栽一邊認真地想了想,十幾盆花都剪完了,楊老將徒弟到堂屋,思索著道:「徐慶堂的名聲已經起來了,要我說啊,食節結束后,你應該先招個做面的師傅,麵館生意給他,你集中力練好廚藝,自己練好了,再收徒弟教導,等廚子、錢都有了,就可以準備重開酒樓嘍。」
清溪也有想過招人,但擔心對方的廚藝不行,麵條味道變差,壞了徐慶堂的招牌。
楊老正閑的沒事幹呢,聞言擺擺手,笑道:「你安心準備食節,師父幫你個師弟,等他能出山了,再去麵館接替你。」
「師父真好!」清溪高興地跑到楊老後,孝順地幫師父肩捶背。
解決了一件大事,清溪神采飛揚,卻沒料到第二天早上,一大坨烏雲就了過來。
當時清溪正在廚房忙碌,孟進在外面端碗收碗,一位客人走了,丟下了看完的報紙,孟進見報紙乾乾淨淨的,微紅著臉將報紙送給了管賬的小蘭。
小蘭喜歡看報紙,在第二頁看到一整版關於東盛紡織廠的報道,居然請了當紅的明星溫霞拍廣告,服還那麼漂亮,小蘭由衷地替三爺高興。以前偏向顧明嚴,但最近顧明嚴不怎麼來了,小姐似乎越來越喜歡三爺,小蘭就跟著改了陣營。
Advertisement
想著休息時再把報紙給小姐看,小蘭繼續往後翻,到了娛樂版,驚見一行刺眼的標題:溫霞來杭,顧三爺親自接人。
標題下面的報道中,配了一張醒目的照片,大酒店門前,陸鐸一白西裝站在車門旁,溫霞穿著緻的旗袍,曲線玲瓏,微微低著頭,好像在與車裏的人打招呼。人容貌姣好,眉眼含,如與.人見面。
三爺在車裏?
小蘭湊近報紙,可惜照片並不是特別清楚,黑的車窗更加模糊了裏面的形。但溫霞的表證明裏面肯定有人的,而一旁的陸鐸,足以讓所有悉舅甥倆的人猜出那人的份。
心沉重,小蘭看向廚房。
清溪戴著口罩,切菜面,忙得熱火朝天。
小蘭難極了,地將報紙藏了起來。
藏了,徐宅,看到報紙的徐老太太卻然大怒,孫一回來,便孫過來看報紙!
好個顧老三,上信誓旦旦的,還說什麼將來生兒生都姓徐,這還沒親的,他就跟不正經的明星勾搭上了!徐老太太既生氣,又到慶幸,慶幸自己沒有托顧老三幫們娘幾個報仇,沒把孫送進火坑。
清溪看著報紙上的照片,因為溫霞的燦爛笑容,雖然沒看見顧懷修,卻好像也看見了他。
不控制地,清溪飛快地比較了下與溫霞。
穿著旗袍、塗著口紅的溫霞,艷人,清溪便又想起,顧懷修送過口紅,也想看穿旗袍來著。但拒絕了那管口紅,更沒有給他看自己穿旗袍的樣子……
孩忍不住浮想聯翩,各種猜測,徐老太太看在眼裏,冷哼道:「別為他找借口了,那麼多明星,他不請別人,只請什麼溫小姐給他拍廣告,圖的什麼?還不就是想趁機……」孫畢竟還小,後面的話,徐老太太臨時吞了回去。
廣告?
清溪還不知道廣告的事。
徐老太太親自將報紙翻到廣告那頁。
清溪一眼就看到了溫霞的幾張旗袍照片,之前車前的只是側面照,而這幾張全是正臉,人時而清純,時而嫵,時而溫婉。這樣的人,連看了都移不開眼睛,顧懷修……
目定在溫霞紅紅的上,清溪忽的合上報紙,轉就往外走。
「你去哪兒?」徐老太太立即問。
「回房休息,中午還要做生意。」清溪頓在門口,聲音平靜。。
猜你喜歡
-
完結664 章

重生暖婚甜入骨
《重生暖婚甜入骨》【憶瑾年甜寵新作】讓我看看是哪個小倒黴蛋被墨閻王盯上了?哦,原來是我自己……
112.9萬字8.09 39585 -
完結160 章

紈绔王妃在線拐人
傳聞中的葉二小姐,紈绔、囂張又目中無人,還是山寨里的山寨老大。 讓她心情不爽的,無論男女,她都懟的毫不留情,唯獨一人她連說話都不敢大聲,生怕嚇著他。 逸王殿下長得俊俏,是京城大部分女子心中的白月光,可惜他自幼體弱多病,身體虛弱,活不久了。 可誰都不知道這樣的人會為了一個女人,血洗大半個皇宮,還成了一大禍害。 “阿嬋……”男子看著熟睡的女人,目光幽深,眼里滿滿的貪欲,又純又欲,只聽他低聲輕呢,“這輩子,你只能是我的。” (爽文加甜文,男主腹黑又會裝,女主張揚又很懶,感謝觀看!蟹蟹)
44.7萬字8 16548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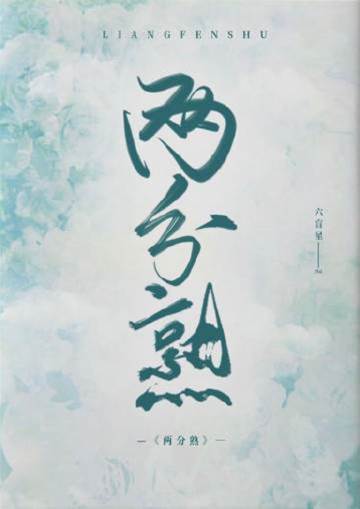
兩分熟
大學時,阮云喬一直覺得她和李硯只有兩分熟。學校里他是女粉萬千、拿獎無數的優秀學生,而她是風評奇差、天天跑劇組的浪蕩學渣。天差地別,毫無交集。那僅剩的兩分熟只在于——門一關、窗簾一拉,好學生像只惡犬要吞人的時候。…
25.3萬字8 6030 -
完結793 章

陛下的籠中雀跑路了
【強取豪奪\追妻火葬場嬌軟不馴寵妃x狠厲腹黑帝王】上一世尤聽容是被養在後宮的嬌雀,縱然錦衣玉食受盡寵愛卻結局潦草重活一世,她不想再和冷心冷肺的帝王的浪費時間,這金絲雀誰愛當誰當!暗中讓庶妹替自己入宮後,想美滋滋的嫁人過安穩的日子是選溫潤如玉的權臣,還是選未來富甲天下的皇商?遠在皇宮的帝王滿麵陰鷙,幽深的眸子浸血一般,扯斷了手裏的佛珠。權臣?皇商?尤聽容,你想都別想!他上一世唯一做錯的事就是護她周全。這一世他絕對不放手之後進宮的庶妹頻頻抱恙,尤聽容依召入宮侍疾。可她麵對的卻是陛下,隻能顫著長睫,任由他搔了綿軟的手心,眼神拉絲一般,刺的她膽顫心驚……
145.4萬字8 22748 -
完結186 章

許你年年歲歲好
【久別重逢/甜寵救贖/雙潔/雙學霸/結局HE】以前,姜歲初是大院里號令群娃的驕縱公主。后來,一場變故使姜歲初失去了家,并與青梅竹馬陸祉年失去聯系.高中重遇,陸祉年還是那個陸祉年,天之驕子.在主席臺上穿著干凈整潔的藍白校服作為新生代表上臺演講.姜歲初站在烏泱泱的人群中,逆光看著臺上的人.陸祉年:“我們是不是認識?”姜歲初愣了一下,揚起一個自認為很自然的微笑:“陸同學果然貴人多忘事,新生大會那天在樓梯間你幫了我.”“我是說以前。”他又走近幾步,“以前我們是不是認識?”胸腔里一股壓力襲來,又酸又漲。姜歲初笑了笑,搖頭:“應該不認識,我以前從來沒有來過云市。”那時的姜歲初生活在無盡黑暗中,十年后的重逢就像是短暫的光,不經意的照亮了一下她。她早已習慣黑暗,她清楚的知道突然出現的光不屬于她,遲早會消失。
57.5萬字8 134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