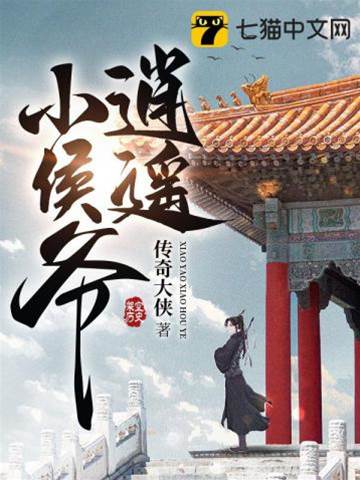《天賜一品》 第一千零一十一章 棋局(4K)
這一次,到了。
陳禮已經走了,衛瑤卿忽地長長的吐出了一口氣。
“我不想輸。”說道。
裴宗之嗯了一下,點了點頭道:“沒有誰想輸的。”
人人都想贏,但常勝不敗又豈是那麼容易做到的?真有人做到了,那就是一個傳奇了。
“這次我若贏了,往後一定會好好做好衛瑤卿。”道。
做了幾年的衛瑤卿,已經習慣於這個名字,可真正在做衛瑤卿這個名字該做的事卻之又。偶爾午夜夢迴驚醒時想的也是張家的舊事。張家的事一日不埃落定,就一日做不好這個衛家兒。
“你要做的不是衛家的兒。”裴宗之手了的頭,道,“你要做的是大天師。”他認真想了想道,“不管你姓張還是姓衛。”
這倒是!衛瑤卿想著想著不由笑了,頓了頓,對他道:“其實我這樣的人,一般人都會怕吧!”怎麼可能覺不到衛家對古怪的態度?畏懼、敬重。
但錯不在他們,這種態度在是張明珠時也能從族人上到。如果要說錯,或許錯在,但不覺得這是錯的。
“大天師當然不是普通人。”裴宗之道,“一般人當然畏懼敬重。”
衛瑤卿斜睨了他一眼:“那你呢?你怕我嗎?”
裴宗之道:“我又不是普通人。”他說這話時神坦然,沒有半點不好意思。
這人還真不會不好意思!衛瑤卿哈哈笑了幾聲,又嘆了口氣,道:“其實這一次,你不用再摻合進來了。”陳善不會對天大師做什麼,他也沒必要再追著陳善了。
裴宗之看了一眼:“這怎麼行?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說出的話怎麼能做不到?”
Advertisement
“你又不是什麼君子,此一時彼一時。”衛瑤卿看著他,替他整了整領,認真的看著他,“你真跟我去了,功了倒也罷了,若是失敗了,天大師就要瘋了!”
“那就讓他一直雲遊著。”裴宗之抓住的手放了下來卻沒有鬆開,“我同裴行庭說好了,一碗飯而已,還是素齋,他供得起的。”
“哎呀,這真是……”孩子瞥過臉去,又是高興又是難過,一向自詡能言善辯的,這種時候卻不知道要說什麼,只是看著他半晌之後,忽地抱住了他,把頭埋在他懷裡,半晌之後,出聲了,“我知道了。”
裴宗之反手抱住,又聽說道:“能遇到你太好了,就是你遇到我不太好。”跟著一起以犯險,他本沒必要這麼做的。
“也好的。”裴宗之認真的想了想說道。這麼活著雖然危險,但比起原來的日子,他更喜歡現在的自己,有七六慾,會喜怒哀樂。頓了頓,他還想說些什麼,卻聽有人在一旁咳了一聲。
兩人循聲去,見容易老先生一臉慨的看著他們。
兩人並沒有因爲他的注視而鬆開,只是就這麼看著他。
對視了片刻之後,還是容易老先生向後退了一步,他都有些頂不住了:現在的年輕人都這樣了麼?倒他有些不好意思了。
“你們,沒事吧?”他說道。
“沒事。”衛瑤卿搖了搖頭。
裴宗之眉頭微擰:“你不出現的話,更不會有事。”
嫌他打攪了年輕人的卿卿我我?容易老先生挑眉,看著神乖巧的孩子,心道這麼個危險的孩子也只在這個人面前這般出幾分小兒態吧!
“沒事就好!”容易老先生目轉向別,道,“雖然上次同你說的綁來陳禮這件事我們已經完了,但大家商量了一下,這個太簡單了,不能作數,所以還是決定留下來幫忙,再幫三天!”他說道,“這是大家的意思。”
Advertisement
三天啊!衛瑤卿盯著他看了片刻,忽地笑了:“真要留下來麼?可能有些危險啊!”
“江湖中人不懼危險。”容易老先生咳了一聲,似是有些尷尬的開口道,“他們……他們覺得你這個人還不錯,司由你掌管也能人放心。”
“那你們知道我在做什麼嗎?”衛瑤卿搖了搖頭,沒有瞞的意思,“這是私事,他們確定要幫忙?”
“確定。”容易老先生點頭,道,“所以,你開口直言吧!”
孩子臉上的意外漸漸褪去,神也認真了起來,看著他鄭重的開口了:“大恩不言謝,你們今日如此助我,我記下了。”
“記下就好。”容易老先生點頭,話帶到他也鬆了口氣,“得你這句承諾不虧……對了,我還有個不之請。”
“你說。”孩子詫異的看著他,還有什麼事?
容易老先生道:“你倆能鬆開說話嗎?看起來怪不正經的。”
不正經的衛瑤卿和裴宗之:“……”
……
陳善的決定並沒有瞞著衆人,即使突然收到要議和甚至要併大楚軍的消息,西南軍中卻自始至終沒有意料之中的慌,依舊每日按時練兵練。
對於陳善的決定,就連軍中主將都沒有半分異議,只除了一個人——陳禮。
“大哥,爲什麼要議和?”陳禮憤怒道,“我們難道沒有一戰之力嗎?現在匈奴大宛聯兵,該急的是大楚,不是我們!”
陳禮只是專心的了擺在桌上的那盆花草,聽著陳禮憤怒不解的聲音在營中迴響。
“你們說話呀!”陳禮推了推一旁幾個如泥雕木偶般站著不不發一言的將帥,道,“怎的都不說話?”
Advertisement
“我們聽侯爺的。”一個將帥看了他一眼,說道。
“民心所向,除了西南十八城,其他的遲早會歸於大楚之下。”陳善的目從那盆花草上移開,看向陳禮,朝他微微頷首,“這花不錯。”
突然沒來由的來了這麼一句,陳禮本能的心中一跳,好在陳善除了這一句並沒有再說別的,他這才鬆了口氣。
“大哥,那我們還有西南十八城,爲什麼要議和?”陳禮不解。
“西南十八城會因爲議和就不是侯爺的了麼?”有將帥見狀忍不住開口道,“不會。我們西南軍也不會因爲併大楚軍就忘了自己的份。”
“這樣打下去沒有勝算。”陳善點了點頭,對他道,“先前我失了民心,這一次自然要拿回來,阿禮,人眼要放長遠一些。”
又來了,陳禮忍不住冷笑,他現在在大家面前哪還有面子這種東西可言?大哥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衆人面前說他,早將他的臉給丟盡了。罷了,陳禮冷哼一聲,掀簾走了出去。
營中誰也沒有理會他的離去,衆位將帥依舊認真的聽著。
“這盤棋再這樣下下去就死局了,要重新盤活自然要置之死地而後生。”陳善說道,“我的軍一聲令下自會回來,我的西南十八城換個大楚的父母照樣是我的西南十八城。”
他說這句話時神倨傲,顯然有這樣的信心。
“如今我西南軍爲大局主求和是挽回民心的第一步。”陳善說著對那些將領說道,“你們跟隨黃定淵去邊境,聽命就是,無妨!”
“黃定淵這個人不會有私心,尤其還是這樣的大事。比起你們,還是他原來的那些屬下更擅長邊境作戰,所以,他的領兵作戰必然以你們爲輔,他們的軍隊爲主。與匈奴、大宛的戰中,你們的損失遠比他的軍隊損失要小的多。”陳善閉了閉眼,“待到時機合適,我自會抖出帝弒君篡位之事,那時候就是這盤棋重新盤活的時候。”
Advertisement
“侯爺所言極是!”幾個將領擡手毫無異義。
侯爺讓他們等,他們也絕無質疑,只要侯爺在,西南軍就不會倒。
陳善說完這些,忽地手了額頭,嘆道:“大楚軍的棋局我能盤活,倒是我這個弟弟越來越不像話了。”
幾個將領默不作聲沉默以對,他們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對於陳三爺的尊敬不過是因爲他是侯爺的手足罷了,沒有侯爺,這位三爺在他們心中什麼也不是。
陳善將桌上的茶水倒了那盆花草之中,那盆花草頃刻間就“滋滋”地冒出了一縷黑煙。陳善沉默的看了片刻,忽地開口道:“聽令!”
他已經足夠顧念兄弟之了,但此時,這兄弟之已不能再顧了。
……
……
夕西下,坐在吏部衙門的王詡了個懶腰,站了起來,看了眼整理齊整的卷宗,他下頭上的帽擡手略略理了理被帽的有些零的頭髮向外走去。
此時是下值的時辰了,王栩含笑與迎面相遇的同僚點了點頭向門口走去。
最近祖父迷上了茶,下值之後恰巧有功夫去城裡逛逛,且看看有沒有什麼能拿來討祖父歡心的。
看著越來越近的衙門,王栩臉上笑意更甚,還有兩步了,就要出去了。
“小王大人!”有人從衙門外火急火燎的衝了進來,王栩臉上的笑容凝滯在了臉上。
“什麼事?”他聽到自己在問。
面前的人一長安府衙差的差服,何太平的人啊,看樣子,今天城裡是逛不了,王栩心道。
走進長安府衙的時候,王栩還有些發懵。
府衙並未在審什麼案子,他被人直接帶到了府衙的後院,一眼便見到何太平以及他旁跟著的一個十幾歲的白淨年人。
“小的見過小王大人。”那年人的聲音有種古怪的尖銳。
王栩盯著他看了片刻,恍然:“你是宮裡當差的?”這應該是宮裡淨了的公公了。
“奴才小福子。”那年人道,“先任大總管李德全是奴才的乾爹。”
李德全啊!王栩微微一愣,回過神來,先帝跟前的紅人,自先帝逝世後沒多久便告老出宮了。
何太平看了小福子一眼,小福子會意當下便開口了。
“乾爹失蹤了!”他紅著眼,重重的朝王栩磕了個頭,“是被人擄走的。”
這是人口走失的案子吧!王栩沒有說話,只是瞟了眼神微妙的何太平。何太平是個盡責的父母,若非不得已,是絕對不會將事到旁人手裡的,就算是轉的話,按理來說也不會來尋他。大理寺的狄方行,吏部又有侍郎、尚書兩隻手都數不清的員爲什麼會來找他?
除非……除非是隻有他攬的下的事,或者準確的說,不是他攬的下,是王家可以手的事。
這樣的事當然不能嚷的天下皆知。
屋裡只有他們三個人,小福子神恍惚,一臉驚懼之。
李德全雖然年紀不小了,但倒是一向很好,陛下登基之後,甚至原本還準備繼續啓用他來著,但李德全卻以年老弱爲由出宮了。
作爲先帝邊的紅人,告老的日子比普通宮人要好過的多,吃穿不愁,但就是這樣吃穿不愁的日子卻讓李德全時常唉聲嘆氣,夜半驚醒。
“乾爹什麼都沒說,只是瞧著心不大好……”小福子說,“有一次奴才去看乾爹,陪著他喝了些酒,乾爹說有人在找他什麼的,當時還從街上尋了幾個武人護了一段時間的宅子。後來……後來沒什麼事就罷了。”
“之後宮裡人手不夠,奴才便未能告到假……”
這個他們也知道,那一段時日長安戒嚴,將西南的探子篩的差不多了,人手確實,宮裡的宮人有好些日子沒有出宮了。
“奴才雖不能出宮卻還記得人遞信什麼的,乾爹一直遞紙條與奴才,說沒什麼事……”
爲先帝跟前的紅人,李德全自然不可能大字不識,被李德全收作乾兒子的小福子也是識字的。
“奴才也以爲乾爹好好的,直到前日……前日奴才……”小福子說著說著便開始抹起了眼淚,瞧這激的樣子是說不下去了。何太平便讓人將小福子帶了出去,這才接話道:“前日放了一批宮人半日的假,小福子去李德全的住一看卻發現房早已遍佈塵土,分明是好些日子沒有人了。”
王栩了鼻子,道:“李德全未離宮前雖是個卻不歸吏部管,這個何大人來找我是不是沒必要?”
“宮裡人手不夠的時候正巧是嚴查西南探子的時候,”何太平道,“小王大人,明人不說暗話,我懷疑李德全或許同這件事有關。”
“西南現在以大局爲重要同我們議和了。”王栩道,“此時是友非敵,就算真是他們抓的人,難道我們會因爲他抓個宮人而翻臉麼?況且你這懷疑沒有什麼證據也不能上奏吧!”
“是啊,不能上奏。”何太平點頭道,“所以本來找小王大人了。”
王栩笑了笑,不置可否。
何太平道:“李德全心不好總有個緣由的,我懷疑他看到不該看的事了,人又被西南藏起來了,若是在不恰當的時候站出來,恐生大。”
當然他不是沒有懷疑過這是宮裡下的手,但細一想,若是宮裡下的手,沒必要拖那麼久的,早就手了。所以,應當不是宮裡頭了。
王栩臉上笑意去,看向何太平:沒有誰是傻的,陛下位子來路不正這件事看出來的不。但這種事看出來不代表會拿來大做文章,更何況,現在的陛下做的很不錯,足以服衆。
只是這個患終究是存在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跳出來。放在不同的人手裡,會有不同的結果。放在有些人手裡沒什麼用,甚至還要擔驚怕,譬如李德全;放在有些人手裡是制掣譬如裴行庭、崔遠道這些人;可若是放在一個有兵馬有威信的人手中,又在恰當的時候站出來,怕是真要釀出大來了。
譬如陳善。
章節報錯
猜你喜歡
-
完結765 章

嫡女狂妃:太子別惹我
沐家嫡女沐纖離。 初來乍到,居然是出現在被皇后率領眾人捉奸在床的現場。她還是當事人之一?! 她豈能乖乖坐以待斃? 大殿之上,她為證清白,無懼于太子的身份威嚴,與之雄辯,只為了揪出罪魁禍首果斷殺伐。 “說我與人私會穢亂宮闈,不好意思,太子殿下你親眼瞧見了嗎?”” “說我與你私定終身情書傳情?不好意思,本小姐不識字兒。” “說我心狠手辣不知羞恥,不好意思,本小姐只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斬草除根。 從此她名噪一時,在府里,沒事還和姨娘庶妹斗一斗心機,日子倒也快活。 卻不料,她這一切,都被腹黑的某人看在眼里,記在了心里……
181.1萬字8 110710 -
完結392 章

傅先生的小祖宗重生了
國際談判官江芙遭人陷害而亡。醒來發現自己重生在一個剛訂婚的女大學生身上。與未婚夫初次交鋒,傅奚亭語氣冰冷帶著殺氣:“聽話,就留著,不聽話,就棄了。”再次交鋒,江芙站在首都大學禮堂里參加國際大學生辯論賽,望著臺下當裁判的傅奚亭,字正腔圓問道:…
106.4萬字8.18 49908 -
完結8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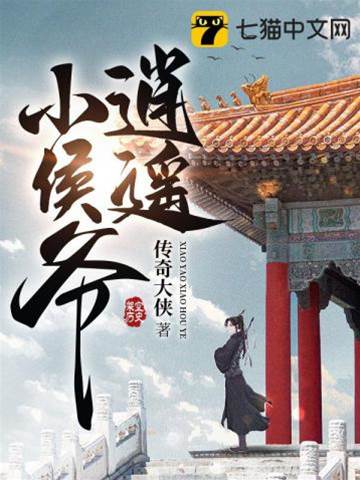
逍遙小侯爺
穿越古代,成了敗家大少。手握現代知識,背靠五千年文明的他。意外帶著王朝走上崛起之路!于是,他敗出了家財萬貫!敗出了盛世昌隆!敗了個青史留名,萬民傳頌!
148.9萬字8 90456 -
完結118 章
穿成沖喜王妃后我成了病嬌王爺心尖寵
從小寄人籬下的傻女,被害死在鄉下后依然難逃被賣的命運。 美眸初綻,傭兵女王穿越重生,夢魘散去后必將報仇雪恥。 沒錢??活死人肉白骨,值多少錢? 亂世?空間在手,天下我有! 蒙塵明珠閃耀光華之時,各路人馬紛紛上門,偽前任:你既曾入我門,就是我的人。 偽前任他叔:你敢棄我而去?! 「傻女」 冷笑:緣已盡,莫糾纏。 掃清障礙奔小康,我的地盤我做主。 某天,一個戴著銀面具?神秘人邪氣一笑:「聽說你到處跟人說,你想當寡婦?」
35.7萬字8 1234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