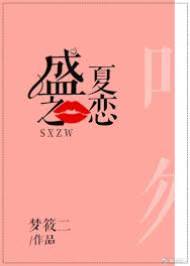《過期暗戀》 第36章 不省人事
周末結束,蘇羨音繼續忙碌起來。
陳潯也一頭扎進了實驗室。
蘇羨音把碎冰藍玫瑰養在洗乾淨的玻璃汽水瓶里,那張直到回宿舍才看見的小卡片則被放在書架最外層,反扣在花瓶前。
陳潯的字很飄逸,看得出有筆功底。
[覺有很多話想說,落筆卻一直停頓,那就說聲晚安吧,好夢。——陳]
不過是普普通通沒太多含義的一句話,蘇羨音仍然當做珍寶一樣收藏起來。
-
11月20日,蘇羨音請了兩天假回了趟南城。
每年臨到這個時間點都有些提不起勁,也不是故意讓自己緒低落,就是像冬眠期一樣,機能自在這個時間點做出相應的反應。
11月22日是媽媽的忌日。
往年蘇橋會帶著蘇羨音一起去墓地,可今年因為出差的安排,蘇橋提前一天去了墓地,今年蘇羨音只能自己前往。
其實反而覺得輕鬆。
心中的那刺讓每每跟蘇橋一起去看媽媽都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彆扭。
其實知道爸爸也是媽媽的。
在媽媽生病以前,不是無法到兩人之間的濃厚誼。
從未懷疑過父母之間的。
甚至一直很慶幸自己的爸爸媽媽鮮吵得不可開互相傷害,原本生活在一個堪稱幸福模板的家庭。
但更因為如此,醫院的那幕才令無法介懷。
無論在心底里做過多次心裏建設,那一幕給帶來的崩塌始終縈繞在腦海。
灰撲撲的一片,牆皮破裂耷拉在牆面上。
所以蘇羨音每次跟著蘇橋來墓園時都很沉默,所有想跟媽媽說的話都說不出口,只能在心裏默念,祈禱媽媽能聽得見。
……
蘇羨音這次起得很早,南城下了一夜的雨,夜裏窗戶沒關嚴實,清早吹進陣陣帶著氣的寒風,將的睡意一點點驅散。
Advertisement
六點,徹底睡不著覺了。
在被窩裏賴床賴到六點半,起床給自己做個早餐,剛坐在客廳剝著蛋。
孟凡璇醒了,著的頭,小聲問:「我等會兒送你去?」
蘇羨音:「沒關係,我已經約好車了,吃完就走。」
孟凡璇沒堅持,只是囑咐下雨天要小心。
剛出門的時候還是鬱的小雨天氣,蘇羨音撐著一把黑傘,捧著花走進了墓園裏。
墓碑很乾凈,被一夜的雨水沖刷過後更顯得潔凈瑩亮。
昨天蘇橋留下的花束已經被雨水泡得有些發灰發白,蘇羨音將花束收起來靠在一邊。
媽媽的像上的笑容很和藹,蘇羨音一下子就酸了鼻子。
好像多年來未說出口的話一下子有了宣洩口,扶著墓碑,低聲絮絮,從高考講到上次國慶回家。
再氣的時候,甚至覺有些頭暈目眩。
淚水已經淌了滿臉。
其實現在已經不經常想起媽媽,在藏緒方面已經做到能生巧運用自如。
算起來,甚至都沒有高中時候那麼敏了。
但想念好像只是埋藏在地底下的酒,時間越久,啟封時就越是醇厚。
蘇羨音被這鋪天蓋地的思念之淹沒,任由淚水淌遍臉頰,滾落至襟。
真的還是,很想念媽媽。
電話聲響起的時候,蘇羨音打了個哆嗦。
哭得太專註,講得太認真,抬頭天才發現天愈發沉,黑雲像是要把整片天給下來,風吹的的黑風簌簌作響,領被風颳起來蓋在臉上,雨傘傘面也像是要被風掀翻,要用很大的力氣才能把傘柄握牢。
按下接通鍵。
陳潯首先聽見的是呼呼的風聲。
於是他問:「你在外面?」
蘇羨音:「我有點事,請假回了南城。」
Advertisement
「你聲音怎麼了?又冒了?」
「沒。」蘇羨音悶悶的。
「有事嗎?」蘇羨音反問他。
「沒什麼,就是……」陳潯難得在電話里也猶豫,半晌又坦誠地繼續說下去,「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突然有一種念頭想給你打電話。」
「但是,你到底在哪?」
風雨雷電的聲音太嘈雜,陳潯的聲音在聽筒里顯得並不清晰也並不真切,但蘇羨音還是聽到了他話語里的一點焦急。
被這風吹得眼淚都乾涸在臉上,連做表都艱難,卻莫名因為這句話,一滴熱淚又滾落下來。
兩人就這樣拿著手機沉默了將近半分鐘。
陳潯打破了這場沉默。
他輕嘆了口氣,語氣有些無奈。
「蘇羨音。」
他溫得像是在夢境。
「為什麼哭了?」
蘇羨音的眼淚更加洶湧了。
注意力全在這通電話上,一道驚天雷落下來,嚇得小聲喊了一聲。
陳潯:「怎麼了?!」
「蘇羨音,告訴我,你在哪?」
他聲音陡然提高了八度,蘇羨音這才回過神來,風越來越大了,握了雨傘。
說:「剛剛突然打雷不小心嚇到了,我沒事,我在……」
「墓園看我媽媽。」
片刻的寂靜。
陳潯:「下雨了?很大?跟媽媽說完話了嗎?雨大的話就先找個地方躲一躲。」
「別害怕。」
「我不掛電話。」
蘇羨音的眼淚立刻蓄滿了眼眶,小聲地跟媽媽道別,然後戴上耳機,大雨順勢傾盆落下,砸在雨傘上的雨滴聲一聲比一聲重。
陳潯小聲叮囑:「走慢一點,小心路,臺階要注意,傘打低一點,找一個最近的可以躲雨的地方。」
一一照做。
明明冰涼的雨水將的頃刻間打,寒氣一點點滲進去,心口那一團卻是暖融融的。
Advertisement
走到了墓園大門的屋檐下,時間還早,躲雨的人並不多。
收起傘柄,雨水淅淅瀝瀝沿著傘面往下落,很快就在蘇羨音腳前積一灘水。
「有人來接你嗎?」
「我等雨小一點打個車吧。」
「我看了天氣預報,看起來大雨還會持續一陣,你那個位置應該不好車吧,你可以在手機上看。」
蘇羨音在手機上作著,低聲說:「排隊第63位,預計等候50分鐘。」
陳潯在那頭嘆口氣:「等著,我給你想辦法。」
「你能想什麼辦法?」蘇羨音下意識地問。
陳潯卻笑了:「我剛剛還在真的有在看航班,可是就算我坐最近的航班回南城,趕到你那裏也已經是中午了。」
他話裏帶點無奈與自嘲。
認栽一般,說:「現在好點兒了嗎?眼淚乾了?」
遲來的恥瞬間包裹住蘇羨音,下卻無論如何發不出聲音。
陳潯:「我找人來接你了,很快。」
「蘇羨音。」
他忽地輕輕喊的名字。
的鼻音依舊很重。
「嗯?」
「是……想媽媽了嗎?」
許久許久,久到陳潯以為電話已經被掐斷,才聽見那端,很輕很輕的一聲。
帶著音的一個單位元組。
「嗯。」
他的心忽地被揪住,五臟六腑跟著發出抖的囈語。
無法不心疼。
……
後來,蘇羨音在電話里聽著陳潯輕的語調,有一句沒一句地幫轉移注意力,一顆心終於回歸原位。
本沒意識到到底打了多久的電話。
甚至在陳潯「安排的人」找到蘇羨音時,他都不允許掛電話。
「安全到家了再掛。」
蘇羨音沒想到陳潯會找到鄒啟然,和對方不,客客氣氣地上車,表達謝。
鄒啟然卻擺擺手:「潯哥一句話的事兒,不必放在心上,我還欠潯哥好幾個人呢。」
Advertisement
「而且我就住附近,很方便。」
蘇羨音禮貌地笑了笑。
後來蘇羨音終於在自己房間坐下時,窗外淅淅瀝瀝的雨聲終於小了點。
陳潯對說:「洗個熱水澡好好休息一下。」
「如果還是怕,或者晚上睡不著,可以隨時聯繫我。」
蘇羨音一顆心被他的溫熨帖得服服帖帖。
-
蘇羨音周四回了川北。
在高鐵上,離川北還有半個小時車程的時候就接到陳潯的電話。
可說話人卻不是陳潯,而是姚達。
「蘇妹妹,快來臨豪街的響KTV,陳潯快被沈子逸灌倒了,快來幫幫他。」
蘇羨音微皺著眉。
只聽到那邊鬨哄一團,姚達簡明說明了一下況。
原來今天是沈子逸的生日。
據說是沈子逸組的酒局,非要一拼高下,姚達酒過敏不參與斗,可陳潯就沒那麼幸運了,完全不是沈子逸的對手。
姚達:「沈子逸說了,可以讓陳潯找個幫手,蘇妹妹快來啊。」
蘇羨音還在猶豫,聽見電話那頭陳潯的聲音。
好像手機被他搶了回去。
他說話含糊不清的,顯然是已經有了醉意。
「蘇羨音……來嗎?」
來嗎?
怎麼能放心。
蘇羨音下了高鐵就打了車直奔KTV。
卻在KTV門口看見了沈子逸。
他站在樹底下煙,面前卻站著一個蘇羨音從未見過的孩。
孩臉龐稚,穿著鈎針套頭,下卻是一條短和長靴,看起來似乎不是同齡人,有著他們上沒有的無畏與朝氣。
兩人都沒有說話,生卻仰著一張小臉,固執地看向沈子逸。
孩似乎是不滿意對方一聲不吭的態度,忽地奪走沈子逸指尖的煙,狠狠丟在地上,踩在腳底。
沈子逸這才看向孩,目是蘇羨音從未見過的冷漠。
「虞芷靜。」
「你適可而止。」
蘇羨音倒吸一口涼氣,對這個名字有印象,眨眨眼不捨得挪開步伐。
孩立刻紅了眼眶,卻依舊一臉倔強,咬著下就是不說話。
良久,孩從包里拿出一個包裝的禮盒,塞到沈子逸手裏。
「懦夫!」
稚的嗓音只吐出這兩個字,然後轉離開的背影很決絕,卻也脆弱。
蘇羨音嘆一口氣。
後背卻陡然來重量,有人從後圈住了的脖子。
熱氣就噴灑在耳邊,恐懼瞬間攀爬至的後背。
「你來啦?嘿嘿。」
蘇羨音躲避的作僵在半空,不可置信地回頭。
果然看見將大半重量都到自己上的、親昵地圈住自己脖子傻笑的,正是醉鬼陳潯。
陳潯臉頰浮起酡紅,眼神渙散,眨著眨著就要閉上。
不是醉鬼又是什麼。
蘇羨音嫌棄地想要推開他,他圈住脖頸的手卻牢固。
嘗試幾次無果后,乾脆認栽,只是他的頭著的髮,害彈不得。
蘇羨音忍住怒火,低聲說:「頭髮!住頭髮了。」
陳潯慢半拍地「哦」了一聲以後,鬆開,將的頭髮全部撥至另一側,然後又繼續圈住。
蘇羨音:「……」
「你怎麼才來啊?」
他話說得含糊又慢,像個稚園剛識字的小朋友。
蘇羨音:「我還要怎麼快?我又沒有飛天掃帚。」
陳潯只顧傻樂。
就這樣,站在原地顯得背影有些落寞的沈子逸也終於注意到了這邊的兩人。
蘇羨音朝他求救:「你能不能把這個醉鬼給我拉開?」
陳潯卻忽然鬆開了,他跌跌撞撞走到蘇羨音正面。
手撐在膝蓋上,忽地彎下腰,將臉湊到跟前。
酒氣更濃了,即便對著這樣英俊的一張臉,蘇羨音依舊下意識往後退。
陳潯卻慢慢地抬起右手,上蘇羨音臉頰,他右手拇指指腹輕輕在蘇羨音下眼瞼掃了掃。
蘇羨音皺著眉:「你又幹嘛?」
陳潯歪著腦袋,目不復清明,話語卻清晰。
「蘇羨音。」
「我看看你哭了沒。」
蘇羨音的呼吸停了一拍,倉惶無措地扇了扇眼睫。
「不哭了就好。」
陳潯笑得咧出一口白牙,眼睛彎了月牙。
「那你笑一個?」
蘇羨音真的笑了,眼睛卻亮盈盈的。
看向已經醉得堪稱不省人事的陳潯,慢慢牽了角。
傻子。
猜你喜歡
-
完結573 章

末世甜寵:大佬罩我超強的
“老大,我臣服你的心,青天可鑒,絕對對你冇有非分之想。你千萬不想要相信外麵的謠言!我絕對是你最忠誠的女小弟!” 謠言紛起,在末世這個大熔爐。 杜涼涼一心隻想抱緊老大的金大腿,在末世裡身藏一個超市係統,希望不愁吃,不愁穿,安安穩穩活到老,不被切片做研究。 然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謠言四起,弄得她小心肝狂跳。 “嗯,我知道你對我冇有非分之想,臣服之心青天可鑒!”老大如是說道。 杜涼涼眼睛放光,連忙點頭。小心肝兒剛放到肚子,就聽到自己老大繼續說道。 “可是涼涼,我對你有非分之想,不想要你的臣服之心,而是要你的愛戀之心了怎麼辦?”
102.9萬字8 14925 -
完結350 章
人魚陷落
战术指挥大佬(撒娇白狮alpha)×武力值top呆呆美人突击手(高贵人鱼omega) 两人从前都是研究院的实验体,相依为命但又相互利用。因为一场误会,白狮被人鱼所伤,嘴上嚷嚷着报仇再见时却难以下手,终究还是想要保护他的小人鱼……
84.1萬字8 6740 -
完結274 章

月光盒子
她大概也沒想到,準備敷衍了事的相親對象,是曾經暗戀的那個人。 就像一臺時光機器把他送到她面前,令她不知所措。 “我是沈恬。” “周慎之。”他低沉冷淡,朝她伸手。 沈恬笑了笑,把那句你還記得我嗎我們高三是同班同學嚥了回去。 - 暗戀,是一個人的戰場。 從上場到退役,單槍匹馬闖過你的世界,成了你牆壁上撲簌簌掉落的灰。
36.4萬字8.09 13754 -
完結324 章

怎敵她風情萬種
【巧取豪奪 先婚後愛 追妻火葬場】 那夜風雨交加,顧慈身後有綁匪,她抓緊眼前男人筆挺的西裝褲,“救救我……” 江祁雲站在保鏢的傘下, 鞋尖踹開她的手指。 “救你,憑什麼?” 她一咬牙:“你救我一次,要我做什麼都可以。” 江祁雲蹲下矜貴的身子,手指捏著她的下巴,譏笑道:“那你得知道,我可不溫柔。” - 成年男女,各取所需。 他貪她美色,她圖他庇佑。 誰都說,江祁雲這種男人隻是玩玩她而已。 可忽有一天,他說,“顧慈,和我結婚,要什麼我都給你。” 她微愣,“今天不是愚人節……” - 顧慈有段失去的記憶,遺忘的夢。 當過往與現實重疊,她幡然醒悟,原來一切都是假。 不過是他的算計,她的淪陷。 - 遇見顧慈前,江祁雲覺得女人這種生物又作又矯情。 再後來,恢複單身的江祁雲風流依舊,別人問他喜歡什麼樣的女人,他說:“作的,矯情的。” …… (排雷:狗血老套路)
60萬字8.18 4510 -
完結17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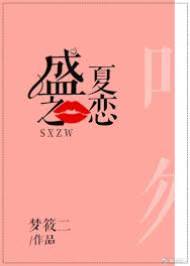
盛夏之戀
那天,任彥東生日派對。 包間外走廊上,發小勸任彥東:“及時回頭吧,別再傷害盛夏,就因為她名字有個夏沐的夏,你就跟她在一起了?” 任彥東覷他一眼,嫌他聒噪,便說了句:“煙都堵不住你嘴。” 發小無意間側臉,懵了。 盛夏手里拿著項目合同,來找任彥東。 任彥東轉身,就跟盛夏的目光對上。 盛夏緩了緩,走過去,依舊保持著驕傲的微笑,不過稱呼改成,“任總,就看在您把我當夏沐替身的份上,您就爽快點,把合同簽給我。” 任彥東望著她的眼,“沒把你當替身,還怎麼簽給你?” 他把杯中紅酒一飲而盡,抬步離開。 后來,盛夏說:我信你沒把我當替身,只當女朋友,簽給我吧。 任彥東看都沒看她,根本就不接茬。 再后來,為了這份原本板上釘釘的合同,盛夏把團隊里的人都得罪了,任彥東還是沒松口。 再再后來,盛夏問他:在分手和簽合同之間,你選哪個? 任彥東:前者。 那份合同,最終任彥東也沒有簽給盛夏,后來和結婚證一起,一直放在保險柜。 那年,盛夏,不是誰的替身,只是他的她。
25.4萬字8.18 7564 -
完結147 章

霍總別裝窮了!夫人知道你馬甲了
薑願撿了姐姐不要的贅婿!沒房沒車沒存款,月入四千五給人當保安!雖然窮了點,但為人上進,人品正直,能處!薑願已經做好拚命賺錢、養家糊口的準備,沒想到自家老公上電視了。億萬身家,頂級豪門!昔日嫌棄他窮的姐姐傻眼了,哭天搶地後悔終生。所有人都說她走了狗屎運,從今往後嫁入豪門享福了。可她卻意外聽到……霍知硯:“我和她的婚姻,不過是逢場作戲罷了。她,根本配不上我。”薑願徹底心死,丟下一封離婚協議連夜買機票逃走。卻不想霍知硯封鎖了整個機場,紅著眼趕了過去,將她緊緊圈在懷裏:“你怎麽敢走的?要走,也要把我帶上!”回去後,男人跪在搓衣板上:“老婆,之前是我不懂事,胡說八道,你大人有大量,別和我一般見識!”霍知硯表示,這婚真香!
25.9萬字8.18 6271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