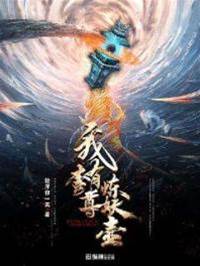《東宮美人(荔簫)》 第 40 章 第 40 章
太子在楚怡這個現代人眼里都顯得過于狂野的舉,果然惹了點麻煩。
——當時有朝臣在逛廟會。
——而且好巧不巧的還是個史。
于是史大人很盡職盡責地彈劾了太子,說他在鬧市“公然強吻民婦”“禮數全無”“傷風敗俗”。
這道折子是在初六晚上被皇帝看到的,皇帝大概也是頭一回看見自家親兒子被指摘這種罪名,立刻傳了太子去乾清宮問話。
沈晰原已沐浴更完打算躺上床跟楚怡商量明天是去賞雪還是去騎馬的問題了,聽到急召不得不趕更,在小兩刻后便冠齊整地走進了乾清宮。
然后就被罵了個狗噴頭。
沈晰站在底下低著頭不敢吭氣兒,皇帝罵痛快了,被史指責自家兒子“傷風敗俗”的那份辱便也淡了,終于給了他個說話的機會:“你究竟怎麼回事!”
沈晰:“兒臣一時……難自。”
都是被楚怡那聲“夫君”攪的,他的腦子在嗡鳴聲中一片空白,憑著直覺就吻了下去。
吻完之后他也傻了啊!他怎麼能在天化日之下干這種事?
皇帝深呼吸,鎖著眉頭看他:“那是哪家的民婦?”
“……那不是民婦。”沈晰悶著頭,“那是兒臣東宮的人,兒臣當真喜歡,出宮玩樂又放松了些,所以一時……”
“行了。”皇帝不耐地擺手,一時卻不知該怎麼說他。
說他不對?他是不對,史說他“有傷風化”一點錯都沒有。別說為太子了,就是隨便一個讀過點書的人,都不該做出這樣的舉。
可年輕人到深難以自持,好像有不稀奇。
況且那還是他東宮有名分的妾室。
皇帝沉著張臉,手指一下下輕敲在案面上,敲出的聲音讓沈晰心慌。
Advertisement
這點子事對他造什麼太大的影響是不至于的,充其量在日后幾十年里都算他一個不大不小的笑柄,但他擔心父皇為了警醒他把楚怡發落了,腦子里百轉千回地在想若父皇一會兒開了口,他怎麼為楚怡辯解。
這事跟楚怡不相干啊!是他突然發了瘋,楚怡連反應的時間都沒有。再說就算反應過來,也不能在大街上他一不是?
父子兩個一個不快、一個心虛,沉默在殿里蔓延了好半晌,皇帝道:“你寫道折子好好謝罪,上元節后呈上來。”
“是。”沈晰頭皮發麻地應下,皇帝又說:“去奉先殿跪半個時辰。”
沈晰又應道:“是。”
皇帝擺手:“去吧。”
沈晰猛地松氣,繼而生怕父皇再想起責罰楚怡似的趕忙施大禮告退。
.
皇帝這樣抉擇,這事便注定不會傳得太廣了,但東宮里依舊知曉了始末。
趙瑾月在臨睡前聽聞了這事,聞訊后面晴不定,半晌都不清自己心里究竟是怎樣的。
是為太子擔心的,也應該為太子擔心。這樣的惡名雖然不至于傷其基,但說出去到底不好聽,聽起來就好像太子是個浪公子一樣。
可心里又地有那麼點兒快意。
太子為了楚氏那樣失分寸,到底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了!
趙瑾月后牙磨著,而后就這樣磨著牙緩出了一口氣:“太子殿下現在在哪兒?”
“在奉先殿。”邊的宦回道,“皇上讓殿下在祖宗靈位前跪半個時辰。”
趙瑾月冷笑了聲:“這事,難道能是太子一人之過麼?皇上不好跟小輩眷計較罷了。”
那宦不好接口,只一欠等吩咐。
趙瑾月一壁悠悠地躺下去,一壁淡聲道:“讓楚氏跪一個時辰。本宮給留三分面,讓在自己院子里跪就行了。”
Advertisement
“是。”那宦趕應聲,便要退下。卻聽太子妃又說:“可既然自己不要臉……”
宦又忙收住了腳。
趙瑾月闔目道:“這個時辰,想來也該準備睡了吧。不必更了,當下穿著什麼,就直接出來跪著吧。”
“……殿下?”旁邊的白蕊覺得不妥,但看太子妃的面,知道是真生氣了便也沒敢勸。
.
綠意閣里,楚怡正躺在床上發著愣等沈晰回來,乍然聽見這種吩咐驚得臉都白了:“啥?!”
宜春殿來的幾個宦不容多做拖延,直接將從床上往下一架,便往院子里去。
現下天冷,楚怡的寢倒是很厚,夾棉的。可屋里畢竟有地龍還有炭盆,這厚度再厚也扛不住外面的冷勁兒,楚怡一被架出屋門就打了個寒噤。
接著便被宦按著跪了下來,膝蓋往青石板上一磕,又打了個寒噤。
于是齒間打著抬起頭,看向青玉:“去!去小廚房,讓應泉給我煮一大鍋生姜紅糖水,煮濃點兒,姜要足,一個時辰后我要喝!”
宜春殿來的宦直蹙眉頭:“奉儀娘子,這是太子妃殿下的吩咐。”
楚怡跪在那兒崩潰地嚷道:“太子妃殿下說不讓我喝生姜紅糖水了?!”
……那倒沒有。
那宦一琢磨,只得訕訕閉口。心里一邊覺得說得在理,一邊又覺得怎麼能這樣呢?他可從沒聽過誰被罰跪敢這麼大張旗鼓地讓底下人提前備好生姜紅糖水。
楚怡現在可顧不上這些,只覺得上的熱度在迅速消散,腦子里破口大罵這吃人的舊社會!
不就是個強吻嗎,怎麼還帶罰跪的啊!!!
竟然還專門說一句不讓加服,變態吧!!!
Advertisement
再說又不是強吻太子!!!雖然也說不上多麼被迫……被吻得還高興的,但這事兒是太子風啊!!!
過了不到五分鐘,又哆哆嗦嗦地開了口:“這位公公,能給我拿個團嗎?”
那位公公一臉無語:“奉儀娘子,太子妃殿下……”
“太子妃殿下說不讓我用團了嗎?!”楚怡凌地問道。
也是趕巧了這位位份較高于另幾位的宦比較實在,一琢磨還真沒有,就只能掛著一臉無語的表給找團去了。
又過了會兒,楚怡:“拿個手爐給我。”
“奉儀娘子,太……”這回那宦說到一半就自己噎住了,咂著扭頭,“得,下奴給您拿去。”
不然又得說“太子妃殿下說不讓我用手爐了嗎?”,他還是沒話說。
他心里腹誹著,心說這位主子也太賊了,以后再怎麼罰,是不是還得提前說明白“不許用團不許用手爐不許提前熬生姜紅糖水”?
這難度也是很大了。
就這樣,楚怡墊著團、抱著手爐跪著了,覺比剛才舒服了不。
雖然手爐就那麼大點兒,只能讓腹部那一小塊和手里熱乎起來,但據中學理里的熱傳導(……)可知,熱量是可以向四蔓延的,總歸比不用要暖和不!
另外,還有了個生姜紅糖水的盼頭嘛!
楚怡打算用數數消磨時。算了一下,一個時辰是倆小時,一百二十分鐘分鐘,合七千二百秒。數數的速度大概會比秒快一點,便告訴自己數到一萬就差不多可以喝生姜紅糖水去了。
在數到五千三百多時,外面響起了一陣嘈雜的腳步。
接著,楚怡聽到守在院門口的白玉問安:“殿下。”
Advertisement
東宮里總共有兩個人能稱殿下,這會兒會來的應該不是太子妃。
——好,這回連一萬都不用數了!
楚怡驟然一松氣,繼而敏銳地覺到,背后的嘈雜一停,變得萬籟俱寂。
遲疑著扭頭,正好看到他那張鐵青的臉。
沈晰定在院門口也看著,一火氣在他中竄了又竄,過了很久,他才得以借著寒風把它制下去。
“都滾。”他咬著牙關道。
滿院的宮人沒一個敢吭聲,幾個宜春殿來的宦訓練有素地跪地叩首,旋即便疾步退了出去。
沈晰幾步走到楚怡邊,手便攙,在楚怡因為麻而發出輕的同時,他看到了懷里的手爐。
“……?”他神古怪地要接過去,一把抱住:“進屋再說!我讓那位公公拿給我的時候,里面的炭好像不太滿,所以本來就不太熱,殿下再拿走就更冷了!”
沈晰:“……”
他就說為什麼罰跪還會抱個手爐,合著是自己要的啊?!
他哭笑不得地把往里扶:“快進屋。”
楚怡麻,而且麻得不均勻,被他扶著也只能歪歪扭扭地單蹦跶。是以到了堂屋門口的時候,沈晰覺得不好過門檻,便直接把抱了起來,大步流星地折進了屋里,直接把放在了床上。
然后他問:“太子妃怎麼說的?”
“……就說我狐主,讓我出去跪著,不用加服了。”楚怡不快地撇,答完話就招呼青玉,“我給我端生姜紅糖水去。”
說罷便滾進了被子里,把臉也蒙了起來。
生氣!
能理解這個時代的制度存在不公是難免的,但覺得太子妃這不是在按制度辦事,是在心折騰!
可沒法跟太子議論太子妃的不是。早就覺到了,他雖然不喜歡太子妃,可他也不會跟旁人(包括)指責太子妃。由此可見,如果反過來跟他抱怨,他大概也不會高興。
第一次對這件事到委屈。
先前只覺得這是沒有辦法的,不是他們三個里任何一個人的錯,是這個時代的錯。他對太子妃的這種照顧其實已經是最好的辦法,能最大程度地讓三方都不傷害。
可現在了欺負,就不這麼想了。轉而覺得或許這個時代有這個時代的無奈,但太子妃這麼欺負,也夠毒的!!!
沈晰坐在床邊又兀自緩了好一會兒氣,拍了拍的被子:“一會兒讓太醫來給你看看。”
“……不用。”楚怡竭力讓語氣正常,“也沒什麼不適,我自己緩緩就好了。”
“宜春殿那邊,我明天一早過去說個明白。”他又說。
“?”楚怡揭開了被子,猶豫地打量著他,“殿下覺得是太子妃殿下不對?”
“不然呢?”沈晰鎖眉,倚到床頭攬住了,“我沒想到會這麼干。最近……”他說著搖了搖頭,“罷了,我從來也不懂究竟是怎麼想的,但這回的事,不該這樣。”
行事不端的人是他,史彈劾的人是他,父皇怒斥的也是他。
史和父皇都半句沒提楚怡,沒說東宮有人狐主,難道太子妃就愣能聽說一出不一樣的故事?
絕不是那樣的。
就是心在找楚怡的茬。
沈晰的心復雜又費解。
他真的不明白,明明是太子妃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一直對他不冷不熱。
怎麼如今他對楚怡好了,又不甘心了呢?Μ.166xs.cc
到底想讓他怎麼樣啊!
猜你喜歡
-
完結119 章
農家醜媳
二十一世紀私房菜老闆葉青青,一覺醒來成爲一名"沉魚落雁"農家媳. 村裡人皆嘲笑她:"李家買來那醜婦,擡頭能把大雁嚇摔,低頭能把小魚嚇瘋,跟李家那病秧子倒也是絕配!" 醜婦咬牙發奮,不但將自己改造成貌美如花,病秧子相公也被調理得日漸健康,好日子來咯! 可是,不想突然蹦躂出一個女人稱是她娘,指鼻子罵窮書生不配她,勒令她嫁給土財主. 她淡定地撫著小腹問,"多給彩禮不?肚裡還一個呢." 相公驚訝不說話,當夜就長篇大論起來,"古人有云:車無轅而不行,人無信則不立,業無信而不興." "怎麼?" "爲了家業興隆,娘子,我們還是把肚裡那個做實吧——"病秧子化身餓狼,夜夜耕耘不知休. 良田大宅、連鎖店鋪、聰明包子、健壯夫君、美貌身材統統拿下.只是,相公,你的身份…有點可疑!
38.5萬字7.91 34579 -
完結185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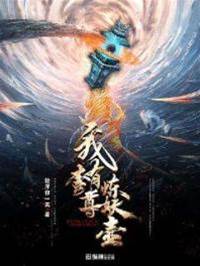
我有一尊煉妖壺
天地為爐,陰陽為碳。 一個破夜壺,誰能想到,竟是傳說中的上古神器「煉妖壺! 剛剛穿越異世,還沒吃上一口香噴噴的軟飯,宅男韓風就不得不手掌煉妖壺,醉臥美人膝,開啟自己寂寞如雪的新人生……
401萬字8 55054 -
完結319 章

帶億萬物資做惡毒后娘
【反套路+亂世求生】 教官九月帶著億萬物資穿成克死了兩任丈夫的黑寡婦。 第三次,她被國家分配給養了三個小崽子的光棍。 尚未洞房,夫君又被抓去做了壯丁。 在這個啥都不如食物值錢的亂世,九月不甘不愿的做了三個崽子的后娘。 于是,她的惡毒之名不脛而走! 多年后,三個崽子名揚天下。 成為戰神的夫君說:媳婦,仨娃都是我撿來的,各個漏風,不如我們自己生一個吧! 九月挑眉:“滾開,別耽誤老娘賺取功德給我的平頭哥特戰隊兌換裝備!”
56.5萬字8 300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