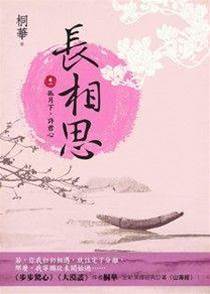《穿書后我推倒了暴躁男二》 第047回:他坦白錯了方向
黃昏,黃昏后。
染回到隨空間里摘了不三七回來,和蕓兒倆人放在小罐子里搗碎。染讓蕓兒拿一些送到后院為李老頭他們敷在傷,自己則把水生到跟前,親自替他敷藥。
水生藏轉著頭,不住地說:“怎敢勞駕夫人親自手。”
“小馬駒不聽話把板車拉翻了?”染歪頭睨向他,“侯爺就在車上,他怎麼沒有傷?偏你這個牽馬的掛了彩?你想瞞我什麼?”
“沒,小的沒有瞞著夫人。”水生怯怯地回道,眉清目秀的臉上早退去與那些潑皮打架時的狠厲。
染把小罐子使勁兒磕在案幾上,“你們在菜市場里遇見地頭蛇了?”
水生深無奈,明明是他不教大家承認的,最后夫人卻是在他這里找到的突破口。他低眉閃躲,含糊其辭。
“這算啥呀?有什麼不敢對我講的?”染指向小罐子,囑咐道:“趕自己個兒敷上,明兒一早就沒事了。”
“噯。”水生口里應承著,已手往自己的青紫敷上去,“多謝夫人。”
“蕓兒特意燒了魚等你們回來吃,本以為你們能吃的高興。瞧你和侯爺剛才在飯桌上那副德,誰看不出來出了事?”
水生聽哈陪笑,不再過多解釋什麼。染心里犯嘀咕,總覺得水生沒有完全代明白,難道那些地頭蛇說了很嚴重的話?又把隋給刺激到了?
簡單安水生幾言,便離開東耳房,穿小門徑直回往東正房這邊來。
隋出奇的安靜,他端坐在案幾旁,手里仍捧著一本快散了架的兵書。在暖黃的燈燭下,他那消瘦的孤影越發教人心疼。
染敲了敲自己的腦子,這人又不是楚楚可憐的姑娘家,自己瞎心疼什麼呢?
Advertisement
悄然走到隋后,手替他拆起發髻,“我給水生送了點藥過去,敷一宿明兒就能好,侯爺不用擔心。”
“多謝夫人。”隋把兵書放回案幾上,子稍稍坐正了些,方便染為他拆開頭發。
“你啥時候會講人話了?”染譏笑一聲,“跟我說多謝,今兒吃到魚開心壞啦?”
“嗯,是。”
他如瀑似的長發垂披下來,染隨意扯了扯,“水生都告訴我了。”
隋心下一滯,側頭向染,“他……都告訴你了?”
“是啊,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就那麼害怕讓我知道?”染半俯下子,單肘拄在案幾上,笑道:“凡事你別鉆牛角尖,臉面這東西得看開些。”
“你……一點都不在乎嗎?”
隋在染的眼中看不到半點吃醋的痕跡,果然,一點都不在乎自己。不在意凌恬兒為什麼會出現在那里,為什麼要出手幫他們打跑潑皮。覺得這就是一件極其普通的事。
“我在乎什麼?”染不明所以,重復地道:“我不在乎的,這事兒取決于侯爺自己。”
隋沉沉地嘆息一聲:“我想睡了。”
“不,你還沒有沐浴呢,我去找金生過來幫你。”
“免了,我很累,明日再說吧。”
不顧染游說,隋已劃著椅回到床榻邊,又把自己巍巍地挪回床榻里,作一氣呵,雖然作不能跟正常人相比,但整個過程已比半年前快了太多。
染自去外面打了盆溫水回來,趴在他側道:“我知道你心不好,不洗就不洗。不過你總得子洗洗腳吧?”
隋背對著不吱聲,子快要弓一只蝦。
“好吧,那我自己手。”反正早就輕車路了。
Advertisement
染匍到他的腳邊,正準備幫他褪掉凈,卻被隋出手攔下來。他子反應沒有那麼敏捷,卻想要竭力制止住。
“你別對我這樣,你不欠我的。”隋的雙眼紅到發漲,“作為夫人,你為我做的已經夠多了。我……不會喜歡的。不管是誰,裝著什麼目的,我、我已有妻兒,就不會再朝三暮四。”
染愣神兒半日,眨了眨盈盈的水眸,“你在說什麼呢?你喜歡誰?我怎麼聽不懂啊?”
“你不用對我這麼卑躬屈膝,我不會攆你回雒都也不會休掉你。”這句話隋不知下了多大的決心才說出口,“無論對我如何,我都不會喜歡。”
“是誰?”染直勾勾地盯著隋,試探問道:“你們今日在縣上見凌恬兒了?”
“什麼?”隋瞬間睜圓了眼,急吼吼地道:“你不是說水生都跟你代了嗎?”
“可他沒說你們遇見凌恬兒了呀?”染這才明白水生跟自己瞞了什麼。
狠狠甩開隋的手臂,莫名地發起脾氣道:“原來如此,你們是見救兵了呢?侯爺好大的魅力,東野的郡主都能境來救你了。區區幾個潑皮都能鬧出這麼大的靜,趕明兒不會幫你招兵買馬吧?”
“你……我……胡說八道!”隋真想一頭扎進被子里捂死自己算了!
這都是什麼事啊,老在面前丟人現眼,還一次比一次嚴重。他的臉面何在?真真是被自己吃到肚子里了。
染把一只手指銜在微微張闔的齒間,忖量半晌,道:“水生和你不想讓我知道,是擔心我會生氣?”
終于繞明白這個圈,再脧向隋時,他燒紅的整張臉都快躲進長發里。
Advertisement
“那東野小郡主真喜歡你呀?該不會是跟蹤你吧?上次我就說不會輕易罷休的。”
“染,你給老子閉!!”
回到東野皇宮的凌恬兒代屬下,要他們只字不提在錦縣上發生的事。回來的有些晚,已錯過用晚膳的時間。兩個姐姐替圓了謊,草草地蒙混過去。
凌澈生辰的正日在后天,兩個兒皆是提早趕來赤虎邑。大郡馬和二郡馬狄真都是凌澈的左膀右臂,分別在舊都和丹郡監管著東野的行政和軍事。
以往都是奏疏呈報,此番見到國主的面,自然得先談公事再聊私事。二人及其屬下重臣都惦記在凌澈面前多多展示。朝堂眾人心知肚明,大郡馬和二郡馬都有可能為東野的下一任國主。
“姐夫他們還在父親那邊,想必今夜不能早歸。”凌碧兒親手替小妹倒了碗馬茶,“快點喝了吧,我讓婢子去膳房拿點吃食過來。”
凌恬兒大口大口地喝起來,“還是姐姐們在邊好呀,什麼都有人替我想著。這次你們多住些日子再走。”言語間一大碗馬茶已然見底。
“這可不,就是我們想待著,父親也不能同意。你見過哪個地方群龍無首?凌碧兒又替小妹倒滿一碗,“你呀,慢著點喝。去北黎一趟,怎麼連頓飯都沒混上?”
“他們那邊的飯味道吃不慣。”
“吃不慣?”凌仙兒盯小妹的神,“離開隋夫人的視線,你都沒有上前跟他講一句話?這一趟下來你都沒有出現在他面前?”
“沒有啊。”凌恬兒裝得特別自然,“我前不久見過他,老在他面前晃悠,怕他嫌煩。”不想姐姐們往下細問,趕繼續說:“我想為他找個醫高明的大夫。”
Advertisement
“你要治他的?”兩個姐姐齊聲追問。
“他下半截兒不是一點知覺都沒有,我見過他行走的樣子。就是有點吃力,模樣特別丑,看起來像個老頭子。”凌恬兒語氣帶笑,漆黑的眼眸里都帶著亮。
夜半,大郡馬走回寢宮中來,凌碧兒一直等候著,見夫君回來立馬起服侍。年約三十,與大郡主同歲,二人算是青梅竹馬的一對兒。倆人親多年,育有四個孩子。
氏和凌氏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親戚,兩族通婚者不計其數。在外形和格上都和凌澈很相像,以至于很多人第一次見到他,還以為他是凌澈的親兒子。
“和父親談得順利嗎?”凌碧兒接過婢子手中的臉帕,親自為拭,“這次沒有帶孩子們過來,父親有點不高興了吧?”
攬住凌碧兒的腰肢往自己這邊一帶,讓坐在自己的上,“帶孩子們過來,你哪能把力放在恬兒上?”
“父親那邊是什麼口風,要給恬兒找夫家了嗎?”凌碧兒靠在的肩膀上,“我倒是很想讓嫁家。就是你的那幾個族弟未必能我小妹的眼。”
“博、浦慶都不?恬兒到底想要什麼樣的男子?”皺起眉頭,“今兒下晌,你們姊妹三人去了哪里?”
凌碧兒便一五一十地跟詳述一遍,“你切莫輕舉妄,聽恬兒的口氣,父親在這件事上沒有明確反對,并且此人能讓父親屈尊去見,可想而知他的重量。不過……一個廢人而已,恬兒多半是過個新鮮勁兒。”
“原是那位將軍。”點了點頭,“我倒是聽說過他的戰績。國主到底有何打算,這是要利用北黎人嗎?”
“你也知道父親從不在國事上與我相說,我哪里能猜他的心思。恬兒這邊暫且還好說,只是仙兒那邊有點棘手。”
“仙兒怎麼了?是不是狄真那廝有什麼舉?”
“咱們這次沒有帶博他們過來,狄真卻把他的胞弟狄格帶來了。一直藏著掖著,仙兒也遮遮掩掩地沒有對我講。還是咱們的人發現了,我猜他們是想給恬兒和那小后生制造機會。”
“狄真!”一拳頭砸在桌幾上,把上面的瓷震的差點掉到地上,“狄氏就是這麼有心眼會算計,這些年好都是他們丹郡在撈,咱們恪盡職守地監管舊都,什麼好都沒有得到!”
猜你喜歡
-
完結97 章

廢後謀
那年,看見他,仿佛就已經中了她的毒,日日思念不得見,最後她嫁給了他的兄弟,他只望她能幸福,哪成想,她的夫君一登基,就將她打入皇陵守孝,既然如此,他不會在放過與她相守的每一個機會了,就算全天下人反對,又如何,他只要她。
17.4萬字8 9476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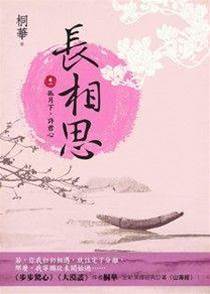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17 -
完結353 章

嫁給白月光的宿敵之后
蘇明嫵本該嫁進東宮,和青梅竹馬的太子舉案齊眉,然而花轎交錯,她被擡進了同日成婚的雍涼王府中。 恨了符欒半輩子,住在王府偏院瓦房,死前才知策劃錯嫁的人是她的心頭硃砂白月光。 一朝重生,蘇明嫵重生在了洞房翌日。好巧不巧,她正以死相逼,要喝避子湯藥... 天子幼弟符欒,十四歲前往涼州封地,十六歲親自出徵北羌,次年得勝被流箭射穿左眼。這樣心狠的大人物,大家心照不宣,蘇明嫵這朵嬌花落入他的手裏,怕是要被磋磨成玩物不止。 尤其是這個美嬌娥,心裏還掛念着她的小情郎,哪有男人能忍得? 雍涼王聞此傳言,似笑非笑點了點頭,好巧,他深以爲然。 婚後滿月歸寧那日,經過樓閣轉角。 “嬌嬌,與母親講,王爺他到底待你如何?可曾欺負你?” 符欒停下腳步,右邊長眸慵懶地掃過去,他的小嬌妻雙頰酡紅,如塊溫香軟玉,正細聲細氣寬慰道:“母親,我是他的人,他幹嘛欺負我呀...” 她是他的人,所以後來,符欒牽着她一起走上至高無上的位置。
53.8萬字8.18 570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