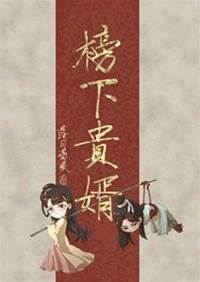《風月狩》 第1章 第 1 章
夜濃稠,繁星漫天,那細細的一弦月早就不見了蹤影,長安城中燃燒的野火,卻照亮了半邊天幕。
直欞門開啟一道,風聲里夾帶著馬蹄聲和嘈雜的驚嚎哭,迫不及待涌進室。守門的家仆探腦袋,慌張地回稟:“叛軍沖進嘉會坊,把靖王及家眷押走了!”
嘉會坊和待賢坊只隔了一條直道,登上后院的小樓,能看見靖王府邸的全貌。
燈火照亮一屋眷的臉,每個都惶惶。
楊夫人穩住心神擺了擺手,“守住大門,千萬不要放人進來。”
其實大家都知道,叛軍的鐵蹄早就踏破了城門,區區一扇府門,哪里擋得住千軍萬馬。
家仆著頭皮說是,重新退了出去,急促的腳步聲走遠了,庭院里寂然,只有遠源源不斷的呼號,隨風忽高忽低地,在四面八方盤桓。
驚魂未定的寧公主開始泣,靖王是的叔父,一個閑散王爺,平時既不參政也不領兵,最的無非人和斗,饒是如此,還是被凌從訓的大軍逮住了。
反正每一次天下大,出帝王家的人都難逃厄運,靖王府近在眼前,下一個怕是就要到自己了。
“母親……”寧公主抓住了楊夫人的袖子,“陛下的親軍呢?守城的金吾衛呢?怎麼放任這些逆賊在城里橫行?”
楊夫人無奈地了公主一眼,什麼話都沒說。
半年前公主下降的長子重威,那時辛家滿門榮耀,斷沒想到駐守朔方郡的凌從訓會起兵謀反。現在天翻地覆只在頃刻之間,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會如何。像激流上漂浮的樹葉,也許一個浪打過來,百年族就不復存在了。
“父親和阿兄怎麼還不回來?”居安仰頭問自己的生母,“叛軍會不會……”
Advertisement
后面的話被母親劉氏捂在了掌心里。
京兆辛氏與清河崔氏、扶風竇氏、會稽顧氏并稱四大世家,這四家累出高,子孫皆在朝。辛家家主辛道昭任史大夫,朝廷在察覺叛軍攻城之前,就把他們那些臣僚全部召集宮,共襄對策去了。
在漩渦的中心,究竟能不能全而退全看命,大家心里都明白,唯有居安年輕莽撞,口而出。
這話引得站在窗前的居上回頭了一眼。
就這一眼,讓居安心頭直打突,對于這位長姐,始終帶著畏懼,倒不是因為嫡庶的差別,是因為經常不長姐的脾氣。
當然這點對于居上來說也很苦惱,戰火侵襲下的每個人都惶惶不可終日,居上同樣慌張。但那張過分漂亮的臉上扮不出愁腸百結的味道,仿佛天生缺了這種表,以至于皺皺眉,也看不出是在發愁,更像是種居高臨下的挑剔。
居安又嚇得窒住了,居上無奈地調開了視線。
這時,遠的喧囂愈發激烈起來,約約在向待賢坊蔓延。幾位嬸嬸臉發白,因辛氏不分家,三房并居在大宅里,外面大,眷們就匯集在一起,偌大的廳房中,時刻能聽見驚愕的氣和抑的哽咽。
二嬸李氏開始擔心自己的丈夫,對媳婦喃喃:“你父親在象州……不知道怎麼樣了。”
三嬸是會稽顧氏出,相比李夫人更鎮定些,說:“凌氏是北地族,早前和我們也有些。再說大族之間常有聯系,好多都帶著姻親呢,料想不會把我們怎麼樣的。”
說起姻親,眾人的視線立刻滿屋子轉,結果轉了半天,發現家里一個姓凌的都沒有。
辛家和凌家,不曾通婚過。
Advertisement
三嬸咽了口唾沫,“那個……沒關系,若是他們對四大家不利,就別想堵住悠悠眾口,全天下都會唾棄他們借機鏟除門閥,妄圖一家獨大。”
其實這推斷也不是沒來由的,凌從訓率領大軍謀反,名聲固然不好聽,但也不能顧頭不顧腚。如今的世家大族雖不像以前那樣與皇帝共天下,但威還在,錯綜復雜的關系網,幾乎延到關外去,不管誰是下一任皇帝,都離不開士族的支持。
要支持就有底氣,至三嬸是這麼認為的。
這話也給了居上啟發,推開窗戶朝外張,才發現院子里仆婦和婢一個都不見了。屋頂上傳來箭羽破空的聲響,咻咻地,從高呼嘯而過。
楊夫人心驚膽戰,招手道:“快回來,別站在窗前。”
居上卻在思考另一樁事,“阿娘,拿兩盞燈籠,掛在閥閱上吧。”
所謂的閥閱,是士族題記功業的柱子,有意在閥閱前掌燈,無非是在賭,如果凌從訓曾下令剿滅四大家,反正誰也逃不掉;但若是沒有,亮明來歷,反倒可以避免被誤傷。
三嬸很贊這個主意,“對對對,掃的叛軍不止一批,萬一哪個瞎驢帶頭闖進來,我們一屋子眷就全完了。”
可是外面聽令的人沒了,誰去傳話又了問題。
眾人面面相覷,居上當仁不讓,轉道:“我去。”
這下楊夫人急了,斷然說不行,“外面箭滿天飛,要是出了事,我怎麼向你父親代?”
居上想笑一笑以示安,奈何笑不出來,便放了語調說:“我只是去傳個令,會快去快回的,阿娘放心吧。”
說完就要出門,居安也不知吃了什麼熊心豹子膽,跳起來道:“阿姐,我陪你去。”
Advertisement
居上沒說話,算是默許了。姐妹兩個從門里出去,著黑,趕到了前院。
結果前院并不如們設想的那樣,忠仆們手持利刃嚴陣以待,事實上前院一個人都沒有,連那個打探消息的也不見了蹤影。
居安呆呆看向阿姐,“人呢?”
居上嘆了口氣,“這種時候,誰也顧不上誰了。”
所以掛燈這件事,就不能指別人了。好在工是現的,燈籠也是現的,居上接過靠在墻邊的撐桿,一手提著一只燈籠,示意居安給開門。
居安猶豫地了,燈籠圈口的照著的臉,長得極白凈,那五便尤其深刻,黑的眼睫,紅的,乍看之下悍然如妖。
“還是別出去了吧,”居安著嗓子說,“萬一遇上叛軍怎麼辦?”
可居上不是深居閨中的孩,有著異于一般貴的旺盛生命力,從小父兄帶騎馬箭,雖然準頭到今天依然沒練好,但膽子大,也有力氣,這個時候義無反顧地擔負起了長姐的責任,“你不用出去,站在檻接應我,等我掛完一個,把另一個遞給我。”
居安還在推搪:“說好了讓下人掛的……”
“玉!”居上沒空應付,不耐煩地喝了聲。
這下居安泄氣了,因為自己從小弱多病,父親給取這個名字,是希長壽。初衷當然是好的,小時候也不覺得有什麼不便,但年紀越大就越別扭,別人什麼珠啊寶的,“”。對于長姐說的王八是王八,是,當然也不認同。
居上行很果斷,決定的事就要盡快落實。外面兵荒馬,說不定前一刻們還在糾結,后一刻大門就被撞開了。
遂不由分說把一盞燈籠遞給居安,自己側耳在門上聽,街道上很安靜,叛軍暫且還未攻進待賢坊。
Advertisement
所以此時不掛更待何時?忙給居安使眼。居安也知道不能再磨蹭了,一手提燈,一手去抬門閂,可惜門閂太重,單手抬不起來,居上沒辦法,放下撐桿和燈籠,與合力才把門打開。
奇怪,門門外仿佛兩個世界,坊院的空氣里混雜著木頭燒焦的味道,加上不時遁逃經過的城中百姓,整個世界都浸泡在倉惶里。
居上觀了一會兒,確定沒有叛軍,才提起裾邁出門檻。
辛家門庭顯赫,閥閱自然也高大,那兩柱子平時不怎麼留意,但到今日升燈卻看清了,左邊的“閥”上記錄功業,右邊的“閱”上記錄著宦歷。隨著燈一點點升高,辛氏祖祖輩輩的輝煌,也在眼前詳細演繹了一遍。
然而探風的居安,幾乎嚇得魂兒都快飛了。長姐仰頭向上頂燈的時候,從延平門闖進來一隊人馬,因隔得太遠看不清面目,但那些人穿著黑甲,一看就不是城守軍,正沖著這里快速而來。
“阿姐!阿姐!”居安跺腳,“快回來!快呀!”
居上也聽見馬蹄聲了,一種莫大的恐懼扼住嚨,連看都沒敢回頭看一眼,匆匆提跑進門,手忙腳和居安一起上了門閂。
“怎麼辦,他們一定看見你了!”居安崩潰地比劃,“那些叛軍,騎著高頭大馬殺進來了!”
居上當然知道大事不妙,忙捂住的,把拖到一旁。自己定了定神,就著門朝外看,看見空的坊道上來了許多人馬,在的滅頂恐懼里微微停駐了片刻,轉瞬又掠過去了。
所以是功了嗎?這樣險象環生卻逃過一劫,至證明目前安全了。
居上和居安一頓雀躍,快步回到后院,把剛才的經歷和眾人說了,大家生出了劫后余生的慶幸,說凌從訓謀逆歸謀逆,道義還是講的,至沒有縱容麾下,搞什麼株連。
寧公主卻從這些話里品出了別樣的苦,捂住臉嚎啕大哭起來。自己是已經出嫁的兒,正因為不在室了,改天換日的時候有幸保住一條命,夫家的人,便都去念逆賊的好了。
公主的哭聲突出重圍,眾人紛紛尷尬閉上了。居上不知道該怎麼安長嫂,只好握一握的手,溫聲道:“等明日父親回來,就知道宮的境況了。”
好在這一夜還算平安,廝殺聲從四更起漸漸平息,大家戰戰兢兢等待天亮,焦急地發現這段時間竟出奇漫長。
宅躲得比家主還深的仆從們開始走了,壯了膽出門打探風聲,說誰家被搶掠了,誰家又死了幾個人。
長安城風聲鶴唳,每道坊門都被封了起來,沒人知道朝中的局勢。全家整整等了一天一夜,越等越害怕,及到第二天晌午過后,才聽見外面傳來拍門聲。
眾人都跑出來,門打開了,看見灰頭土臉的家主,拎著一串角黍邁進門檻。走到廊前,木木地坐在了臺階上,一臉菜道:“今日端午,祿寺置備了廊下食1,歷國公下令賞角黍,我吃不完,就帶回來了。”
猜你喜歡
-
完結824 章

凰權弈:戰神王妃有點毒
星際時代的女武神鳳緋然,一朝被人暗算身亡,無意間綁定鹹魚翻身系統竟然魂穿到古代,原主還是被人欺辱的嫡出大小姐,看她鳳緋然如何逆天改命、獨步天下。
141.3萬字8 15203 -
完結1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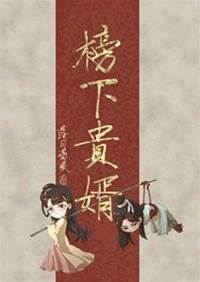
榜下貴婿
預收坑《五師妹》,簡介在本文文案下面。本文文案:江寧府簡家世代經營金飾,是小有名氣的老字號金鋪。簡老爺金銀不愁,欲以商賈之身擠入名流,于是生出替獨女簡明舒招個貴婿的心思來。簡老爺廣撒網,挑中幾位寒門士子悉心栽培、贈金送銀,只待中榜捉婿。陸徜…
46.9萬字8 7765 -
完結215 章

妻憑夫貴
穿越成剛出嫁的農村小媳婦,沒有極品親戚,因為原身就是最大的極品! 蘇婉好不容易把新婚丈夫以及丈夫的一家,好感度從負數刷正了,卻發現她的丈夫很有可能是日後高中拋妻娶貴女的宰相。 她是休夫呢,休夫呢,還是休夫呢?感謝中國好基友楚琰同學做的封面,還有小天使須淺也給做了,封面放不下,等渣作者研究完代碼就放文案里。
68.5萬字8 160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