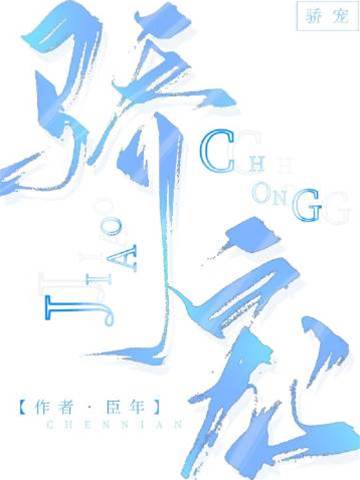《換親姐姐重生了[八零]》 第17章 017
跟葉蔓分開后,彭玉良沒有回學校,而是到了郵局排隊打電話。
其實學校里也有電話,憑借他跟萱萱的關系,借電話用一用也不是什麼難事,往常打電話回廠子里找家里人,他都借系里的電話。
不過今天這個電話,若是被人聽了去,他就完了。
所以彭玉良寧可麻煩一點,多花點錢也不圖這個便捷。
好在他今天運氣不錯,前面只有三個人排隊。到他時,他進去就掏出小本子,撥打了開關廠的電話找谷建城。
過了幾分鐘,谷建城才慢吞吞地過來,接起了電話:“喂,你哪位?”
聽到這聲音,彭玉良心里就窩火。他惱怒地吼道:“是我,彭玉良!”
電話另一頭停頓了片刻,接著響起谷建城若無其事的聲音:“哦,是你啊,彭大學生,什麼時候把說好的500塊給我啊?”
聽到谷建城這東西事沒辦,竟然還問他要錢,彭玉良怒火中燒,咬牙切齒地說:“谷建城,事沒辦好,你他媽還好意思問我要錢?你不是說上個月月底就跟葉三妮結婚了嗎?為什麼沒結?”
這東西,收了他的定錢,不認真辦事就算了,結果事沒辦也不通知他,還想繼續從他這里訛錢。若非葉蔓今天找過來,他還要一直被蒙在鼓里。
彭玉良自詡聰明,卻被一個老婆都跑了的無能男人玩弄于掌之間,他又氣又怒,將從葉蔓那兒的氣一并發在了谷建城上,說話也沒了往日的斯文。
但他實在低估了谷建城的不要臉。
谷建城比他嗓門還大:“你他、媽的還好意思提這個!老子被你害慘了,結婚當天葉三妮臨時悔婚,老子的臉都丟了,我沒找你算賬都是好的了,你還找我!”
Advertisement
結婚當天悔婚?彭玉良怎麼都不相信這是靦腆子溫的葉蔓能做出的事,他火大地說:“你不是說搞定了葉家嗎?你們這麼多人,連個人都搞不定?”
廢!
“媽的,報警把公安和婦委會的人都找來了,你這麼能,你去搞定公安啊!”谷建城也窩火。
彭玉良被堵得說不出話來。
他深呼吸了幾口氣,稍稍冷靜下來,如今他腳踏兩只船的事已經被葉蔓知道了,葉蔓嫁不嫁給谷建城都不重要了,原來勞神費財的計劃也沒進行的必要了。
他對彭玉良說:“這個事我也不追究了,不過事你沒辦好,我給你的500塊定錢你得還給我!”
這才是他來找谷建城的目的。
葉蔓一開口就要把前面三年談花的錢都要回去。可他一個窮學生,哪一下子拿得出幾百塊啊。既然谷建城沒辦好他代的事,自然該把錢還給他。有了這筆錢,他也可以從葉蔓那里換回照片和自己的書信。
可谷建城卻不這麼想:“屁的定錢,老子辦婚宴幾十桌,結果婚沒結,還倒了一筆錢進來,丟人丟到了姥姥家,沒問你要損失費就不錯了。你小子還問我要錢,想得!”
撂下這句話,谷建城直接掛了電話。
聽到電話里傳來的嘟嘟聲,彭玉良差點氣得砸了電話,這個狗東西,難怪老婆不要他,跟別的男人跑了呢!
白白損失了500塊錢,彭玉良這樣于算計的男人自然不甘心,但谷建城遠在長永縣,他一時半會兒也拿這家伙沒辦法,只能暫時按下。
可從谷建城這里要錢行不通,那這筆錢從哪兒找呢?
饒是彭玉良腦子靈活,一時半會兒也沒什麼好辦法。
Advertisement
扶著桌子想了好幾分鐘,外面排隊打電話的人都在催他,他才重新拿起了電話。
這次,彭玉良將電話打到了紡織廠,找他爸。
他父母都是紡織廠的工人,所以當初高考填志愿的時候他才會填溪化市高等紡織工業專科學校。
“玉良啊,今天怎麼想起打電話回來,是有什麼事嗎?”彭父接到電話,關切地問道。
這會兒打電話不方便,價格又很貴,沒什麼重要的事,大家都是寫信,極打電話的。
彭玉良抿了抿說:“爸,把媽那個工作指標賣了吧。”
“啊?”彭父吃了一驚,“咱們不是說好了,先留著,等你畢業再說的嗎?”
工作指標多難得啊,這工作他還想留給自家人呢!
彭玉良也不想,可上次給谷建城那500塊已經掏空了家底,還找親戚借了點錢,父母肯定沒法在短時間再湊齊500塊的。而跟萱萱這樣出生富裕家庭的姑娘談對象,也不可能再像跟葉蔓一樣,約會就去公園里坐坐,頂多再花幾錢看場電影就完了。
去外面飯店里吃飯,買服和小禮之類的,每個月總得來上那麼一兩回吧。他每個月十幾塊錢的津可不夠用,以前還有葉蔓和家里時不時地補他一點,現在可都沒了。不弄點錢,怎麼繼續談?還有大半年才畢業呢!
“爸,我畢業后會學校會分配工作,這個工作指標咱們家也用不上,媽這些年辛苦了,讓早點退休,回家養養吧!”彭玉良話說得極好聽。
可知子莫若父,彭父很清楚兒子不會無緣無故突然提這個,他問道:“你是不是在外面遇到了什麼難?”
彭玉良猶豫了一下,說了實話:“爸,三妮找到市里來了,要我把以前談花的錢折算給,不然就拿……我以前寫給的信去學校里找領導。”
Advertisement
“好,那我回家跟你媽商量商量。”彭父答應了。他家好不容易出了個大學生,可不能被葉三妮給會毀了。
彭玉良聽到這話不由著急,咳了一聲說:“三妮說只給我三天時間!”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彭父的聲音好似一下子老了十幾歲:“我這就去找你媽商量,賣得這麼急恐怕要被人價!”
這可是家里人好不容易弄來的工作指標,還想傳給下一代的,就這麼賤賣了,彭父心疼啊。
彭玉良連忙安彭父:“爸,等我畢業分配出來就是干部份,咱們家也不缺一個普通工人的工作指標。最遲你明天就得給我寄過來,要加急啊!”
“知道了!”兒都是債,彭父掛斷了電話。
今天不趕時間,葉蔓沒坐公,邊走邊逛街。
走了半個小時左右,葉蔓看到路邊有一家照相館,便走了進去。
照相館老板立即熱地招呼道:“同志,要照相嗎?”
葉蔓點頭,從包里拿出一捆信,從里面挑了幾封,將信紙取出來,一一攤開擺在桌子上:“老板,對著拍,拍清楚點啊,洗出來之后要能辨認出字跡。”
老板……
開照相館幾年了,他還是頭一回看到錢多得給信紙拍照片的,手抄一遍多省錢。
不過送上門來的生意沒有推出去的道理,老板提醒葉蔓:“四寸的五錢一張,六寸一塊錢一張,你這得拍好幾張。”
葉蔓一揮手:“沒關系,拍吧,清晰點,洗四寸大小的就夠了。”
這可都是證據,花幾塊錢存檔很有必要。要的也不是照片,而是膠卷,照片洗出來后,照相館會把膠卷一塊兒放進袋子里給顧客,以后想洗照片可以拿膠卷去照相館洗。要是彭玉良給玩的,想賴賬,把這照片洗個幾十張出來,撒在他們學校里,讓他直接社死。
Advertisement
既然對方沒有意見,老板便拿起相機將這些信紙拍了下來,讓葉蔓了錢,然后提醒:“明天下午就可以來取了,記得帶收據過來。”
“好,謝謝老板。”葉蔓將收據塞進包里,繼續往《溪化日報》的方向走去。
門衛大叔一看到,很是稀奇,笑瞇瞇地招手:“小同志,又來找熊記者啊?”
葉蔓含笑點頭:“對,大叔,他今天在嗎?”
門衛大叔搖頭:“沒呢,估計是出去采訪了,你下午再過來吧!”
人不在,葉蔓只好謝過門衛大叔,先去吃飯,又在附近的市場上轉了一會兒,大約下午兩三點的時候,再次來到報社。
熊記者已經回來了。葉蔓站在辦公室門口輕輕敲了敲門,等熊記者抬頭,立即揚起笑容喊道:“熊記者,您好!”
熊記者看著就很無語:“你怎麼又來了?那篇報道前幾天已經發了!”
葉蔓笑瞇瞇地點頭:“我們已經看到了,梅主任還說您寫得真好,是咱們學習的榜樣……”
熊記者不吃這一套:“我還有工作,有什麼事你直說吧!”
葉蔓馬上從包里拿出工作本,遞了上去:“熊記者,耽誤您一會兒,我是來向你匯報工作進展的。目前,我們活的贊助商品都已經到位了,請您過目。”
熊記者拿著本子念了出來:“紅星牌12寸黑白電視機一臺,大米三袋(20斤)、面三袋(20斤)、餅干兩斤裝10袋,單人打谷機一臺,男皮鞋各五雙,啤酒六箱……我說你們這是打算開商店嗎?”
吃的、穿的、用的,甚至連機都有,獎品是打算堆一座山嗎?
葉蔓搖頭笑道:“當然不是,這不是縣里的各單位太熱,鼎力支持咱們婦聯的工作嗎?”
熊記者已經見識過葉蔓的狡詐和難纏,本不信這話。他放下本子說道:“這種事,寫信就行了,你沒必要特意跑一趟。”
葉蔓臉上燦爛的笑容散了一些:“我有點事要來市里理,就想著干脆直接來找熊記者您,面對面,講得更清楚點。”
“你這又是準備去找哪個單位?”熊記者隨口問了問下個倒霉蛋的名字。
葉蔓出一個很勉強的笑容:“不是,是私事。找我前男友,他背著我早就跟系主任的兒好上了。”
熊記者……
這樣的事為什麼要跟他說,他一個大男人不知道怎麼安小姑娘啊。
“你想開點吧,回頭讓你們梅主任給你介紹個更好的。”熊記者勸道。
葉蔓點頭,將拍過照的那幾封信拿了出來:“我是來向他討債的。他多次寫信向我索要財,轉頭就戴著我省吃儉用給他買的手表陪系主任的兒逛街,拿我寄的錢給對方買服。他攀了高枝,要跟我分手,我認了,但他不能拿我當傻子,這些錢都是我辛辛苦苦每個月攢的,他得還給我。”
這種狗的事歷來吸睛,辦公室里其他幾個記者不自覺地放下了手頭上的工作,豎起耳朵聽八卦。
坐窗邊的那個記者更是按捺不住,替葉蔓打抱不平:“這也太不是東西了吧?吸著原友的,拿去討好新友,還大學生呢,怎麼能干出這麼不要臉的事!”
有了帶頭,其他幾個記者也議論起來,都是指責彭玉良太沒道德,良心都被狗吃了。
葉蔓垂眸,這還只是冰山一角呢,更壞的是他還算計嫁給一個二婚家暴老男人,可惜手里沒有直接的證據。
熊記者聽著同事們七八舌地討論,睨了葉蔓一眼:“你跑我辦公室里來說這個干什麼?我又不是你爸!”
“熊記者您若是想當我爸也不是不可以,我正好缺個干爸!”葉蔓打蛇隨上。
熊記者被的不要臉震驚了,難得的詞窮。
旁邊幾個記者聽到這話,起哄:“熊哥,答應啊,這麼漂亮聰明的干兒,比你家那兩個皮小子好多了。”
“閉吧你!”熊記者丟了個眼刀子給對方,看著葉蔓抬了抬下,“到底想干什麼,直說吧!”
葉蔓有些憾,要有個干爸撐腰,下次葉國明他們兩口子再冒出來,直接把熊記者推出去,能省多事啊。算了,人家不愿意也不能勉強。
垂下眼瞼說道:“彭玉良說他一時半會兒拿不出這麼多錢來。我們約定好了,三天后在紡織學校的大門口面,我怕他耍花招,所以想麻煩熊記者到時候陪我走一趟,在市里我也就認識你們。”
猜你喜歡
-
完結96 章
再見及再愛
家道中落,林晞卻仍能幸運嫁入豪門。婚宴之上,昔日戀人顏司明成了她的“舅舅”。新婚之夜,新婚丈夫卻和別的女人在交頸纏綿。身份殊異,她想要離他越遠,他們卻糾纏得越來越近。“你愛他?”他笑,笑容冷厲,突然出手剝開她的浴巾,在她耳朵邊一字一句地說,“林晞,從來沒有人敢這樣欺辱我,你是第一個!”
17.2萬字8.18 20793 -
完結1965 章

盛寵名門佳妻
旁人大婚是進婚房,她和墨靖堯穿著婚服進的是棺材。空間太小,貼的太近,從此墨少習慣了懷裡多隻小寵物。寵物寵物,不寵那就是暴殄天物。於是,墨少決心把這個真理髮揮到極致。她上房,他幫她揭瓦。她說爹不疼媽不愛,他大手一揮,那就換個新爹媽。她說哥哥姐姐欺負她,他直接踩在腳下,我老婆是你們祖宗。小祖宗天天往外跑,墨少滿身飄酸:“我家小妻子膚白貌美,給我盯緊了。”眾吃瓜跟班:“少爺,你眼瞎嗎……”
284.1萬字8 29639 -
完結43 章

我的愛生生不息
雲知新想這輩子就算沒有白耀楠的愛,有一個酷似他的孩子也好。也不枉自己愛了他二十年。來
4.3萬字8 13074 -
完結493 章

甜心玩火:誤惹霸情闊少爺
訂婚宴當天,她竟然被綁架了! 一場綁架,本以為能解除以商業共贏為前提的無愛聯姻,她卻不知自己惹了更大號人物。 他…… 那個綁架她的大BOSS,為什麼看起來那麼眼熟,不會是那晚不小心放縱的對象吧? 完了完了,真是他! 男人逼近,令她無所遁逃,“強上我,這筆賬你要怎麼算?”
90.4萬字8 37776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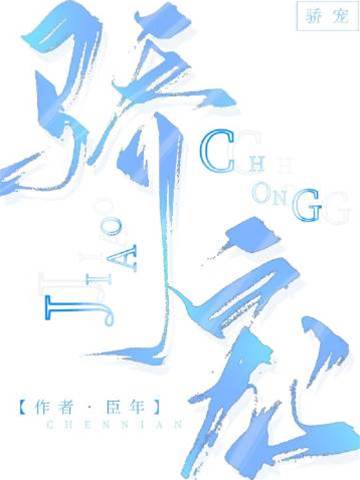
驕寵
作為國家博物館特聘書畫修復師,顧星檀在一次美術展中意外露臉而走紅網絡,她一襲紅裙入鏡,容顏明艷昳麗,慵懶回眸時,神仙美貌顛倒眾生。后來,有媒體采訪到這位神顏女神:擇偶標準是什麼?顧星檀回答:我喜歡桀驁不馴又野又冷小狼狗,最好有紋身,超酷。網…
31.3萬字8 4218 -
完結503 章

沈總別虐了,夫人和新歡約會上熱搜了
結婚三週年紀念日那天,沈澤撂下狠話。 “像你這樣惡毒的女人,根本不配成爲沈太太。” 轉頭就去照顧懷孕的白月光。 三年也沒能暖熱他的心,葉莯心灰意冷,扔下一紙離婚協議,瀟灑離開。 沈澤看着自己的前妻一條又一條的上熱搜,終於忍不住找到她。 將她抵在牆邊,低聲詢問,“當初救我的人是你?” 葉莯嫌棄地推開男人,“沈總讓讓,你擋着我約會了。”
36.8萬字8 33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