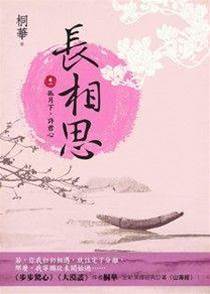《春江花月》 第 71 章 第 71 章
村民們聚在一起,用畏懼的目,看著那個正朝自己走來的男子。
他停在了他們的面前,說:“我乃義刺史李穆。你們奔我而來,我卻未能保護你們周全,你們不幸遭此劫難。此為我李穆之過,請我一拜!”
他作揖謝罪。
村民們再次驚呆了。
片刻之后,反應了過來,一聲“李刺史!”亦不知是哪個起的頭,七八十人,無不涕淚加,向著李穆跪拜在地,不住磕頭。
李穆上前,將人一一扶起,一番。
眾人嚎啕大哭了一番,漸漸收了眼淚。
雖遭遇意外不幸,但終于死里逃生,更沒有想到的是,他們要投奔的李穆,長路奔波,涉險追趕來此,為的,不過就是救回他們這些命如螻蟻的幾十個普通之人,怎不人激涕零?
想到往后若得他庇護,于這世,真能得一立足之地,則比起旁人,朝不保夕,又不知幸運多。
“李刺史,我們回鄉投奔于你,往后你會不會撇下義,我等空盼一場?”
一個膽大之人,終于鼓足勇氣,小聲問道。
李穆道:“父老兄弟面前,我李穆立誓。我人在,義便在!離開之日,亦是為驅逐胡獠,北伐中原!”
眾人沉默了片刻,當中那個方才被西金士兵以尿淋面的漢子,突然面激之,從人群后拉出一個年,高聲道:“李刺史,我兩父子皆愿當兵,隨你北伐胡人!”
“我也愿!”
“我也愿!”
一時,立誓發愿之聲,爭相而起,此起彼伏。
Advertisement
李穆目掠過眾人之面,笑道:“得父老兄弟如此助力,我李穆之愿,何愁不酬!”
……
小魚很是懂事。
獲救后的這些天,遲遲不見自己母親面,似乎也猜到了什麼,不再像一開始那樣,總不停地詢問。
只一個人悄悄地垂淚,很是悲傷。
神也被的緒染,心愈發沉重,又不放心李穆,天天晚上睡不好覺。
如此牽掛了數日,這一天的傍晚,忽然得到消息,李穆回來了。
隨他一道回的,還有被他救回的那些回歸民眾。
很難形容得知這消息時,的心。
那一刻,甚至還不及長舒一口氣,便幾乎是飛奔著出了屋,裝作吹風,來到了通往刺史府前堂的那道垂花門前,等著他的出現。
但他卻一直沒有現。
天漸漸地暗了。
刺史府的前頭,似乎有人不斷出,雜聲可聞。
這里卻靜悄悄的,耳畔只有晚風掠過那叢枯竹時發出的空的沙沙之聲。
神立在垂花門旁那座殘破石亭之前,心里忽然涌出了一種被這世界忘了的失落之。
下怏怏心,轉回了屋。
阿也回了,臉上終于出了笑容,說老天總算沒喪盡良心。小魚的父親和阿兄都沒事,今日跟著李郎君一道回了,兩人都要投軍。方才剛接走小魚,又托阿轉話,對照顧了阿魚數日的刺史夫人激不盡。
終于聽到一個不幸中的萬幸消息,神抑郁著的心,才稍稍好轉了些。
阿出去,沒片刻,提了食盒,送晚飯進來。
Advertisement
神何來胃口,順口問李穆。
阿說,李郎君一回來,就被蔣弢給攔走了,兩人此刻應還在前頭的議事堂里。
神猶豫了片刻,打開食盒,看了一眼,遲遲不鋪開。
阿便猜到了的心思,暗嘆了口氣,卻笑道:“我瞧李郎君回來,連口氣都沒歇,又被蔣弢給去了,此刻想必也沒吃晚飯。不如我再多準備些,小娘子送去,問問他們吃不吃?”
見神不語,自己轉去了。
……
瓊樹打著燈籠,神提著食盒,朝前堂走去。
傍晚出刺史府的那些人,此刻都已去了,前頭也安靜了下來。
城中一切資都極短缺。
照明的火燭,更是不夠。所以刺史府里也無庭燎。天黑下來后,便黑魆魆一片。
只有地上一團燈籠的昏,照著神前行的腳步。
到了那間議事堂外。遠遠地,看見門窗里出一團昏暗的,知李穆和蔣弢此刻應該還在里頭,下心中突然涌出的一陣張之,放輕腳步,提著食盒,慢慢地走了過去。
三天之前,侯定派人送來一信,道自己讀了李穆手書,深有,本也不和大虞敵對,更無意競逐中原,只想守住仇池祖業,蒙李穆不棄,又釋放了他的長子侯離,愿會上一面,共商大計。正好數日之后,是他五十壽日,他隨信附上邀,道李穆到時若能蒞臨,則是他莫大榮幸。
蔣弢皺眉道:“我怕此人不信。探子消息,道前些時日鮮卑人在仇池時,他還笑臉相迎,應是締了盟約,鮮卑人才走的。侯定此人,老巨猾。鮮卑人一走,就又向你示好,邀你仇池,怕另有謀算,萬一不利。”
Advertisement
“依我之見,為穩妥,不如尋個借口婉拒,邀他來義商議。”
李穆慢慢搖頭:“善左右逢源者,疑慮必重。我初來義,勢單力薄,雖不懼戰,但若能化戰為友,大有裨益。侯定也知我想結于他,邀他來義,他怎肯來?不虎,焉得虎子。他既邀我,我去便是。臨機制變,也非難事。”
蔣弢和他相多年,早知他必迎難而上,便也不再多勸。只道:“好在我瞧那侯離,因忌憚其弟,倒是真心要投靠于你。我前幾日和他暗遞消息,他應允到時倘若有變,必會出手相幫。另有一事……”
蔣弢搖了搖頭:“可惜,時日太過短促,此地又如此偏荒,怕是尋不到人了。”
“何事?”李穆問。
“那侯離倒是一心想要我們和他父親結盟,連他父親早年私事,也和我說了個底朝天。道他生母從前乃是茲國世,貌,又通樂理,擅胡琵琶,聲名在外,當年曾引侯定和谷會隆競相求親,其母嫁了侯定,生侯離。不想沒幾年,仇池生,谷會隆指使叛軍作,攻襲城池,破城搶走其母,獻給谷會隆。其母不堪□□,也是個烈子,竟自刎而死。后侯定平,聯合茲興師復仇。西金當時還只是彈丸之地,為息事,谷會隆將他母親尸首送回,道是死于叛軍之手,和自己毫無干,又贈金銀珠寶,買通茲,茲退兵,侯定孤掌難鳴,不得已,含恨作罷。”
“此事過去已有二十多年。那侯定卻對妻子依舊懷念,每每想起,更覺虧欠。多年以來,一直珍藏他母親生前所用的那把胡琵琶。不料數年之前,遭遇一場大水,將琵琶浸壞了。侯定夢見其妻流淚,責備他毀了自己珍,致間不寧,愈發愧疚,尋人想要修復,再將琵琶燒給。奈何琵琶乃他生母自創,乃六相十八品,和尋常的四相十五品很是不同。莫說修復原音,便是能彈奏,知音的,當世怕也尋不到幾位。侯定只能作罷,但至今,仍是一樁心事。侯離被其弟侯堅排,卻至今還能保有世子之位,其父對其母的愧疚之心,怕也是緣由之一。”
Advertisement
“侯離之意,乃是我漢人里多有技藝高超之樂工,若能尋訪到一位,修復了琵琶,了卻侯定多年心病,他必會激。”
蔣弢搖頭。“這一時之間,去哪里尋如此之人?只能罷了!”
“蔣二兄,可否讓我試試!”
神再忍不住,一下推門而,走了進去。
。
猜你喜歡
-
完結97 章

廢後謀
那年,看見他,仿佛就已經中了她的毒,日日思念不得見,最後她嫁給了他的兄弟,他只望她能幸福,哪成想,她的夫君一登基,就將她打入皇陵守孝,既然如此,他不會在放過與她相守的每一個機會了,就算全天下人反對,又如何,他只要她。
17.4萬字8 9476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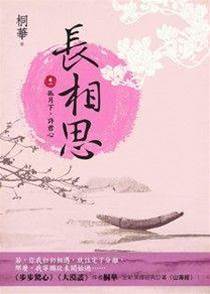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17 -
完結353 章

嫁給白月光的宿敵之后
蘇明嫵本該嫁進東宮,和青梅竹馬的太子舉案齊眉,然而花轎交錯,她被擡進了同日成婚的雍涼王府中。 恨了符欒半輩子,住在王府偏院瓦房,死前才知策劃錯嫁的人是她的心頭硃砂白月光。 一朝重生,蘇明嫵重生在了洞房翌日。好巧不巧,她正以死相逼,要喝避子湯藥... 天子幼弟符欒,十四歲前往涼州封地,十六歲親自出徵北羌,次年得勝被流箭射穿左眼。這樣心狠的大人物,大家心照不宣,蘇明嫵這朵嬌花落入他的手裏,怕是要被磋磨成玩物不止。 尤其是這個美嬌娥,心裏還掛念着她的小情郎,哪有男人能忍得? 雍涼王聞此傳言,似笑非笑點了點頭,好巧,他深以爲然。 婚後滿月歸寧那日,經過樓閣轉角。 “嬌嬌,與母親講,王爺他到底待你如何?可曾欺負你?” 符欒停下腳步,右邊長眸慵懶地掃過去,他的小嬌妻雙頰酡紅,如塊溫香軟玉,正細聲細氣寬慰道:“母親,我是他的人,他幹嘛欺負我呀...” 她是他的人,所以後來,符欒牽着她一起走上至高無上的位置。
53.8萬字8.18 5723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