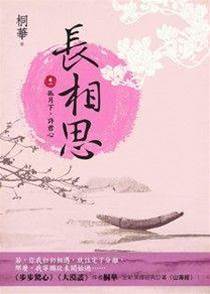《殊色誤人》 第92頁
他有些驚訝,原來小公子長這個樣子,可能因為年紀小,眉眼像極了夫人,有些男生相,雖然瘦瘦弱弱,看起來就像春草說的弱多病,但眼睛頗為機靈。
婁復撓了撓頭,對崔茵道,“夫人,前面是個鎮子,大司馬說要在鎮上停留幾日,他先行一步,去給小公子尋郎中了。”
崔茵了阿珩的小腦袋,心里五味雜陳,“多謝。”
婁復知道這幾日趕路,夫人一心撲在小公子上,大司馬似乎有些不開心,但也不知道為什麼,也沒有跟夫人說過幾句話。
總之就是怪怪的。
……
這一趟人馬頗多,蕭緒桓人去賃下了一院子,比客棧要清靜些。
這日上午在路上時還艷高照,有些悶熱,傍晚收拾好東西住進院子里,庭前的芭蕉葉上開始落雨。
阿珩里嗚哇嗚哇的,小手指了指寬大的葉片,崔茵心里的一塌糊涂,帶他站在檐下,“下雨了,珩兒,這是雨。”
“鳴窗更聽芭蕉雨,一葉中藏萬斛愁【1】……”
鄭嬤嬤聽見了,輕聲道,“夫人說什麼愁不愁的,郎中來了,請他來給小公子診脈吧。”
Advertisement
崔茵笑了笑,“請進來吧。”
阿珩大概是見過太多蓄著胡子的郎中,手里提著藥箱,小臉瞬間垮了下來,搖搖晃晃走了一步,撲倒在崔茵懷里。
崔茵狠了狠心,抱起他來,哄道,“不吃藥藥,只給郎中看看。”
阿珩可憐的看著阿娘,地了一聲,“阿娘……”
他平時不說話,偶爾蹦出幾個字來,鄭嬤嬤對崔茵說別著急,有些孩子說話就是晚一些,何況阿珩小小年紀遭過那麼多罪,也沒在母親邊長大。
這是他頭一次開口阿娘,吐字清晰,聲音乎乎的,崔茵心里化了一灘水。
抱著他給郎中診完了脈。
郎中搖搖頭,“夫人,小公子這是打娘胎里帶出來的心疾,小的醫不,沒什麼法子。”
崔茵自然知道,“我只是想問問,他前些天了驚嚇,原先吃的藥也停了,可有妨礙?”
郎中道;“脈象上來看沒什麼大礙,只是小公子弱,千萬注意別染上風寒,小的開一副調理的藥,可以一直服用,但也只能是一時之策,安神養心。”
Advertisement
鄭嬤嬤帶人下去抓藥,天漸漸暗了下來,雨聲淅淅瀝瀝,崔茵用晚飯陪阿珩玩了一會兒,沐浴之后,小家伙便困了,如今非要阿娘在旁邊才睡得著。
他抓著崔茵的袖子,一會兒就睡了過去。
崔茵替他掖了掖被角,想了想,春草過來,問,“大司馬呢?”
春草小聲道,“奴婢聽婁復那會兒攔住了郎中,問他要一副退燒的藥,我問他是誰病了,他支支吾吾的,奴婢猜是大司馬病了,夫人要不過去看看吧。”
崔茵有些慚愧,這幾日忽略他的,也不曾說過幾句話,忙找來一件自己穿過的裳放在阿珩枕邊,將自己的袖子出來,親了親小家伙的臉蛋,“你和嬤嬤仔細看著他點,千萬別踢被子。”
自己撐了一把傘,朝旁邊院走去。
崔茵敲了敲門,里邊沒有靜,但燈還亮著,便輕手輕腳推門進去。
蕭緒桓躺在床上,俊朗深邃的面容上略帶著憔悴,崔茵輕輕坐到床邊,聞到一清新的皂角香氣,見他頭發還沒有完全干,皺了皺眉,拿來干凈的帕子,替他頭發。
Advertisement
其實也很想念他。
就是一切說開之后,有種說不出來的不自在,一心撲到阿珩上,其實是在逃避。
看得出來,蕭緒桓其實心并不喜歡阿珩,只是礙于自己,才盡心盡力替阿珩著想,給他們母子悉的時間。
崔茵手里的作輕無比,生怕驚醒他。
目落在他臉上,遲遲不想移開。
頭發得差不多了,見他似乎真的發燒,臉上微微有些紅,手探了探他的額頭。
剛剛上去,果然手滾燙。
剛想收回來,卻見人已經醒了,捉住的手,眸幽深,靜靜看著。
崔茵被他嚇了一跳,慌忙想收回手,那還在病中的人力氣卻比大了不,直接將人往懷里一帶,崔茵一下子倒在了他上。
“夫人還肯來看我。”
蕭緒桓聲音沙啞,嗓音低沉,喃喃道。
崔茵聽的心里酸酸的,回抱住他,不語。
“蕭某還以為,夫人有了孩子就不在乎我了。”
輕笑,聽他繼續埋怨道,“我怎麼能跟夫人的孩子吃醋拈酸呢。”
“是我不好,”聲道,掙扎著想起來,“快蓋好被子,你還發著燒呢。”
Advertisement
那人眼底如深潭,滾著暗。
面頰緋紅,一直盯著崔茵,“夫人再讓我抱抱。”
崔茵無奈,實在是拒絕不了他的溫聲低語,只好重新靠過去,卻被他細細親了過來。
大概是怕傳染給風寒,只親了親的耳垂,低聲卻越來越重。
崔茵當然察覺到了他的變化,推了推他,“你還病著,別胡鬧了,快起來。”
他不依不饒,崔茵力氣抵不過他,被熱氣和他的呢喃染得暈暈乎乎,睜眼看他捧著自己的臉,眼睛半睜,目迷朦又帶了一懇求。
猜你喜歡
-
完結97 章

廢後謀
那年,看見他,仿佛就已經中了她的毒,日日思念不得見,最後她嫁給了他的兄弟,他只望她能幸福,哪成想,她的夫君一登基,就將她打入皇陵守孝,既然如此,他不會在放過與她相守的每一個機會了,就算全天下人反對,又如何,他只要她。
17.4萬字8 9476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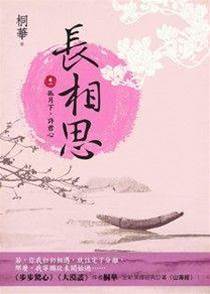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17 -
完結353 章

嫁給白月光的宿敵之后
蘇明嫵本該嫁進東宮,和青梅竹馬的太子舉案齊眉,然而花轎交錯,她被擡進了同日成婚的雍涼王府中。 恨了符欒半輩子,住在王府偏院瓦房,死前才知策劃錯嫁的人是她的心頭硃砂白月光。 一朝重生,蘇明嫵重生在了洞房翌日。好巧不巧,她正以死相逼,要喝避子湯藥... 天子幼弟符欒,十四歲前往涼州封地,十六歲親自出徵北羌,次年得勝被流箭射穿左眼。這樣心狠的大人物,大家心照不宣,蘇明嫵這朵嬌花落入他的手裏,怕是要被磋磨成玩物不止。 尤其是這個美嬌娥,心裏還掛念着她的小情郎,哪有男人能忍得? 雍涼王聞此傳言,似笑非笑點了點頭,好巧,他深以爲然。 婚後滿月歸寧那日,經過樓閣轉角。 “嬌嬌,與母親講,王爺他到底待你如何?可曾欺負你?” 符欒停下腳步,右邊長眸慵懶地掃過去,他的小嬌妻雙頰酡紅,如塊溫香軟玉,正細聲細氣寬慰道:“母親,我是他的人,他幹嘛欺負我呀...” 她是他的人,所以後來,符欒牽着她一起走上至高無上的位置。
53.8萬字8.18 570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