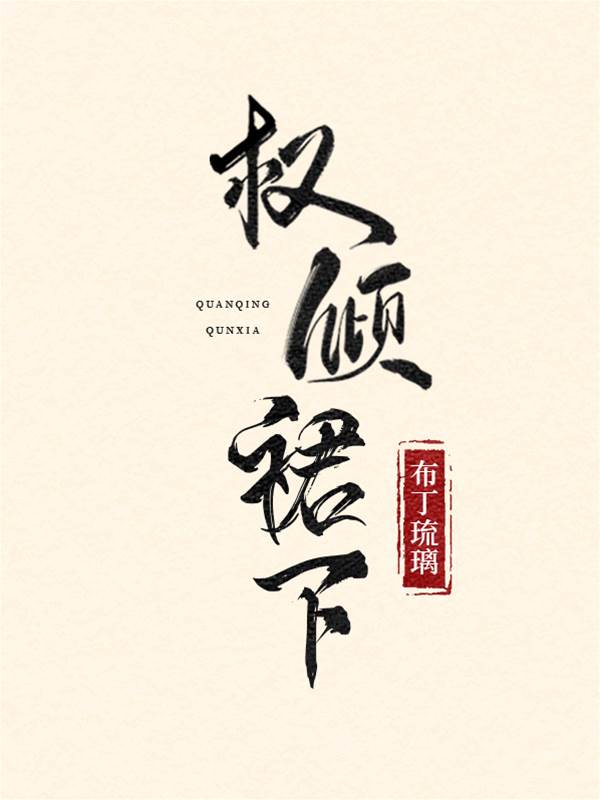《神醫魔后》 第68章 我們做過的事,賴不掉的
福祿院兒。
夜景盛跪在老夫人面前,一臉苦地道:“不是兒子不爭氣沒魄力,實在是兒子怕那個小賤人手打母親。那小賤人從小子就野,現在更野,瞧那樣子是什麼事都敢做的。所以兒子當時要是了手,萬一真的一掌打下去可怎麼辦啊?”
蕭氏也在邊上跟著道:“二爺從小就孝順,心里想著的盡是母親。他不是不能上戰場,也不是練不好功夫,以前他就同我說過,家里父親上戰場,大哥上戰場,如果他也去了,那誰來孝順母親呢?穆千秋脾氣不好,別看做主母時一副賢良淑德的樣子,那都是裝的,要是他也離開家去建功立業,穆千秋在府里一定會欺負母親的。”
夜景盛連連點頭,說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好男兒志在四方,誰不想被外頭的人高看一眼?誰愿意像我這樣一被人提起就說是沒上過戰場的將軍?兒子是舍不得母親,兒子想在家里盡孝,所以兒子寧愿被人脊梁骨,也不能冒風險把母親一個人留在家里。”
老夫人也被說得不停抹眼淚,最后干脆跟兒子抱頭痛哭。
蕭氏松了一口氣,哄好了就行,這老太太只想著自己沒面子,因為二兒子沒替自己出頭,沒打死穆氏和夜溫言,可是生了好大的氣。可也不想想,真要打了,這事兒能善了嗎?
母子二人正哭著呢,外頭一個婆子快步進了前廳。老夫人趕問:“肅王府那邊怎麼樣?可有什麼靜?”
婆子答:“肅王府沒有什麼大靜,只是找了人連夜修繕府墻和府門,卻沒聽說他們有要找四小姐算帳的意思。老奴問了肅王府的侍衛,侍衛們對此事閉口不言,看樣子還有幾分忌憚,也不知道是因為沒面子,還是因為怕了四小姐。”
Advertisement
“怕那個丫頭作甚?他可是王爺啊!他姓權啊!”老夫人實在不明白六殿下這個腦回路,明明以前暴脾氣的一個人,怎麼遇著了夜溫言的事兒,就跟個頭烏似的?“他的王府被連砸兩回他都能忍,這到底是在忍什麼?難不還等著我們家給他出氣?”
婆子不吱聲,能看到打聽到的就這些,實在也給不出什麼建議來。
老夫人氣得揮揮手讓下去了,然后轉問蕭氏:“書白你說,那肅王府到底在怕什麼?”
蕭氏想了想,道:“四姑娘不是得了一塊暖玉嗎?”
一提到暖玉,老夫人的心又了兩下。是啊,暖玉,那是先帝賜給嫡子的珍貴件兒,如今卻到了夜溫言的手里。能讓六殿下把暖玉都舍出來的,除了當今太后,也就只有炎華宮能做到了。莫不是肅王府在怕炎華宮?炎華宮真的是夜溫言的靠山嗎?
再問:“你真的相信那死丫頭跟炎華宮有關系?”
蕭氏說:“母親,寧可信其有,也不信其無。”
“你什麼意思?”老太太推開兒子,跟蕭氏發了火,“你是在替那個死丫頭說話?”
蕭氏趕解釋:“沒有,兒媳怎麼會替說話,兒媳只是分析這個事。母親,肅王府都沒有作,咱們為何當這個先鋒呢?不如靜觀其變,即使要,那也該肅王府先。”
老夫人咬咬牙,“肅王府如何沒?他們不是派人把這事兒告訴給太后,太后不也將景盛到永安宮去訓斥了嗎?”
“只是訓斥,卻沒提賠償,也沒提把四丫頭進宮一塊兒訓斥,母親覺得這是李太后一慣的作風嗎?”
老夫人想了想,覺得蕭氏說得也有幾分道理,那合著今天晚上這一場架白打了?
Advertisement
“母親,四姑娘邪乎,咱們別主招惹。”蕭氏又對說,“李太后派來的那位扶悠姑娘也還在府里呢,今晚這樣的事要是換了從前的崔嬤嬤,一準兒就出來給六殿下出氣了。可扶悠連面兒都沒,這還不能說明問題嗎?”
老夫人想問問說明什麼問題,可轉念一想,還用問麼,這說明李太后不想跟夜溫言正面剛,卻偏偏們這些人傻了嘰的把得罪人的事給做了。做還沒做好,惹了自己一腥。
“罷了,就聽你的。”老夫人終于了下來。可還有一事不明白,“那死丫頭口口聲聲說什麼頭七又是什麼意思?哪有給活人辦頭七的?瘋了不?”
蕭氏答:“咱們管瘋沒瘋呢,反正要辦,我就把攤子給支起來,自己都不嫌晦氣,咱們怕什麼?”
老夫人琢磨琢磨,到也是這個理。最好辦個頭七能把那死丫頭真給送走了,那可就萬事大吉,一定要大慶三天。
夫婦二人終于離開福祿院兒,蕭氏打從離了老夫人的視線就開始鐵青著臉,越是往遠走臉就越難看。夜景盛不解,問道:“你這是怎麼了?方才不是還好好的?”
蕭氏狠狠瞪向他,“方才好好的是在給你臉,是不想在你娘跟前讓你下不來臺,也不想讓那老太太以為我有多欺負他兒子。但是夜景盛你告訴我,你都背著我做了什麼?”
夜景盛心下一驚,第一反應就是常雪喬和夜無雙的事被發現了。
這可把他給嚇夠嗆,臉都白了,額上也冒汗了。蕭氏借著錦繡提著的燈籠仔細瞧他,越瞧越心涼,“你我夫妻這麼多年,你要納妾也納了,想當家主,我也幫著你當上了。沒想到到頭來你居然背著我做那樣的事!夜景盛你對得起我嗎?”
Advertisement
夜景盛害怕了,他從來都是怕這個妻子的,再加上蕭書白本就比他大,一教訓起人來就跟姐姐訓弟弟似的,這麼多年他一直都害怕蕭氏發火。
雖然一直都在為常雪喬謀劃,可這事兒拖了十幾年都沒辦,可見有多難,也可見他對蕭氏有多忌憚。眼下他還沒做好準備呢,突然就被蕭氏提起來,他該怎麼說?他該怎麼做?
夜景盛不說話,只顧著在心里瞎想。蕭氏的話到是沒停,說起這件事那是滿腔悲憤。
問夜景盛:“我堂堂寧國侯府大小姐,是不是在你心里從來都比不上個丫鬟?以前有一個梳頭的柳氏,如今你又盯上了熙春,你有沒有點兒出息啊?你就是要找人,是不是也該找些能上得去臺面兒的?你出去打聽打聽,誰家的妾一說出去全都是丫鬟上位?你讓我這張臉往哪放?你讓夜家的臉面往哪放?你是家主了,為什麼就不能有個家主的樣子?”
夜景盛打從熙春二字從蕭書白里說出來之后,他就沒怎麼聽后面的話,只顧著慶幸了。
原來說的是熙春,他還以為是說常雪喬,真是嚇死人了。
不是常雪喬就好,只要不是常雪喬,是誰都無所謂。他必須得讓雪喬母萬無一失風風的府,絕不能一早就被蕭氏發現,再徹底打。
他終于開了口,回蕭氏一句:“熙春的事也是沒有辦法,你知道從前我們讓做了什麼。”
“我是知道。”蕭氏將聲音低,努力穩著自己的緒,“但是我只知道你答應給拿回賣契,再給一筆銀子讓去過不用侍候人的好日子。可你干了什麼?你又給了什麼?”
蕭氏舉起一只鐲子,“眼吧?以為是我常戴的那只?我告訴你,不是,這是我從熙春手腕子上擼下來的,我的那只早被夜溫言那個死丫頭拿去換了。這破鐲子不是什麼好,扔到外頭最多值二三十兩銀子,可是我蕭書白、我堂堂寧國侯府大小姐卻一戴就是十幾年。夜景盛,你以為我圖什麼?我為什麼戴著它?”
Advertisement
蕭氏越說越激,“因為親之前你與我見面,你喝醉了酒侵犯了我。過后你給了我一對鐲子,說是娘留給你的唯一念想。你家老夫人養尊優,一天沒喂過你,你是娘喂大的。所以你心里頭念著娘,一直把他的隨帶著。你將鐲子送給我,說以后一定好好待我,與我舉案齊眉,白頭到老。我信了你的鬼話,把這鐲子看得比價值連城的珠寶都重要,這麼多年一直戴在腕上。”
吸吸鼻子,一邊說一邊抹眼淚,“但我也是有份的人,我不能讓人瞧見自己雙手一就出兩只廉價的鐲子。所以平時我只戴一只,空出一只手去撐你們夜家的門面和我自己的臉面。結果你到好,居然把另一只鐲子從我這里走,轉送給了熙春那個小賤人。夜景盛你告訴我,你想干什麼?”
夜景盛讓說得好生沒臉,特別是蕭氏提起當年他醉酒之事,讓他更是添了幾分惱怒。
當初為何會醉酒還做出那樣的事,他到現在都想不明白。明明他不喜歡蕭書白,也不想娶蕭書白的,可就是因為那次的事,讓他不得不把這個人給娶回家。
眼下蕭氏借著熙春的事把這茬兒提起來,他一時火氣不住,當時就怒道:“我不想干什麼,但是熙春改了主意,著我納為妾!的要求我賴不掉,你也賴不掉!我們做了什麼你自己心里清楚!”
猜你喜歡
-
完結2728 章
冥婚霸寵:天才萌寶腹黑娘親
她,華夏古武最強傳人,醫手遮天的變態鬼才,卻因一次意外,穿越成了林家不受寵的廢物小姐。一睜眼,發現美男在懷,與她在棺材裡正上演限製級大戲……六年之後,她浴火重生,帶著天才萌寶強勢歸來,手握驚天神器,統率逆天神獸,大殺四方!虐渣男,踹賤姐,沒事練練丹藥,錢包富的流油,日子過的好不快活。可某日,某男人強勢將她堵在牆角:「你要孩子,我要你。」她輕蔑一笑,指間毒針閃現寒芒:「再靠近一步,你就沒命要了。」某寶道:「想要我娘親,我得去問問我的乾爹們同意不同意!」
476.1萬字8.18 113267 -
完結2346 章

快穿:女配又跪了
位面金牌任務者池芫被系統坑了,被逼無奈前往位面世界收集上司沈昭慕散落在三千位面世界中的靈魂碎片。作為一名優秀的任務者,池芫對于攻略這回事信手拈來,但是——三千世界追著同一個靈魂跑,攻略同一個人這種坑爹的設定,她拒絕的好嗎!一會是高冷的校草、…
424.5萬字8 51719 -
完結109 章

良宵誰與共
寡婦娘親改嫁到了蕭家,經歷了各種酸甜苦辣,終于把徐靈蕓養大了,到了徐靈蕓挑選夫婿的年紀,卻發現自己早就已經被蕭家的長子給盯上了……,相愛當中,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43.3萬字8 22217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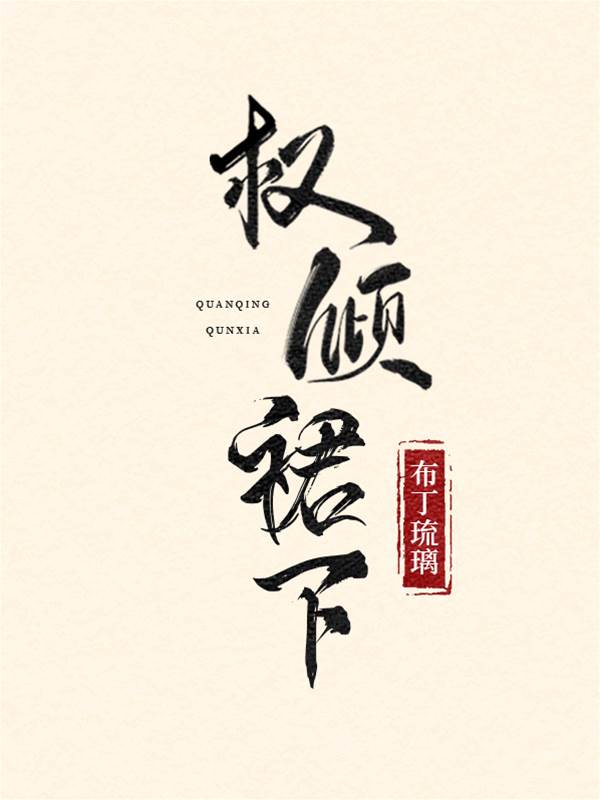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14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