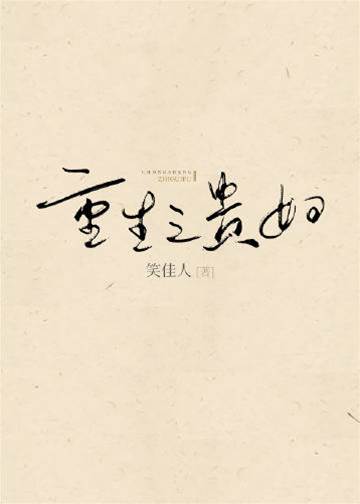《重生后我養了五個權臣》 第72章 不要隨便動手動腳
晏傾傷重,剛施針用過藥,原本正趴在榻上閉目養神,整個人都看著病怏怏的。
此刻上只著一件白長衫,松松垮垮地披著,好幾滲了白衫,如同紅梅綻放在了積雪里,妖異而綺麗。
偏生他睜開雙眼仰視著時,眸中又著幾分惹人惜的破碎孱弱之態。
秦灼兩輩子加在一起,也很難見到晏傾這般模樣。
看到此此景,很難用言語來形容是什麼覺。
加之屋中燈火被夜風吹得明明滅滅,外頭又下著大雨,夜深沉地不像話。
竟讓有種在幻境的錯覺。
“咳咳……”還是晏傾的咳嗽聲驚醒了。
秦灼回過神來,看到他傷的難以彈,還不忘攏了攏衫,便走到邊上把打開的窗戶合上了。
窗一關,風雨聲就隔絕了大半,顯得屋里越發安靜無聲。
好似彼此做什麼作都能聽得清楚。
秦灼轉回到榻邊,面上表淡淡的,“你既一直醒著,應當聽到我方才問你話了,為何不答?”
晏傾低聲道“在想該怎麼說。”
“那你慢慢想,我就在這等著。”秦灼在榻邊坐下,握住了晏傾的手腕把了把脈。
這人的脈像是真的怪。
每次看著人都快死了,可回回都不死,過了那危急的幾個時辰,就又沒事了。
這次也只是脈象虛浮一些,外傷重,看著嚇人,死是肯定死不了的。
難怪花辭樹說走就走,連一句話都不留。
晏傾沉默了許久,忽然開口問道“你什麼時候學了醫?”
秦灼自然不能跟他說是上輩子久病醫,隨口回了一句,“你不知道的時候。”
晏傾道“左手把脈也能把得準?”
“準或不準,都不重要。”秦灼給晏傾把完脈,就把他的手擱回了原,“我只不過是在給你點時間想清楚怎麼同我說那些事罷了,不如我奉勸你一句,若是在想怎麼蒙我,還是省省。””
Advertisement
說著,掀開他上那件輕薄的白外衫看了一眼。
只一眼,秦灼就把外衫披了回去。
晏傾這滿的傷上了藥也不管用,不過他明明可以有別的法子進宮,偏偏選了敲登聞鼓這條最罪的路子。
堂堂帝師的徒,面圣竟然要做此舉,說出去誰都得問一句“是不是腦子壞了?”
這痛也該他自己著。
r> 不然,長不了記。
偏偏晏傾這會兒開了口,“這傷就是看著嚇人,其實也不是很痛。”
“這樣說來還是我多管閑事了?”秦灼起,居高臨下地看著他,“就該讓你去牢里待著,天天不應地地不靈,只能在那等死才知道痛是不是?”
晏傾張了張,卻只說出來兩個字,“不是……”
“算了,不說這些。今天我想問的也不是這個。”秦灼忽然有些煩躁。
強下心里的不悅,正道“不管你今日做這些所圖為何,都擔了罪名,保住了無爭,我該謝你。但也因今日之事,你我暫且綁在了一條船上,在此事塵埃落定之前,你所做之事,亦關乎我命,還往如實相告,我會盡我所能助你,即便幫不了,也會守口如瓶。”
晏傾聽罷,微微皺眉道“你和大殿下不過才相識數日,就要為了他來謝我?”
秦灼頓時有些無言以對。
心下道我說了那麼多,你就聽進去了一句我替無爭謝你?
這人八是滾刀床、杖刑的時候被打壞了腦子!
有些不住火氣,張口便道“是啊,我不能替他謝你麼?我與無爭雖相識不過數日,但我就喜歡他那樣的,等料理完這些七八糟的事,我才好同他談風月,這都是男歡的私事,晏公子非要我把話說的這麼明白做什麼?”
Advertisement
晏傾看著,一下子有些說不出話來。
他愣了好一會兒,忽然笑了,又擺出了那副對誰都客氣有禮的模樣,緩緩道“是我冒昧了。”
“無妨,我不與你計較。”秦灼方才嗆了他好幾句,這會兒沒那麼氣了,還不忘順勢再進一尺,面如常道“還是說說你還有什麼后招,究竟要做什麼吧。”
晏傾漠然道“我確實有后招,但不便相告。”
秦灼想過他會瞞著不說,但是怎麼都沒想到他居然會這麼直接地拒絕,連編謊話遮掩一下都省去了。
“晏傾啊晏傾……”都被氣笑了,“你什麼都不說,今日又何必為無爭這遭罪?既作此舉,總要有所圖謀,否則不是白費心機?”
晏傾道“我自是有圖謀的。”
他微微
側,對上了秦灼那雙眸,沉聲道“你應當聽過,富貴險中求。”
“你求個鬼!”秦灼想也不想地就回了他這麼一句。
若晏傾圖謀別的,也就信了。
富貴?
晏傾生來就有,遲早會有更多的東西,他用得著拿命去換嗎?
秦灼特別想把花辭樹回來給晏傾看看腦袋,站在榻前問道“你被人打壞了腦袋,便當別人都傻了不?你若真要富貴,讓恩師推舉你仕便是,帝師徒,江南名士,又生了這樣一張招人的臉,平步青云指日可待,用得著玩命去搞什麼險中求?”
微微俯,出完全的左手拍了拍晏傾的臉,“你今日這登聞鼓一敲,不但背了滿聲罵名,還招了天子厭棄,樹敵無數,二皇子黨恨不得了你的皮,這般形你若朝,只怕會被啃得連骨頭都不剩……”
“秦灼。”晏傾忽然喚了一聲,打斷了的話。
Advertisement
秦灼道“怎麼?被我當場穿,瞞不下去打算說實話了?”
晏傾眸如墨地看著,語調如常道“說話就說話,不要隨便手腳。”
秦灼看著自己剛剛拍了他臉的左手,頓時“……”
氣氛忽然有點尬。
也怪前世居高位之后,瞧見了合心意的人,不管男總喜歡上手一,其實也不做什麼,就是很單純地一下,邊也沒人敢開口管一管。
況且,審問犯人刑訊供的時候,手上拿著鞭子活著刑什麼的往人家臉上拍,也沒有今夜這般尷尬。
最關鍵的是,從未沒人跟晏傾今夜一般,一本正經地跟秦灼說過不要隨便手腳。
搞得是借機占便宜的登徒子一般。
秦灼心復雜地不得了,面上卻毫不顯,隨口“哦”了一聲,又道“講正事的時候,何必在意這種小事,我方才講到哪了?”
晏傾眼看著裝腔作勢,語調微涼道“說我被人啃得骨頭不剩。”
“對,是這里。”秦灼接著往下說“放著青云之路不走,偏要上刀山下海涉險,晏公子這什麼癖好?簡直聞所未聞,還請你與我說說。”
晏傾面無表地說“我累了,馬上要支撐不住昏睡過去,請回。”
“什麼?”秦灼有一瞬間都懷疑自己幻聽了。
可晏傾說完那句話之后,很快就
閉上了雙眼。
他趴在榻上,一聲不吭的。
秦灼想手去推他,又想起方才被他當做占便宜的,不好再有什麼。
可這廝分明是不想再談這事裝的。
‘昏睡’之前,還知道提早跟說請回。
Advertisement
但凡用了點心,都不該使這麼拙劣的法子誆人。
這哪有點日后以謀略過人著稱那位第一權臣的影子!
倒是像極了十來歲的時候,日日想著要‘居于青山之巔,坐看四海盛景’,一聽長輩要讓他考科舉做大就有一千個由頭不做的那個逍遙年。
“你行!晏傾你真行!”秦灼又好笑又好氣,扔下這麼一句,就轉出了屋子。
門大開著,夜里風大,八要把屋里那人吹得傷上加傷。
一邊想著‘晏傾醒了做什麼?一直昏迷著好了’,一邊手把屋門給帶上了。
庭前風雨加,不水都落在了秦灼上。
抹了抹臉,靜了靜心。
想著晏傾人都在這了,今日說得不多,好歹了些底。
反正他這傷一時半會兒也好不了,還得在這西和園里住些日子,總有自己愿意開口說那些事的時候。
花辭樹明日八也還得來。
侯府的小廝出去請大夫,想來也不是湊巧請到這人的,應該是他與晏傾早有往來,斷不會放任他重傷不治。
謝無爭被足府中,今兒第一天被人盯得出不來,想來也會尋找時機過來探。
秦灼忽然發現,如今的晏傾就像個餌似的,只要在邊擺著,自然就會就有人上門來。
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只管等著便是。
想知道的事也不用著急,反正遲早都會知道的。
秦灼這般想著,心里平和了不,回屋換了服,洗漱完便躺下睡了。
第二天天剛亮,就起來和秦懷山一道去給老侯爺和老夫人請安。
走之前,秦灼特意推開晏傾那屋的門,走到里屋和外屋的中間,掀開珠簾往里看了一眼,人還睡著沒醒。
出來的時候,隨口吩咐小廝“去備些清粥小菜來,等人醒了,讓他用一些。”
站在幾步開外的秦懷山見狀,忍不住道“阿灼,你現在和晏傾好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95 章
醫女冷妃
雖爲庶女,卻長得一副絕美的面貌,一朝得太子看中,欲捨棄嫡姐,納她爲妃,哪知嫡母因此記恨,竟生生將她害死。一朝穿越,天才醫生成了宅斗的犧牲者,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欺負了我的人一個也別想逃開!一場陰謀,揭開重重迷霧,溫文爾雅的太子鋒芒畢露的大皇子還有詭異的三皇子到底誰纔是她的真命天子?且看天才醫生如何護親孃,滅情敵
49.5萬字8 41626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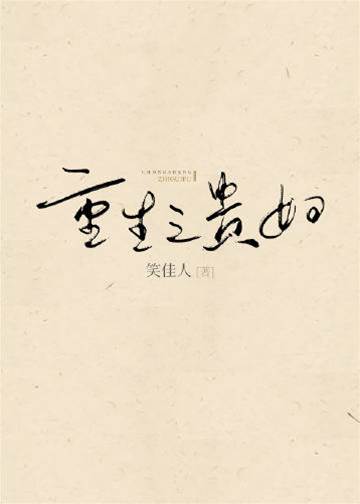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1 187275 -
完結480 章
首輔家的美食小辣妻
現代女強人,21世紀頂級廚神,一朝穿越成了軟弱無能受盡欺負的農婦,肚子裡還揣了一個崽崽? 外有白蓮花對她丈夫虎視眈眈,內有妯娌一心想謀她財產? 來一個打一個,來一雙打一雙,蘇糯勢要農婦翻身把家當。 順便搖身一變成了當國首富,大將軍的親妹妹,無人敢動。 但是某個被和離的首鋪大人卻總糾纏著她...... 寶寶:娘親娘親,那個總追著我們的流浪漢是誰呀? 蘇糯:哦,那是你爹。 眾侍衛們:...... 首鋪大人,你這是何必啊!
90.3萬字7.73 7655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