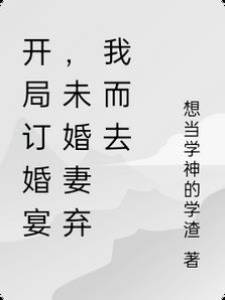《分手後我懷了大佬的崽》 陳喃
母親最終還是葬在了上海,葬禮那天,外婆哭著揪住外公的領,一遍遍斥責:“為什麽!你為什麽啊!囡囡到死都不圓滿,你為什麽啊!”
那時候他不懂這句話是什麽含義。
直到在整理母親時,他才知道,在與父親這場以利益為目的的婚姻之前,也曾有過屬於自己的青蔥歲月,與滿懷期許想攜手共度餘生的人。
離開上海的前一天,他順著母親收藏的那一封封來信上的地址,去了那個已經被劃為建設新區的老弄堂。
在上海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方,這一拆就又是一批價過千萬的家庭崛起。
他最終見到了那個男人。
人至中年,鬢已星星,但氣質依舊溫潤,來幫父母搬家。
他沒看見他的妻兒,許是沒來,也許是終生未娶。
那一刻,他心裏莫名地覺得蒼涼。
即是為了母親,也是為了自己。
他的出生不被期待,甚至伴隨罪孽。
陣陣回苦的口腔,讓他在弄堂口的小賣部買了包煙,店主隻當他是來幫家裏人買的,問都沒問就從櫃臺中將煙丟了過來。
一百塊一包的利群休閑雲端。
他嚐不出口好壞,隻覺得嗆,最終整包丟進了垃圾桶。
……
從上海離開後,路家老太太難過了很久,念叨了好久:“婉嫻這孩子也是命苦。”
命苦什麽呢?
沒有這場強加於之的婚姻,又怎麽會命苦呢?
後來路家生活逐漸恢複了正常,直到陳絳再次出現在路家老宅。
Advertisement
那天路闊打球回來,門口停著路父的車,陳絳姿態無措地站在院中,主屋裏傳來一聲聲老爺子暴怒的吼聲,以及杯盞摔裂的響。
不一樣的長環境,讓路闊比同齡人早些,那一刻他就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麽。
陳絳紅著雙眼轉看他。
他怔了許久,最終轉離開了院門。
陳絳在後了一聲:“路闊!”
像是懺悔,又像是無奈。
那時候恰逢暑假,他當天什麽都沒帶,買了車票回了上海。
說來也是奇怪,林路兩家,隻有四老在地方,才算是他的家,而不是父母在的地方。
那天他到時,林家二老不明況,問他為什麽忽然回來。
他隻回了句:“暑假,想回來。”
當晚路老太太就來了電話,在聽筒那頭久久沉默後,聲音哽咽地說了聲:“阿闊,對不起。”
路家最終還是接了陳絳,腹中的孩子因了驚嚇,早產。
一個男孩兒。
他了鼻子,嬉皮笑臉地回了聲:“您對不起什麽啊?我就是想林家二老了,回上海住幾天而已。”
那天老太太在電話那頭沉默了許久,最終像是哄孩子似的說了聲:“阿闊,你永遠是路家的孩子,爺爺也永遠你。”
不有什麽重要的,他無牽無掛,好的。
他打哈哈說了聲:“您一把年紀了怎麽還這麽麻,行了,老爺子我下棋,我先掛了。”
匆匆收了線。
心底一片空與茫然。
也是那時候,他收到了一則周祈年發給他的視頻,底下配了條文字信息:【這怎麽那麽像你爸?】
Advertisement
他頓了許久,才點開了那則視頻。
深夜醫院的走廊,空寂寥,哇哇大哭的嬰兒,與滿臉喜悅的男人。
他見過自己出生那天的紀念視頻,是老太太拍的,他一人躺在嬰兒車裏,背景裏隻有老太太笑著逗他的聲音,與林家二老的應和聲。
那天,路父在出差,並沒有回來。
怎麽說呢,他沒太大的覺,或者說早就習慣了。
在三歲之前,他其實一直是跟著父母生活的。
直到一次他生病發燒,路遠良與母親皆不在,那天保姆阿姨也因家中有事請了假。
他燒到迷迷糊糊,直到老太太覺得心裏慌得不對勁,來查看,才發現他。
高燒四十二度,他差一點死掉。
事後,老太太跟老爺子氣到給路遠良和路母開了家庭會議。
路遠良愧疚著辯解,說自己公務太忙。
而路母則是一臉淡漠地坐在一旁。
路家二老無奈歎息,最終說了聲:“孩子,以後我們倆帶著。”
自那以後,一直到年,他都是住在老宅。
*
褚雲降打車去了何文秀的住,下車後匆匆往社區跑去。
樓道也老舊,腳步踩踏過水泥樓梯,連帶著整棟樓都好像頻頻震響,到了門口,敲了敲門:“媽!”
寂靜的樓道隻有的敲門聲,屋沒有應答。
忽然想起先前何文秀是給過鑰匙的,急忙打開包翻找了起來。
不常來這邊,鑰匙基本用不到,好在最終還是在夾層裏翻到了。
鑰匙進鎖孔,門板老化,擰了兩遍才打開。
Advertisement
門打開,屋漆黑一片,像是所有的窗簾都被拉起來。
對著門試探地喊了聲:“媽?”
無應答,忽然一陣穿堂風從裏麵吹出來,頓了頓,了進去。
門“咯噠”一聲在後關上,正開燈,忽地從側來一隻手,捂住了的。
*
天逐漸昏黑,書房靜默了幾秒。
路闊緩緩開口:“您怎麽形容陳絳都與我無關,但褚雲降不是,明正娶也好,不清不楚地糾纏一輩子也好,我這輩子也就這一個人了,孩子和我都要。”
說完,兀自轉,打開書房的門走了出去。
*
陳喃臨上車前,又看了眼老太太手裏抱著的孩子,彎了彎,說了聲:“那我就先走了伯母。”
老太太連忙點頭應了聲,看了眼放在一旁的兩盒“妃子笑”荔枝,說道:“好,你說你還專門跑一趟,上次你姐姐也才剛送來不水果,我們倆老骨頭,也吃不完這些。”
陳喃笑了聲:“不礙事,你收下吧。”
說完,上了車,看了眼握著棒棒糖一下下著的小包子,誇讚了聲:“小朋友還可。”
老太太聞聲笑了笑:“阿闊的孩子。”說哇,又慈藹道:“小文子都十六歲了,你也快些找對象,侄子都快年了,你這個小姨還沒家,可不像話了啊!”
陳喃跟路闊同齡,比陳絳小了六歲。
“好。”陳喃溫和一笑,眉眼漂亮到極致,眼神淺淺掠過褚禾易的小臉,道了聲:“那我就先走了。”
Advertisement
老太太笑著往後退了幾步,應了聲:“好。”
*
路闊從院門出來,也沒見著老太太,往胡同口走過去,兜裏的手機忽然響了起來。
顯示來自“媳婦兒”。
他點開了接聽鍵,通話剛接通,那頭就忽然傳來一聲刻意低的驚恐呼聲:“救……救茉茉!”
何文秀的聲音。
他倏地一愣,腳步頓在了原地,急忙問:“您在哪?”
還沒問完,聽筒裏忽然傳來“啪”的一聲,而後就是掛斷的忙音。
他怔了幾秒,本來不及細做思考,迅速上了停在一旁的車。
車子拐過胡同口,車速極快,老太太正牽著褚禾易往回走,過快的車速給嚇了一跳,定神看了眼,才發現是路闊的車。
“哎!”
呼了聲,車子就已經駛沒了影。
猜你喜歡
-
完結264 章

情是回憶如困獸
曾經發誓愛我一生的男人竟然親口對我說: 顧凝,我們離婚吧!”三年婚姻,終究敵不過片刻激情。一場你死我活的爭鬥,傷痕累累後我走出婚姻的網。後來,我遇見師彥澤。站在奶奶的病床前,他拉著我的手: 顧凝,跟我結婚吧,你的債我幫你討回來。”我苦澀的笑: 我隻是個離過婚,一無所有的女人,你幫我討債? 他笑笑點頭,深似寒潭的眸子裏是我看不懂的情緒。 很久以後,我才明白,在他心裏那不過是一場遊戲 .可師彥澤,你知道嗎?那時候,我是真的想和你過一生。
45.2萬字8 19116 -
完結1774 章

荊棘深處
厲墨和唐黎在一起,一直就是玩玩,唐黎知道。唐黎和厲墨在一起,一直就是為錢,厲墨知道。 兩個人各取所需,倒是也相處的和平融洽。只是最后啊,面對他百般維護,是她生了妄心,動了不該有的念頭。 于是便也不怪他,一腳將她踢出局。……青城一場大火,帶走了厲公子的心尖寵。 厲公子從此斷了身邊所有的鶯鶯燕燕。這幾乎成了上流社會閑來無事的嘴邊消遣。 只是沒人知道,那場大火里,唐黎也曾求救般的給他打了電話。那時他的新寵坐在身邊。 他聽見唐黎說:“厲墨,你來看看我吧,最后一次,我以后,都不煩你了。”而他漫不經心的回答, “沒空。”那邊停頓了半晌,終于掛了電話。……這世上,本就不該存在后悔這種東西。 它嚙噬人心,讓一些話,一些人始終定格在你心尖半寸的位置。可其實我啊,只是想見你,天堂或地獄
276.9萬字8 29007 -
連載17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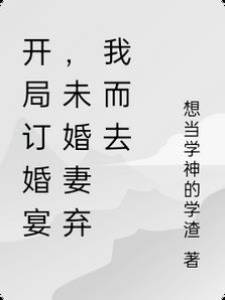
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
微風小說網提供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在線閱讀,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由想當學神的學渣創作,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最新章節及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就上微風小說網。
25.5萬字8.18 24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