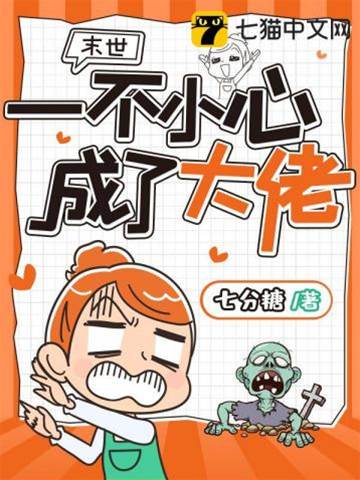《臣服》 第80章
宋綰的話說出口以後,陸薄川的臉沒有多大的變化,就連聲音,都是平穩無波的,他隻是用著那雙深邃銳利的眼看著宋綰,薄輕掀:"你說什麽?"
他的聲音明明那麽平靜,平靜到像是沒有任何變化。
可宋綰卻覺得,他的聲音那麽冷,冷得仿佛抑著低沉狠厲的風雨來。
森寒的冷意朝著宋綰的脊梁骨爬了上來。
宋綰下意識想退一步,的秀拳的握住,不知道為什麽,宋綰來的時候,明明那麽篤定,可這一刻,卻害怕極了。
但是的心髒那麽痛,當年如果不是那個人。那麽所有的一切都不會發生。
爸爸和二哥不會死,的孩子會好好的生下來,或許還好好的活在宋顯章為編製的象牙塔裏,而周竟……
周竟也不會像現在這樣,了無生氣的躺在重癥監護室裏。
宋綰強忍著淚,咬著牙,再次朝著陸薄川道:"我說,那份資料,是溫雅從我上搶走了的,是害得陸家破了產,是害死了爸爸和二哥!陸薄川,一切都是在背後搞的鬼!"
轟隆隆的一聲炸雷,在天空中響起,閃電臨空劈下,幾乎要將天空一分為二。
外麵下起了雨,連綿的雨幕幾乎要將整座城市淹沒。
陸薄川的臉這才一點點徹底冰寒起來,他的所有怒火和戾氣全部藏在皮囊之下,仿佛醞釀著一場更為盛大的暴風雨,他一字一字的問:"宋綰,你知不知道,你在說什麽?"
周圍的人仿佛也到了這裏的氣氛,全部都朝著兩人這裏看了過來。
宋綰忍著淚,害怕極了,可是太恨了。這麽多年來,背著這兩條人命,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
一千四百多個日夜,一場漫長而殘暴的洗腦。
Advertisement
宋綰說:"溫雅呢?溫雅在哪裏!你把找出來,你們是不是把藏起來了?為什麽從我出獄後,就從來沒有看見過!是不是心虛,逃到了別的地方!你把找出來,我要和對峙!"
"綰綰!"鄭則一陣心驚跳!
宋綰怎麽可以在這樣的場合,說出這樣的話來!
知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麽!
然而已經來不及。
"啪--"的一聲,帶著震耳聾的掌聲狠狠朝著宋綰的臉上甩了過去。
宋綰被這一掌甩得整個人差點飛了出去,背後就是餐桌,被甩得朝著餐桌狠狠撞了過去。
宋綰的肚子抵在了餐桌的邊緣,又被彈了回去,整個人摔倒在了地上,生理上的疼痛讓半天沒有緩過氣來!
與此同時,的半邊耳朵嗡嗡作響。臉上火辣辣的疼得麻木。
宋綰捂著半邊臉,耳朵裏一片嗡鳴,的眼淚一滴一滴的滾落下來。
這樣大的衝擊力,讓久久回不過神來,好像聽到了周圍的人的驚聲,又好像沒聽到。
宋綰這才知道,原來陸薄川第一次甩掌的時候,已經是收了力道的。
他真正用氣力來,是這樣的可怕。
宋綰被打的半天沒能從能從地上爬起來。
半邊耳朵出了嗡嗡聲,收不到任何聲音。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的手被一大力狠狠攫住,宋綰回過頭去,陸薄川有力的手扣住纖細的手腕,將用力拉了起來,大步朝著宴會現場離去。
宋綰還被桌子邊緣抵得有些不過氣來,陸薄川人高長,步子邁得又大又快,宋綰打著小跑都跟得有些吃力,更不要說是在這樣的況下。
鄭則也是一陣的心驚跳,宋綰當著這麽多人的麵說出這樣驚世駭俗的話,明天的新聞還不知道要怎麽寫!
Advertisement
他趕跟了上去。
而樓上,季慎年站在二樓,涼薄冷寒的目注視著樓下,他揣在袋裏的手的握拳,一直目送陸薄川和宋綰離開。
隋寧穿著拽地紅,畫著濃豔致的妝容,也看著樓下,直到宋綰被陸薄川強的拉著離開,才小心翼翼的轉覷了一眼旁渾氣冷沉的季慎年。
"你不去幫幫嗎?"隋寧半靠在欄桿上。
既震驚於季慎年的冷靜,又震驚於季慎年的殘忍,這種震驚裏還有種讓人止不住的害怕,這樣的男人。該說他是冷,還是該說他是狠心,隋寧紅彎起一抹弧度,道:"可是當著這麽多人的麵被打了呢,這一鬧,陸薄川還指不定要怎麽對,你竟然在這裏也能看得下去?"
季慎年的臉寒下來,他轉頭看隋寧:"隋寧,別試圖從我這裏試探東西,你會後悔的。"
隋寧隻覺得脊背森寒,但還是笑了笑:"被人這麽對待,難道你就不心疼?"
季慎年揣在口袋裏的長指驀地收,眼底覆著冰寒。
隋寧知道應該停止,不該踩了這個男人的底線,這個男人有多冷心冷,不是沒有見過,但還是忍不住,道:"你該知道,陸薄川人帶去的地方,未必能夠承得住。"
隋寧的話一說出口,心就高高的提了起來。
季慎年上寒氣深重。
隋寧以為季慎年不會回答。
然而季慎年的目又落向了兩人消失的門口,良久,隋寧聽到季慎年的聲音涼得可怕的道:"總要過了這一關。"
隋寧心中卻沒來由的打了一個寒,想起曾經,接了宋綰打給季慎年的電話後,也是這樣問他:"我也是不明白,你既然這樣,為什麽還要把推給陸薄川?你知道陸薄川隻會折磨,殺父害兄之恨,可不小呢,得住這種罪嗎?"
Advertisement
那時候他的眉目凜了下來,轉頭問:"你覺得是為什麽呢?"
隋寧便明白了,這個男人的用意。
不管宋綰是不是和陸薄川隔著海深仇,但宋綰陸薄川比誰都深,對他的和愧疚隻要一天不消除,那麽就永遠會留在陸薄川邊。
的心就永遠在陸薄川上。
也隻有這樣,才會漫無止境的承陸薄川帶給的任何傷害。
可是人的和恨都是有極限的,隻要時間足夠久,就算是多麽深刻的和恨,最後都會消弭。
但是這樣的傷害。於宋綰而言,和剝骨筋帶給的傷害,隻會有過而無不及。
而如今看來,他要達到的語氣,未必還會遠。
--
宋綰一直被陸薄川拉倒了地下停車場,陸薄川抑在麵容之下的滔天怒意讓宋綰心驚跳,他按了車鑰匙,打開副駕駛的車門。一把將宋綰甩了上去。
宋綰被甩得差點吐出來。
宋綰抿著,人還沒坐穩,陸薄川已經欺上來,他修長有力的手指的虎口一把卡住宋綰的下,用力收,那力道大得,幾乎要將宋綰尖尖的下給碎!
宋綰被迫和他對視,終於看清楚了他湛黑雙眸裏洶湧的怒意。
宋綰下意識覺到害怕。陸薄川冷然的笑了一聲,他薄如刀鋒:"宋綰,你真是無可救藥!你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是不是不把陸家的人全部害死,你就不會善罷甘休?"
宋綰搖搖頭,說:"我想起來了!真的是!我當初出車禍,本就不是因為被陌生人撞的!而是命人搶了我的資料!我追著的車跑!我真的看見了!監控!那一段的監控巡捕局應該有記錄,你去找巡捕,去翻一翻記錄就知道了!"
Advertisement
當年宋綰出事,巡捕局恨不得將每分每秒的行蹤都調查出來,出車禍的地點,不可能什麽也看不到!
陸薄川上的寒意像是結了冰,他就為了這麽個狼心狗肺又蛇蠍心腸的東西,一次又一次為了破列,他甚至還想把留在邊,生病的時候還想讓獎獎陪。
這種蛇蠍心腸的人,到底哪裏配?
不管他對再好,永遠隻想著要把陸家所有的人都趕盡殺絕。
他當初就不應該救,讓被聞域的人給了!
陸薄川黯黑的眼底風起雲湧,他本來還想給留有一餘地,但就這麽個惡心到家了的玩意兒,哪裏配?
陸薄川道:"既然你這麽想見,想和對峙,那我就帶你去!"
陸薄川說完。"!"的一聲,關了車門,
他繞道另一邊,上了駕駛座。
後鄭則跟上來的時候,陸薄川已經一腳踩下油門,車子劃出一道優的弧線,絕塵而去。
鄭則回過頭去,整個人卻猛地僵住。他的背後不遠站著聞域。
聞域單手抄兜,目注視陸薄川和宋綰離開的地方。
這幾天陸薄川和聞域之間,因為宋綰的事,表麵上風浪就,暗地裏簡直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
今天要不是宋綰提前打來電話,他這邊早就已經控製了聞域。
而這麽久以來,若不是顧及到鍾友良,聞域也不可能就這麽放任宋綰。
但就算暗地裏鬧了什麽也,陸家和聞家表麵上也全都是和和氣氣的,鄭則走過去,和聞域打了一聲招呼:"聞總。"
"鄭特助。"聞域似笑非笑:"我聽說陸總扣了我好幾個人,就是為了找出害得陸家家破人亡的殺人兇手,可這殺人兇手就在他邊,陸總這樣不拿我聞家的人當回事,說扣就扣,未免太過分了點吧?"
"聞總說笑了。陸總哪裏敢聞總的人?一切都是誤會。"鄭則也是一陣後怕,現在陸家和聞家真正撕破臉皮,並不是什麽好事,反而是件鋌而走險的事,鄭則道:"我們手底下的人不會做事,陸總已經讓我狠狠教訓了他們一頓,如果聞總覺得不解氣,我改天將他們過去。親自向你道歉。"
聞域臉鐵青。
而另一邊,陸薄川修長有力的雙手握住方向盤,渾氣低沉冷冽,車子從地下停車場開出來後,駛滂沱大雨中。
這麽大的雨,幾乎要看不清路,陸薄川卻將車子的速度一加再加。
宋綰坐在副駕駛,因為車速過快,即便是係著安全帶,宋綰也好幾次都被甩在車門上,的撞擊著車門,撞得幾嘔吐。
但是生生忍了下來。
宋綰的半邊耳朵已經失了聰,而被扇的那邊的臉頰是麻木沒有知覺的。
因為陸薄川那一耳扇過來的時候,剛好著牙齒,宋綰的裏一陣一陣的腥氣怎麽也吞不完。騰輝的空間大而空闊,陸薄川自上了車後。始終一語不發,上冰寒的氣息卻縈繞在車廂,就算宋綰不去看他,也知道他有多憤怒。
宋綰一陣心慌害怕。
用力抓住車門扶手,不敢去看陸薄川的臉。
在陸薄川帶宋綰去見溫雅之前,宋綰的底氣明明那麽足,可是自從坐進陸薄川的車裏後,卻又開始恐慌起來。
那種恐慌沒來由。卻又實實在在。
但是沒有出聲,隻是故作鎮定的坐在車裏。
車子路過文景路,宋綰看見了那條撞了周竟的長街,眼圈一下子紅了起來。
連綿的雨幕裏,整個文景路模糊不清,可卻仿佛又看到了那天中午,周竟被車狠狠拋了起來的樣子,仿佛還能聽見他朝著自己道:"綰綰,別哭。"
"綰綰,別怕。"
宋綰的心像是被人生生挖了出來。
抿著,不讓自己哭出聲來。
在醫院呆了兩天,四十八小時,周竟從頭到尾沒有醒過來,他醒不過來了。
車子從文景路直接穿過去,整整開了一個半小時,終於到達目的地,陸薄川將車停在了地下室。
宋綰不知道是鬆了一口氣,還是更張了。
自從出獄後,從來未曾見過溫雅,這是一件多麽詭異的事,可卻從未發現過。
因為陸薄川不讓去陸家,因為陸薄川不讓接陸家的人。
車子停穩後,陸薄川解了安全帶,推開車門下車。
宋綰手忙腳的去解安全帶,但一路上,的眼圈都是模糊不清的,解了好幾次都沒解開,等好不容易解開,這邊的車門已經被陸薄川從外麵大力拉開,他有力的手扣住宋綰的細腕,直接將宋綰拖下了車!
猜你喜歡
-
完結1470 章

罪妻求放過
代替以薇嫁秦天翼,不嫁我就弄死這個孽種!三年後她剛剛出獄,就被親生爸媽以寶寶要挾,逼她代替假千金嫁給個傻子。...
261萬字8.18 54927 -
連載3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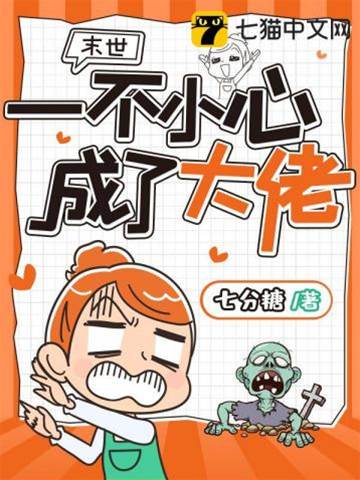
末世一不小心成了大佬
她在末世掙扎五年,殞命瞬間卻回到了末世剛開始,恰逢渣男正想推她擋喪尸。她踹飛喪尸,準備再掀一次渣男的天靈蓋!囤物資,打喪尸,救朋友,她重活一次,發誓一定不會讓任何遺憾再次發生。不過周圍的人怎麼都是大佬?殊不知在大佬們的眼里,她才是大佬中的大佬。
73.6萬字8 8263 -
完結129 章

別哄
沂城傅家丟了個女兒,千辛萬苦尋回后,沂城就傳出了江傅兩家聯姻的消息眾人都以為是豪門里慣有的手段,兩人肯定沒什麼真感情果然,很快就聽說周以尋跟江少斷了聯系,眾人紛紛押注這婚約啥時候能取消江夫人只是去旅了個游,回來后就聽說了這事,她大怒特怒地沖到江京峋的私人住宅,開門進去——卻看到小姑娘穿著件寬大的男士襯衣,瓷白的小腿踢著江京峋,聲音微啞:“滾開啊……”江京峋單膝跪地,把小姑娘攔腰抱起,聲音低啞地哄著她:“老婆,我錯了。”
29.1萬字5 18372 -
完結332 章

先婚后愛:霸道前夫放開我
她嫁給了自己暗戀了十幾年的男人,卻在新婚之夜慘遭羞辱,后來她才知道原來他心中的白月光是自己的表妹,一次次的誤會和算計讓她終于無力承受再愛她,她選擇放手離開,而他在之后則失魂落魄,痛不欲生。幾年之后,她鳳凰涅槃,成為上流社會炙手可熱人人追捧的女王,卻在一次宴會以后再次和他糾纏在一起,牽扯不清,恩怨不斷。“同樣的錯誤我不會再犯第二次,留下來,做我的妻子。”“不,當年我愛你的時候,你棄我如敝履,如今我不愛你了,以后再也不會愛了!” 男人低頭強勢吻住她的唇用志在必得的語氣說“你會的,秦夫人,老婆,孩子他媽。”
59.6萬字8 715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