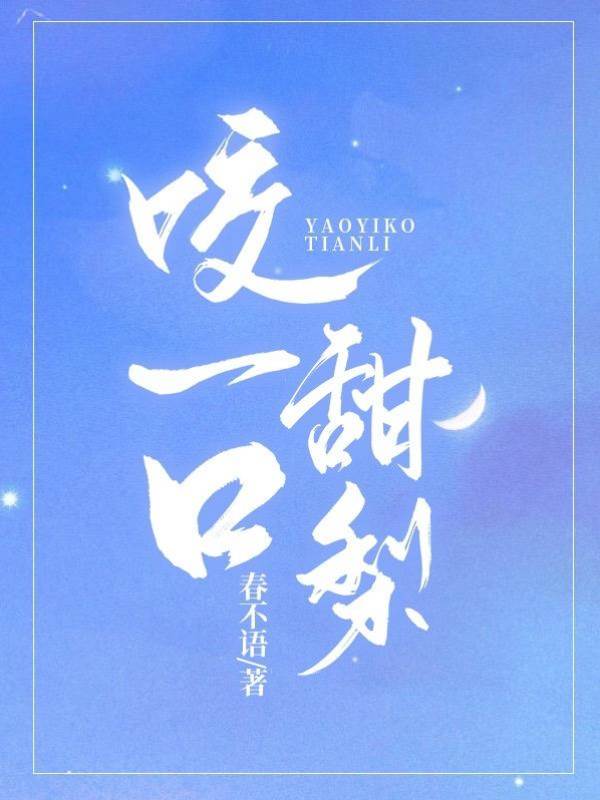《頂級溺寵!嬌軟小漂亮被病態圈占》 第104章 她是白月光
在聖潔的白外麵,小肚中間的位置,突然箍著一個黑的環狀品。
像是限製人行的定位,又像是細版的電子鐐銬。
而在旗袍下擺的纖細小,已經在以極小的作微微發抖。
宋清卿一張小臉白的像紙,輕聲細語,
“對不起,杳杳,我很想陪著你的。”
終於到了朋友,不想掃對方的興。
可是,太痛了。
痛到了忍耐的極限。
明明花園就在幾十米外的地方,明明連那個刷著白漆,在微風中晃的秋千都清晰可見。
可是這麽短的距離,無法到達。
就像是被盛鬱京囚在掌心中的鳥雀,腳踝拴著繩索,繩子另一端被他攥在手中。
隻需要輕輕一拉。
自己就哪裏也去不了了。
薑杳杳愣愣的看著那個東西,看了好幾秒。
卷翹濃的睫終於抬了起來,含著水的眼睛帶著震驚,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東西,聲音中都滿是遲疑,
“卿卿……他——”
細的聲音頓了頓,薑杳杳終於再次找回了自己的音調,
“盛鬱京……他不讓你走遠嗎?”
這種不讓走遠的話無異於是最溫和的說法。
對方沒有明晃晃的指出自己被囚,可宋清卿一張臉卻更白了,神格外淒惶,努力把淚水咽下去,自欺欺人一般地講著,
Advertisement
“嗯……”
“我走太遠的話,就會很痛。”
電流穿過皮的痛和麻,似乎連骨頭都能震碎。
穿著旗袍的鬆開了自己的手指,寬鬆的旗袍落下,罩住了黑的鐐銬。
故作不在乎的笑了笑,看向那個傳聞中被捧在掌心中的薑杳杳,聲音很溫,
“對不起啊杳杳,我嚇到你了。”
隻是那笑容裏的淒哀實在太重了,連薑杳杳那顆心都跟著了一下。
習慣地抿了抿紅紅的,上前一步握住了宋清卿的手,拽著對方快步往回走去,的聲音義憤填膺,氣到不行,
“盛鬱京也太不尊重人了吧!”
“你又不是犯人,他憑什麽這麽銬著你?”
“還限製你的人自由,他真的太過分了!”
穿過參差不齊的樹枝,在地上投下大片大片斑駁影。
日照在空氣中,有細小的塵埃漂浮遊,像是灑滿了金細。
在被握著手的奔跑中,宋清卿偏過頭,看著薑杳杳被風拂的發和亮晶晶的眼睛。
為鍍上一層金影,瓣紅,白如雪。
淺茶發勾勒出風的形狀,像是從天上飛躍而來的小仙子。
踏而來。
帶著救贖和希。
穿著旗袍的愣愣的看著,紅了眼睛。
快回到原點的時候,一道大力拉著薑杳杳,讓停下了腳步。
Advertisement
薑杳杳回頭,宋清卿抓著的手指,聲音很輕,
“杳杳,他一直很瘋,他不是正常人,他也不會聽任何人的話。”
因為自己和盛鬱京的這段孽緣,他被盛父罰跪祠堂,幾次打的皮開綻,踹出碎骨折,可是他依舊不肯放過自己。
即使穿著鮮淋漓的服,角都被咬的斑駁,他也會踉踉蹌蹌地趕回來,然後把自己勒進懷裏。
他說,
他一輩子都不會放過自己。
宋清卿握著薑杳杳的手指,輕輕開口,
“沒關係的,我現在已經不疼了,我們不去遠的地方玩就可以了。”
那位裴先生和盛鬱京私甚篤,甚至還有生意上的往來。
他們是同一個階層的人,既是朋友,又是利益共同。
這種人,怎麽會為了一個人鬧僵。
更何況,誰知道那位裴先生是什麽人?
萬一因為這一點,裴珩遷怒薑杳杳,那自己就真的罪人了。
宋清卿握著那幾纖細手指,輕輕的勸對方,又像是勸自己,
“沒關係的,在哪裏玩不是玩呢。”
“今天能出來認識杳杳,我就很開心了。”
將每一句話都拉得格外長,站在門口的兩道影映在地板上。
“喵嗚”一聲,小貓從薑杳杳懷裏竄了出來,落在地板上,追著自己的尾玩。
薑杳杳靜靜的看著宋清卿,前傾,輕輕抱了抱對方,
Advertisement
“今天的很好,卿卿。”
“既然出來了,那就在下玩吧。”
在溫度漸升的中,薑杳杳鬆開了對方,然後快步朝大廳中走去。
宋清卿怔怔的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
沒過多久,耳邊傳來兩道腳步聲。
看著出現的影,宋清卿越發僵。
肩膀被摟住,盛鬱京含笑的聲音也隨之傳來,
“我和卿卿開玩笑呢,對吧,卿卿?”
宋清卿垂著眼睛沒有說話。
那道頎長的影半跪在地板上,修長有力的手指攥住了的小,熱意穿薄薄的一層布料,幾乎要把的皮燙化。
“哢”一聲,金屬鐐銬被打開,又被盛鬱京似笑非笑地在掌心中把玩。
他起一雙桃花眼,抬起棱角如刻的臉龐仰宋清卿,笑容邪戾,
“我們卿卿,今天確實到了好朋友呢。”
宋清卿一顆心都提了起來。
盛鬱京從容不迫地站了起來,對著那道纖細影笑道,
“嫂子,我們卿卿格有些悶,不太說話,就拜托您了。”
薑杳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麽答應的。
輕輕“嗯”了一聲。
盛鬱京又轉過臉去,直勾勾的眼神看向宋清卿,意味深長,
“我們卿卿,可不要辜負小嫂子對你的關心啊。”
宋清卿聽懂了他的威脅,臉更白了。
如果原先還存了逃跑的心思,那麽當杳杳為自己求的那一刻,今天就再也沒有辦法逃跑了。
Advertisement
不會連累杳杳。
盛鬱京算準了這一點。
恐怕從早晨帶上鐐銬的那一刻,就已經在他的算計中了。
溫暖甜香將環繞,的小手握住了的手指。
宋清卿終於回神,對上了薑杳杳那張到讓人心驚的臉。
對方眼瞳很亮,小臉白的像是在發,
“卿卿,”
握著自己的手指,好像要給自己無窮無盡,足以抵擋暗的力量。
連聲音都輕快明,“看,太升起來了!”
宋清卿怔怔地看著自己被握住的手指,羽睫很輕很輕地了——
這一瞬間,好像真的……
照到了上。
猜你喜歡
-
連載1965 章

左先生寵妻百分百
她是能精確到0.01毫米的神槍手。本是頂級豪門的女兒,卻被綠茶婊冒名頂替身世。他本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專情總裁,卻因錯認救命恩人,與她閃婚閃離。他從冇想過,有一天,她會用冰冷的洞口指向他的心臟。“這一顆,送你去給我的孩子陪葬!”她扣下食指……
164.4萬字8 184421 -
連載2383 章

錯嫁纏婚:首富老公乖乖寵我
為了救父親與公司,她嫁給了權傾商界的首富,首富老公口嫌體正直,前面有多厭惡她,后來就有多離不開她——“老公寵我,我超甜。”“嗯......確實甜。”“老公你又失眠了?”“因為沒抱你。”“老公,有壞女人欺負我。”“帶上保鏢,打回去。”“說是你情人。”“我沒情人。”“老公,我看好國外的一座城......”“買下來,給你做生日禮物。”媒體采訪:“傅先生,你覺得你的妻子哪里好?”傅沉淵微笑,“勤快,忙著幫我花錢。”眾人腹誹:首富先生,鏡頭面前請收斂一下?
219.6萬字8 148201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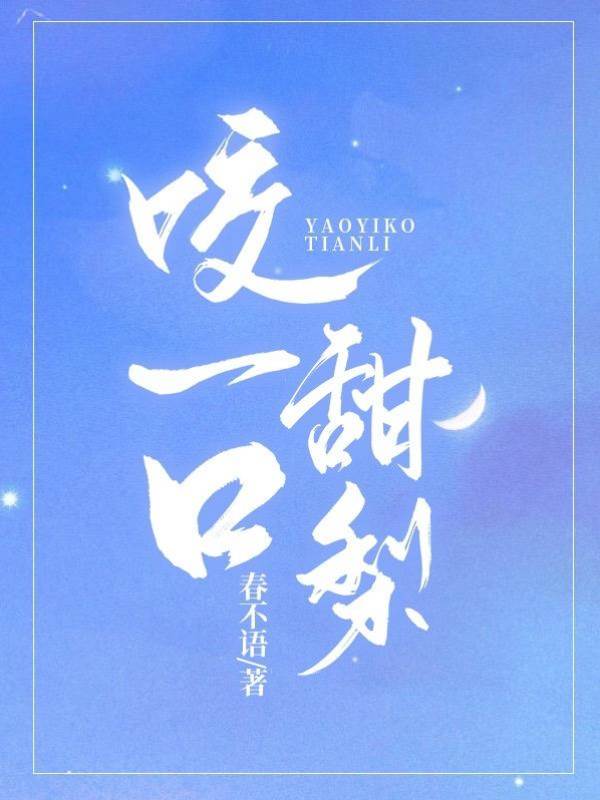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86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