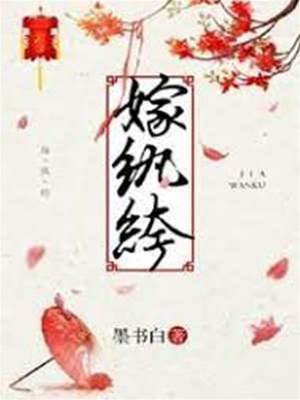《皇后她作天作地》 第70章 癖好(不如改日念念先穿給朕瞧瞧...)
“我昨個兒好像迷迷糊糊地, 見著陛下了?”鐘念月坐在鏡子前,香桃給梳頭時,疑地出了聲。
香桃與書容平日裡, 都被孟公公安排著去了別待著。
們也知曉, 許是陛下旁有什麼事,是們不夠資格知曉的, 自然也就乖覺地自己待著了。
隻晚間, 們才又回到鐘念月旁伺候著。
昨個兒有沒有人來, 香桃睡得正香, 是渾然不知的。
但書容知道。
書容心下輕。
憶起晉朔帝來時的舉,總覺得心底有些說不出的慌。
但不敢在鐘念月面前說假話。
於是書容抿了下, 聲道︰“是, 陛下是來過。”
鐘念月一下坐直了︰“來做什麼了?”
“倒也、倒也沒做什麼……”
鐘念月笑道︰“是不是將他自個兒的裳拿回去了?果然,陛下也只是上說說罷了。”
書容忙搖了搖頭︰“沒呢。還在。”
“還在?”鐘念月轉頭一瞧。
不遠的椅子上, 還放著被團吧團吧抱走的晉朔帝的外。
那豈不是晉朔帝昨夜一來,就瞧見了被隨手放在那裡的裳?
鐘念月心下有一分心虛。不過很快便又理直氣壯起來, 震聲問︰“那陛下來做什麼的?”
書容有些不好說出口。
總覺得這話若是說出來,便有了毀姑娘名譽的嫌疑。
結結道︰“姑娘、姑娘瞧瞧, 屋子裡了什麼?”
鐘念月聽這樣說,心下疑得,忙香桃也不用急著梳頭了,且先站起來,四下打量、搜尋。
“不曾什麼啊……何況我這裡的哪樣東西不是他備下的?說起來,本也該是他的東西。取便取了……”
Advertisement
鐘念月的聲音到這裡戛然而止。
鐘念月疾步走到了那屏風前。
這江縣的縣衙自然遠不比京中住的豪華,裡間許多擺設、家都有缺失。
連個掛裳的架子都沒有。
於是鐘念月換下來的服, 便都是掛在那屏風上的,與晉朔帝一致。若非如此, 也不能就將晉朔帝的外給拿走了。
可如今那屏風上頭……
了件裳!
不是外,倒也不是裡,而是夾在中間那一件短襦。
他拿我的裳作什麼?
鐘念月愣了愣,又覺得別扭,又本能地有些耳熱。
他要從我上沾什麼氣?
古人不都說子屬麼?他倒不怕?
鐘念月疾步出了門,不多時便到了晉朔帝的門外。
孟公公一見,連忙道︰“哎喲,姑娘怎麼起得這樣急?連頭髮都還未梳好呢。不急不急,今個兒江縣中的形已經有了好轉,姑娘且寬心罷。”
鐘念月聽他這樣說,倒還臉紅了一下。
只因急著來,並非是因著江的災,而是這樣一樁小事……與江的事比起來,這是小事了。
鐘念月立在那裡愣怔片刻的功夫,門便已經傳出了晉朔帝的聲音。
“念念來了?進來罷。”
他的口吻倒是平靜沉穩。
與往日沒什麼分別。
這一下便好像又襯得這樁事不算什麼了。
此時書容提著擺,勉勉強強跟了上來,上氣不接下氣,在鐘念月耳邊小聲道︰“姑、姑娘……昨個兒您睡得迷迷糊糊,是您自個兒應了的。”
鐘念月一驚︰“我應了什麼?”
“陛下問您說,不過分吧?您說,不過分,可好了。”
鐘念月︰“……”
“念念?”屋晉朔帝似是已經等不及了。
Advertisement
鐘念月推門進去。
晉朔帝端坐在桌案後,跟前立著知縣,還有幾個生面孔。
再仔細看上一看,晉朔帝換了件外,今日著的是玄衫,上面約印有金的暗紋。氣貴且勢威。
晉朔帝應當是正在忙,並無空隙應付。
他頭也不轉地道︰“念念自己坐。”
鐘念月左右一瞧。
這屋子裡禿禿、冷冰冰,連一張待客的凳子也無。
鐘念月問一旁的宮人︰“我坐何?”
宮人面茫然,自然也是不知。
鐘念月也不為難他們,便一挑眉尾道︰“那我不如坐陛下的帳子裡去好了。”
順便找找的裳。
晉朔帝明明正在與知縣說話,方才說到︰“你明日帶人往……”他卻生生地頓了下,轉頭與鐘念月道︰“念念,過來坐。”
鐘念月頭也不回︰“陛下那裡也沒有凳子。”
晉朔帝笑道︰“朕坐的不就是?”
鐘念月頓了頓,這才轉往回走,等走到了桌案前,晉朔帝還當真起了。
於是眾人便眼見著晉朔帝將他的座位讓給了這位主兒。
“坐罷。”
晉朔帝道︰“正巧與你說,甦傾娥帶來的糧食,分別安置在城西、城南兩富戶私人持有的倉庫之中。只是安置得並不多。想是怕再發大水,撤走不及。不過到底是低估了江縣災的百姓之眾,於是昨夜又連夜有新糧城。被武安衛了個正著,如今已經順著那條來路,去一鍋端去了。”
鐘念月笑道︰“這個消息我聽。”頓了下︰“不過甦傾娥哪裡來的這樣多的糧食?”
晉朔帝淡淡應聲︰“是啊。”
這個人似是有著某種非凡的造化境遇。
竟能絕逢生。
再見時,又能改頭換面,讓自己站上高。
Advertisement
“恐怕在黨之中,的地位不低。”晉朔帝道,“等回去之後,便將甦家拿下。”
鐘念月也沒說什麼。
原主很討厭。
但對原主很刻薄的甦家,也一樣不是什麼好東西。抄了便抄了罷。
鐘念月在椅子上坐了會兒,覺得有些硌。
也不知晉朔帝怎麼能在這樣的地方,坐得面不改,還形拔。
晉朔帝瞥見面上倦,問︰“坐著不舒服?”
“嗯。”
晉朔帝笑道︰“坐朕上便要舒服些了。”
底下人一個個聞聲面驚恐。
鐘念月卻是嗆了回去,全然不稀罕︰“罷了,萬一今晚陛下又趁我迷迷糊糊的時候,問我,換你一條不過分罷?那怎麼好?”
果然發覺了。
還記仇得很。
晉朔帝面上沒有一點怒,更沒有憂,反倒笑意更濃了些。
晉朔帝卻是一彎腰,不顧驚訝瞪他,將按在了自己的上,道︰“頭髮也沒梳好。”
“把梳子拿來。”
孟公公趕給遞上了。
晉朔帝這才面向其余人,雲淡風輕地一笑道︰“正如昨個兒知縣所說,常養在朕的側。朕是舍不得見吃半點苦的。”
鐘念月有點臉紅。
晉朔帝待一向很好,但很與旁人這樣直白地提起。
等這邊晉朔帝與他們說完了話,將人打發走了。頭髮便也就梳好了,梳得松松垮垮,不過好歹有了個形狀。
鐘念月終於得了機會問他︰“陛下為何拿我裳?”
晉朔帝︰“作換。”
“還趁我睡得迷糊時來……”鐘念月沒好氣地道。
晉朔帝︰“嗯,自然。只有此時,無論說什麼,念念都會應。”
鐘念月︰?
學到了。
好,今夜我也要潛你的屋子。哈,便同你提個什麼要求好呢?一來就讓你殺太子,那是有些急了,不穩重。
Advertisement
鐘念月腦子裡已經排列了種種。
於是一下就不生氣了。
拿吧拿吧。
鐘念月粲然一笑道︰“我還當陛下有什麼癖好呢……”
晉朔帝垂眸︰“癖好?”
“嗯。我以為陛下喜好穿子的裳呢,只是想想,我的裳那樣小,陛下定是穿不下的。”
孟公公心下一咯 ,心道姑娘啊,您可真是什麼話都敢拿來調侃啊!
晉朔帝卻神不變,隻不聲地注視著,笑道︰“嗯,朕穿不下念念的,念念卻穿得下朕的。不如改日念念先穿給朕瞧瞧吧?”
鐘念月︰?
這就反客為主啦?
輸了輸了!
鐘念月腳底一抹油︰“我得肚子都疼了,我且用膳去了。”
另一廂甦傾娥正咬牙切齒地道︰“我不去了,那些災民,不,那些刁民,渾然沒有規矩!竟然敢手來搶……”
上下兩輩子加起來,也不曾過這樣的驚。
為何要將自己弄到這般境地?
相公子好笑地看了看。
好似昨個兒因為百姓追捧而心下歡喜的人不是一般。
“你一定得去。”相公子頓了下,輕聲反問︰“怎麼?你怕了那位鐘家姑娘?”
甦傾娥咬了下︰“自然……不怕。”
“那便去。否則你以為我拿了那麼多糧食來給你做什麼?讓你扮過家家的把戲,說不玩就不玩了嗎?”相公子的聲音微冷。
甦傾娥打了個哆嗦,不說話了。
“去嗎?”他問。“……去。”
將語氣放得了些,哀求道︰“只求公子能多賜我幾個傍的護衛,這樣我就能有把握,住那鐘念月的氣焰了。”
相公子點了頭,心下卻是嗤笑。
也就隻記得鐘念月的氣焰了。
傻子。
你若做得好了,揚名天下,何止一個鐘念月呢?
只是這廂剛廢了相公子的口舌,門外便有人火急火燎地撞門而,噗通一聲跪倒在地上,道︰“公子,咱們的糧車,被、被劫了!沒有一個活著回來的人……還是咱們的人前去查探,才知曉的……”
相公子的臉驟變。
而甦傾娥臉也變了。
不想去做,和不能去做自然是有區別的。
可以不想,但不可以不能!
不多時,卻是又有人疾奔而來,臉蒼白,滿頭大汗︰“公子,公子,糧倉、糧倉的門破了!”
那糧食呢?
自然也沒有了。
相公子連問都不必問。
甦傾娥兩眼發紅,想也不想就道︰“定是鐘念月!定是!”
就是我的克星!
這廂鐘念月慢悠悠地陪著又發了一日的錢。
而縣衙中人則組織著,用搶來的糧熬起了粥。
百姓們今日也是一樣的激涕零,只是耳邊了幾聲“菩薩”。
這一日很快就過去了。
相公子那廂還著。
鐘念月卻難得心大好,坐在院子裡,著天開始等天黑。
好不容易等到天黑了,卻也有些困了。
書容知要去尋晉朔帝,不由道︰“姑娘快些去吧,一會兒都該困住了。”
鐘念月搖搖頭道︰“不,你不知,他平日裡這個時辰都還未睡呢。”
當真是最最敬業的帝王了。
倒是鑽個空子都不好鑽。
鐘念月等啊等啊,又等了半個時辰。
而這廂晉朔帝喚來了宮人問︰“鐘姑娘還在院子裡坐著?”
“是。”
“取個披風給,再拿上手爐。”他頓了下,笑道︰“備水,朕這就歇息罷。”
猜你喜歡
-
完結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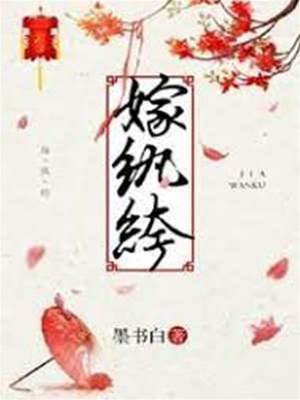
嫁紈绔
柳玉茹為了嫁給一個好夫婿,當了十五年的模范閨秀,卻在訂婚前夕,被逼嫁給了名滿揚州的紈绔顧九思。 嫁了這麼一人,算是毀了這輩子, 尤其是嫁過去之后才知道,這人也是被逼娶的她。 柳玉茹心死如灰,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后,她悟了。 嫁了這樣的紈绔,還當什麼閨秀。 于是成婚第三天,這位出了名溫婉的閨秀抖著手、提著刀、用盡畢生勇氣上了青樓, 同爛醉如泥的顧九思說了一句—— 起來。 之后顧九思一生大起大落, 從落魄紈绔到官居一品,都是這女人站在他身邊, 用嬌弱又單薄的身子扶著他,同他說:“起來。” 于是哪怕他被人碎骨削肉,也要從泥濘中掙扎而起,咬牙背起她,走過這一生。 而對于柳玉茹而言,前十五年,她以為活著是為了找個好男人。 直到遇見顧九思,她才明白,一個好的男人會讓你知道,你活著,你只是為了你自己。 ——愿以此身血肉遮風擋雨,護她衣裙無塵,鬢角無霜。
81.5萬字8.46 48627 -
完結375 章

寵妃有道:戰神王爺不好惹
別人穿越都是王爺皇子寵上天,打臉虐渣看心情。 她卻因為一張“破紙”被人馬不停蹄的追殺! WTF? 好吧,命衰不要緊,抱個金主,云雪瑤相信她一樣能走上人生巔峰! 不想竟遇上了滿腹陰詭的冷酷王爺! 云雪瑤老天爺,我只想要美少年!
88.5萬字8 16404 -
完結396 章

嫁給反派后天天想和離
穿成惡毒女配之后,姜翎為了不被反派相公虐殺,出現慘案,開始走上了一條逆襲之路。相公有病?沒事,她藥理在心,技術在身,治病救人不在話下。家里貧窮?沒事,她廚藝高超,開鋪子,賺銀子,生活美滋滋。姜翎看著自己的小金庫開始籌謀跑路,這大反派可不好伺候。誰知?“娘子,為夫最近身子有些虛,寫不了休書。”不是說好的?耍詐!!!秦子墨:進了我家的門,還想跑,休想。
71.2萬字8 1803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